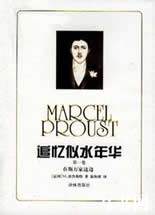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美]-第4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异。听起来犹如律师辩护时那夸张激昂的论辩,完全离开了他通常的语速。这是过度激动和神经兴奋造成的声音放大现象。这同样的激动和兴奋也曾使盖尔芒特夫人在一次晚宴上,将声音升到极高的音域,目光也越抬越高。“我正在打算明天早晨派一名卫士给您送信去,把我的激动心情告诉您。我本来倒是希望能当面向您表示这种心情的,可是,瞧,那么多的人等着跟您说话!弗罗贝维尔的帮助当然是万万不能小看的,但是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经得到了部长的许诺,”将军说。“啊!太好了。况且,您已亲眼看见,这样一位天才确实是受之无愧的。霍约斯①听了非常满意,可是我没有看见大使夫人。除了那些有耳无聪,生着舌头却不会说话的人以外,谁还会不为之欢欣鼓舞呢?”维尔迪兰夫人趁男爵走开去跟将军说话的机会,跟布里肖打了个手势。布里肖不知道维尔迪兰夫人会对他说些什么。不过他走近对老板娘说:“男爵看见凡德伊小姐跟她的女友没有来,非常高兴。他对她们十分反感。他说了,她们的道德品行叫人害怕。您无法想象,男爵的德行是多么纯洁和严肃。”
……………………
①霍约斯伯爵,当时奥地利驻巴黎大使。
布里肖说这番话只想到要让老板娘高兴,也不顾我听了心里有多么痛苦。可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维尔迪兰夫人听了一点儿也没有高兴:“他是一个淫邪之徒,”她回答。“您去把那位夏吕斯拉过来,建议跟您一起抽支烟,设法别让他发现,我丈夫把他的杜尔西内带走了。”布里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我对您说,”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消除布里肖最后一丝疑虑,又说,“我家里出现这类事情我有些不太放心。我了解,他有过那些肮脏的前科,警察的眼睛正盯着他哪。”维尔迪兰夫人一旦获得恶毒的灵感,立刻就会显示出即兴编造的天赋,她绝不肯只说两句就此罢休:“据说他还坐过监狱。真的,真的,这是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告诉我的。而且他的一个街坊还告诉我,真令人难以想象,他甚至还引狼入室,把强盗歹徒带进自己家里。”布里肖经常出入于男爵家,他不同意这种传言。见布里肖不信,维尔迪兰夫人越发激动起来,居然高声叫道:“既然我这么对您说,我就敢向您保证!”这是她信口雌黄以后竭力表明自己是言出有据时的惯用语, “他有朝一日也会遇到他同类一样的命运,遭人暗害。他甚至还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他正落在那个叫絮比安的手里呢。他竟有脸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这人原来是一个苦役犯。您知道吗?我可一清二楚,哼,我是经过调查的。他掌握着一些不堪入目,让人害怕的信件,以此把夏吕斯捏在手里。这是一个亲眼看到那些信件的人告诉我的:‘要是您读了那些话,您一定会病倒的。’那个絮比安用木棍赶着他走路,叫他把自己所需要的钱吐出来的。放在我,情愿去死,也不要象夏吕斯那样苟且偷生。总而言之,如果莫雷尔的家人决定向他提出起诉,我可不想被指控为同谋。他要执迷不悟,那是他自己愿意铤而走险,我可做到了仁至义尽。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天天都有快乐的事情。”维尔迪兰夫人盼望着她丈夫快跟小提琴手交待,想到这里她非常兴奋地对我说:“您问问布里肖,我是不是一位打抱不平的朋友,我对伙伴是不是赤胆忠心,肝胆相照。”(这话暗指她及时挑动布里肖,先后跟他的洗衣妇和康布尔梅夫人闹翻。这阵反目以后,布里肖理智几乎丧失殆尽,而且据说还变成了一个吗啡瘾。)“您是一个无与伦比,眼光敏锐,见义勇为的朋友,”大学教授天真激动地附和道,“维尔迪兰夫人使我避免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维尔迪兰夫人离开后布里肖对我说。“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我的朋友戈达尔说过,她是一位干预别人事务的专家。我得承认,想到可怜的男爵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快要受到打击,我十分难过。他还狂热地迷恋着那小伙子呢。如果维尔迪兰夫人这一手成功的话,那这个男人就要倒霉了。当然她难保一定会成功。我只担心她只能在他俩中间挑起不和,到最后,不能把他们拆开,只能叫他们俩一起跟她反目。”维尔迪兰夫人跟门客们经常发生此类事情。显而易见,她需要维护自身跟门客之间的友谊,但在她身上这种需要日益为另一种需要所支配,即她需要她与门客之间的友谊永远不受门客们相互间友谊的管束。同性恋只要不涉及正统,她不会提出什么异议;一旦触及正统,她却跟教会一样,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作出半点让步。我有些害怕起来。她之所以对我耿耿于怀,别不是由于我不让阿尔贝蒂娜白天上她家里来的缘故。她不要象她丈夫在小提琴手面前拆夏吕斯的台那样,也在阿尔贝蒂娜身边着手或者已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以此来离间我们俩人的关系。“去吧,快去把夏吕斯找来,找一个借口,是时候了,”维尔迪兰夫人说,“特别注意,我不派人去找您,尽量让他回来。噢,都成了什么晚会哟!”维尔迪兰夫人还在说,她气急败坏的真正原因昭然若揭。“给这批蠢货演奏这样的杰作!我不是指那不勒斯女王,她是个聪明的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请理解为:她对我很客气)。可是其余的人!噢!简直叫你发疯!有什么办法,我,我可不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了。年轻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应该学会烦恼,我当时还能尽力而为。可是现在,噢!不!这是不由自主的,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生命太短暂了。要我自寻烦恼,跟蠢人交往,还要弄虚作假,假装觉得他们很聪明,噢!这我怎能办到。去吧,怎么啦,布里肖。我们可磨蹭不起。”“我这就去,夫人。这就去。”布里肖见德都尔将军已经走掉,终于答应说。不过大学教授先把我拉到一旁说: “道德责任,并不象我们的伦理学所教导的那样,清晰明了,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尽管神智咖啡馆和康德啤酒店认为道德责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却仍然十分可怜,连善的本质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我本人就为我的学生讲解此位名叫埃马纽埃尔·康德的哲学,可不是自吹,也不是有什么偏见,关于目前面临的社交决疑论的情况,我在那本《实践理性批判》中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阐述。这位伟大的还俗者信奉柏拉图学说,是为了按照日耳曼的方式,建立一个具有史前情感和枢密院意志的德国,完全是出于某种波莫瑞神秘主义特有的实用目的。他讲的当然是《会饮篇》,但他是在哥尼斯堡讲课,使用的是那地方的特有方式。讲课内容虽然严肃庄重,但都难以消化,因为里面讨论的尽是腌酸菜,却避而不谈小白脸。①我们的女主人请求我助她一臂之力,遵照正规的传统道德,我不能拒绝她的请求。确实不应听人花言巧语,上当受骗,不然就会说出许多蠢话。可是也应该说回来,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如果让母亲们获得选举权,可惜的很,那男爵在教授品德的评比中就有可能要名落孙山,他是带着一个放荡者的气质在从事教育家生涯的。请注意,我可没有说男爵的坏话。这位男子举止温文尔雅,可切起烤肉来谁也比不上他。他虽然具有诅咒的天才,但又拥有无边的善心。他倒象一名高级小丑,能引人发笑,可是我跟有些同仁——请别弄错,是学士院院士——在一起,如同色诺芬②所说的每小时花一百个德拉克马③,竟买一个无聊。
……………………
①柏拉图《会饮篇》中讨论过各种爱情类型,其中论及成年女子对美少年的恋爱问题。
②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约公元前430—约公元前354)。
③古希腊银币名。
但我担心的是他有些超过了道德健康的要求,对莫雷尔施与了过多的善意。尽管我们不知道年轻的苦行僧对教理讲授人给他规定的特殊修行项目表现出何种程度的顺服或反抗,但是不必成为大主教我们也能断定,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向他发放许可证,听其崇拜撒旦,那我们就如人们所说,对圣—西蒙和佩特罗尼乌斯①而传给我们的这蔷薇十字会②就犯了宽容的错误。然而,维尔迪兰夫人让我去牵制住夏吕斯。她是出于对这道德罪人的好意,并想试一试她的医治方法灵不灵。她要直言不讳地跟蒙在鼓里的小伙子挑明一切。这会夺去他所喜爱的一切,甚至还会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对此,我不能说无动于衷,我觉得我似乎在把他引入陷阱,似乎在向卑鄙的行为让步。”布里肖说得动听,可这卑鄙的行径,他毫不犹豫地就去做了。他挽住我的胳膊说:“走,男爵,我们去抽一支烟怎么样。这位小伙子还没有领略公馆的全部奇观呢。”我托词说我得回家了。“再待一会儿吧,”布里肖说。“您知道您得带我回去,我可没有忘记您的应诺。”
“您真的不要我取出银器来看看吗?没有比这更方便了,”德·夏吕斯先生说。“您答应过我,对莫雷尔,一字别提他受勋的事情。我想过一会等人走空一些,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大吃一惊。尽管他说,艺术家对这套东西并不稀罕,倒是他叔叔希望他获得这个荣誉(我听了脸都红了,因为维尔迪兰夫妇从我祖父那里打听到了,究竟谁是莫雷尔的叔叔)。怎么样,您真是不要我把最漂亮的银器拿出来让您瞧瞧啦?”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不过您熟悉那套银器,您在拉斯普利埃见了都不下十次了。”我未敢对他说明,可能使我发生兴趣的,并不是那几件散发着布尔乔亚气息的劣等银餐具,即便是最为富丽堂皇,配套最为齐全的餐具,我也毫不在乎,我感兴趣的是巴里夫人收藏的几件餐具样品,那纵然是印在一张美丽的木刻上,也一定赏心悦目。
……………………
①运动。运动倡导人受1880年左右的象征主义影响,重提十七世纪的这一结社。拉丁作家,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著有淫诲故事。
②十七世纪德国一种神秘主义的秘密结社。布里肖此处暗指一种文化艺术我的心事十分沉重——
尽管这并不是由于发现了凡德伊小姐的到来而引起的——在社交场合我总是心不在焉,坐立不安,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漂亮程度不同的玩物上。能使我聚精会神的唯有向我想象发出召唤的某种现实。比如我下午如此渴望见到威尼斯,要是能让我看上一眼今晚我就有可能达到聚精会神的境地。有些凡常的因素也具有这种功能。凡常因素与表面事物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却比表面事物更为真实。凡常因素总是唤醒我体内通常沉睡着的心灵;当心灵浮上意识的表层,我便感到莫大的喜悦。我随布里肖和德·夏吕斯先生走出称为剧场的客厅,又穿过其它的客厅。这时我发现一件件家具中夹杂着一些拉斯普利埃的气息,但我却从未加以注意。公馆的陈设和古堡的陈设之间诱发着某种令人熟悉的格调,体现着一种长时不变的统一性。布里肖笑着对我说:“瞧,您看见这客厅的布置了吧,现在您对二十五年前蒙塔利维街的情形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再纯属grandemortalisaevispatium。”①
……………………
①参见110页注。
我对布里肖此番话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