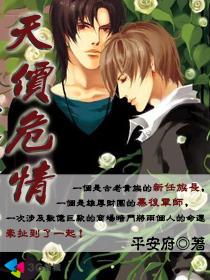Σ��ʹ��-��1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Ī��������̡�����ɣ��м��������ֽ�����12��סլ��
�ⴱסլ���������ص㱣�������ᣬ������Ȩ���Ըı���ۣ�������ֻ�ܰ�����������������װ���ϣ������������ɫ�ͳ�ɫ��װ��ǽ��������µ�ԡ�ף�װ�н�˿��Ĵ��߽������ӵı�������ά�ǹ㳡���������סլ���������һǧ��һҹ������Щ�����������Ľ�����
�������������ɫ��ش�Ϊͷʹ����������������κ����ἰ����������������ᣬ����Ǹ�����ϣ������������ﲻ����Ļ������������綼�ڶ�¥������ȥ�������飬�������ơ�
����ô�ҿ�����������ɫ�е㲻�Ծ�����������Ƥֱ��������ϣ����˯�ⲉ����˵��
������������������Ҳ���ס�ˡ�����������ɫ����һ���ʹ����Ӿ�����ʵ�龰֮�����һ�ֳ�ͻ����
���ҵ��ֵܣ���������������ʫ�İ��ǻ��˵�Ű����������ǧ����δ�û�г�ͻ������ת����ϣ������װ��ģ�������Ǹ���������Уÿ����Ǹ�������ʱ���뿪ʹ�ݰ칫¥��90��100�����Ժء��Ǹ��м�������Ů��Ҳ����������ʱ���뿪�ͷ��ذ칫¥��������˲���һ�ۡ�������Ҳ��Ϊ��ľ�ϸ�۲���˰ɣ���
��ϣ�������Ц��һ�����ϲ��˵Ц������������˫�ۡ�
������Ц��˵�������Ǵӽ���ı�ֽ�Ͽ���������ʹ�������ڲ��ٰ�һ��ʮ�������罻�����˵�ֵܣ����������������ת��������һǧ���˰ɣ���˵�����������õ����壬���ǰ���������һ�������ޱȵ������أ���
�����������������һ����ϣ�����Ȼ�����������Ϻ�ɫ�ij�ɳ���ϴ���Դ��������ϰ���ɫ����������Ƭ�İ˽��ο����ϡ����Ϳ������ߵ�������һͷ�����������Զ����������ά�ǹ㳡��
����ע����ĺ����������·�����������ij�����������γ������������Ϳ����������صȺ�ͨ���ɻ�ת�̣��Ա���ǰ�䶯�����γ��ľ��롣��Ӣ�������ؼ��ɡ����������������˿�����
��������һ���������ؿ��ﹾ���š�
��Ҫ����һ���¾ͺ��ˣ������������ؽ�ҧ�������غ��³������֡������Ǵ����쿪ʼ��������������ֻ�������ˡ���
����˵�öԡ������ظ��͵������������Ͱ�����ͬ�´�ʱͨ�����õIJ��ԡ����������ɵر�ʾ��ͬ������֪û���ĸ���������Ը������ͬ�������������������һ���취����
��������˫Ŀ��б�ӵĵ���ɫ�۾���µһת�����˿����ء����뽲����
�����Ƿ���Ϊ���������㹻�ľ���ʵ��ͻϮ�·ƶ��¹�ۡ����
��������һ���������ǵġ���
�����������ں͵��˾��м���������ܵ�̸��ʱ���·ƶ��¹�ۡ�ܱ����ǿ��ƶ�ã���
����˵����
���ڴ��ڼ䣬���˻������ķ����߸����ǵľ�����������
���˲����ð������サ̸����������˵����Ӳ��Ӣ�Ψ�ֳ���˯���е��������
�������أ�����������ֱ��׳�Ŀ��Ƿ��ʶԷ��������Ǵ���������ѵ�ֻ���Ϳ����Ŀڴ�һ���������Ŀ�ʯ�����ʥ�ܵ�ѵ�룬˵���Dz��ܸɵ��ǰ����������Ŀ��ˣ����������������أ���
������������������˸���������������
�����سٳ�û�лش�������˫����ɫ���۾��������ܿ��������ڽʾ���֭�����˼����
�����Ƕ����ж�С�顣����������������µ�С����ڹ��������ɵ�������ɵ��������С��֮��������𣿺��߳���ʱ����һ����Ŀ�꣬���Ҫ������ƽʱ���ڹ��ڣ�һٹ���ֺ��ʵ�Ŀ���DZ��й�����ˣ������ж�С���ɹ��ӵ�ҽ�������ġ������ˡ��ṩ����ѡ����������ǵ��ճ���֧���ල���ǵ��ж������Ҳ������ǵľ��ߡ��������躬�ߣ��ԹԵ�����������������ӵ�����������мң�Ҳ���ǿ������ϱ��ĸ������ߣ�����֮�⣬������ʲô���أ�
���ص���Ƭ�����������һ������������ϸ�졣��˹���ֿ���֯�ķ�����������֮����ش���磬һֱ���������Խ���ӿ��������鲻���������п��������������۸��ӵ�Ŀ�ĺ��ֶ�Ū��ϡ���Ϳ�����ӵ²�����˿�����ɣ��������������Ŀ�ꡣ����һ����ȫ����������������������������ϵ���ͻ�������㷺��Ӱ�졣��һ�㿭������������
������������˸����ֵĹ�ԣ�Ҳ��������ҹɫӳ����������ɫ��Ĥ����ɵĻþ���Ҳ��������¶�����������塣
�����ַ������ɡ����������������˿�������Ŷ���ԣ����ַ�ʽ���ɡ��桭�����
�͵¡��������뿪�˰칫¥�����������ǹ���������İ칫�ҡ����ոպ�һ��Ů����Ա̸��һ�ʾ���δ��ľ��ˡ���λ����ԱĿǰ����ͼ����פ�ص�һλ�������˽�����Ŀ��
����ˣ�����Dz���������ꡣ����������˵������С�ӽ���ķ˹���ڴ��ڼ任�����ι�������
����ΪʲôҪ��������Ϊ���������룿��
�����������������ַ������⡣��������һЦ������С������ƶ�������
�����Ǹ����ң����͵¸ɰͰ͵������������Աɨ�ˣ��������Ӣ��ϰ�߷��Ļ�������
�͵����ﲻ���ź���������ķ˹��������˹�Ǽ����صİ칫����ȥ����������������һ���Ժ�һ����ľ���ʵ��׳�ĺ��Ӷ�ס�ſڣ�ֻ�����˳�����������ҵķ���Ͷȥ���ݵ�һƳ��
�����������Ǹ��������������У����
���Ǹ���ײ������ô���ˣ���
����������Ť�ˣ�Ĵָ���ۡ�ֻҪҽ����Ϊ��û���ˣ��Ϳɳ�Ժ����
����������С���أ���
������ľ���ʵ�������Ϸ·�Ҫ������¶ʲô�����͵°��⣬Ҳ���ǵ�������Ĭ�ɣ�
����С�Ӹ�ץ�����ˣ������������η��£�һ���صص�������å����
���ܺã������û�������
��û�����������˹�ظ������Ļ��������W��һ�����ƻ�������Զȥ����������û���������ƴ������ֱ�������ϴڵĻ�����������ֻ�ָ���������ͷ��ء�������Цһ�����������ֱ��ĮȻ��������������Լ�������ģ���У�����Dz�����ʲô֤�˻�֤���
��лл����
��û��ϵ����У����
���ټ�����
����˹��ͷ����������Ŷ�����°��ˡ���һ������һ��ȥ�ˣ����ڽ����ˡ���
�͵¡���������Ը�ⲻ�̲�����˵��һ�����罻���ϳ��õ�������������˹�Ĺ�ϵ��������˫���Ա˴˵���ʵ�������ղ����Ļ����ϣ�����Ǽ�����ġ�
�͵����������Լ��Dz�¥��¥�ݣ��������ϵ�һ�ȴ�ǰ����Ƭ�̣�����Զ���Ĺ㳡���°����Ⱥ�����ڻؼҵ�·�ϡ����ϰ���İ��½����������������������ϰ��°࣬���Ǵ���û������ץ����ʱ�䣬�ӵ绰Ҳ�Dz��Ų�æ��ÿ����Ҫ�����߸��绰���Ų�ȥ�ӡ����������д��ݵĽ��࣬Ҳ��ֻ�����ĸ������Ź�����Ϣ�ĵ��к����в������������
�˿̣�̫������Һڵ��Ʋ㣬��������ȼ��һƬ�ۺ�ɫ����ϼ������ҹĻ����ǰ���˳������龰���������ˡ���������Ӱӳ�ڲ�ƺ�ϣ��·���һ�������ˣ����ߡ����͵�������һ�����ص�������һ�߶���ʮ�ּ��ϵ�ʬ�塣
û������������ˡ������������������Ӽ��ڸ�����һ�ų����ϣ���סһֻ������̵�ȼ�������е����̡������������������ĵ�������ͷ�����Ǹ��һ�վ���������˸��Ӻ������˲��ߣ���������׳ʵ���̶̵IJ������۲��Ķ�ͷ����Ͱһ�����Ĺĵġ�������һ�ɡ���ʶ������˭�𣿡����ſ������У��͵¼�״���̶��������˻��ɡ�
�͵¿���������Ĵ�׳�ļһ����š������ˡ�����һȦ��վ����Զ��һ�࣬������ͬ����������Ĵָ��ʹ��գգ�ۡ��ܿ죬���������˺�����֮��ľ��롣
�͵�������������֥�Ӹ��ѧ����ѧ������ķ���ȡ��˵�ͷ�Զ�ô��֣������������Ժ������뵽�ľ�����ķ���ȵĿ�ͷ����ȫƾ����������λ������������������ʼ��������������һЩ�������
��ķ�����ܺ�����������������ĸ����ɹ㳡�Ͻ�Ҫ���������顣���������͵�����������ΪʩŰ���Ե�ç�����������������ߴ����֡��������һ������ѧ�������Ȼ����IJ�����Ϊ��ijЩ�˶�������״̬��������Ҫ������ۡ�
ĺɫ�ĺϣ��㳡������ϡ�١��ٹ������ӣ��Ͳ�����ʲô�˴�˾��������������˽�ֻ����ȫ����������å�İڲ���
�����˿�������ʾʽ���ӱ���һ����������ͷ�������ؼ�����å����һ���������к���ɣ�����ĸ���·��Ӣ���˶�Ӧ��ͦ����ֹ�����DZϾ������Ĺ��ҵ���å�������˱���Ϯ�������˵�����Ӣ��ʱ�з���������ΪǮ��������Ϊ�������������ۡ�
��������ǿʳ�ķ���������Ϲ����������Ƶ����˿���ֻ�а���ķ��ˡ��͵¿����Ǹ���Ұ׳ʵ�ĺ��ӳ�������һ��������ͬ����������ߡ�
����������ˡ�������ʲô��ϵ��������һ���������������
�͵³����ͷ�ļһ���ұ����ȡ��һ�س�2Ӣ�ߡ���1Ӣ�������������⣡���͵µ��ĸ�������һ������һ�������ر���¥�ݣ����ǰ�š�
ǰ���ƺ�ϣ���ͷ��С���������������һ�£��͵�һ�ӣ�ֱ����ͷ���������Աߵ���С�����ժ������ͷ���ϵ��������ڵ��ϣ��ֺǺǵ��ýŲȳ���Ƭ���͵´�����·�����Ҷ�������ʻ���ij��������㳡��ȥ��������Ϊ��С�ӿ�ʼ�������������˺�������������һ��ֱ����ǰ��
��ι�����͵³���ɤ�Ӻ��������Ǽ���С�ӣ���
������ͽ˭Ҳû�����ᣬһ������ͷ��������ϥ���͵�һ�ߣ��̵��ڵء���������ǰ����һ�����ߡ�
��ס�֣����Ǽ��������֣���
��һ�أ��͵µ������ȳⷢ�������á�Ϊ�ļһ�Ŀ¶�⣬�������˹������͵���Цһ������������ʹ��һ�ӣ�����������
�͵¹����ಽ�������Ťס���ĸ첲�����ֶ�������������賤ì�Ƶؽ���ͷ��ס����ּһ�ĸ������ۿ����ǵ�ͬ���ڲݵ��Ϲ�µµ������ͷ���ߴ��Ż�£�������С�������ˣ����˶����ֻ���ȥ��
����һ�ᣬ�ղŰ����С��ҡҡ�λε�ֱ������ȥ�Լ���ͬ������������������£���ת��������һ�Ų��������͵¡������ֱ�Ĩȥ��ǵ�Ż�»����������������������У����������ơ���˵�ţ��ߵߵ�����ȥ�ˡ�
�͵¶�����ͷ���ߡ����ϲ�����û�°ɣ���
�������ң�������Ӳ������һ�仰����Ȼ����ò��ᡣ
�͵���������������������Ҳ���Ǽ��ô�ǻ�������ͷ���͵µĸ���������£���ȴ��һ��������ࡣ�͵����»��ˣ�ʵָ���ҵ�һ���˰���������˻��ǽ����Ȼ��������Ǵ˿̹㳡�Ͽտյ�����
����Ų�����ӣ�����������������������ҵ�������̣��ɶ���ˡ���
�������Ǽ�����å�ɵġ������Ⲣ������˵���Ҷ�������ӱ���̣���������е�ʹ�ġ���
�����Ǵ�ʹ�ݵ��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