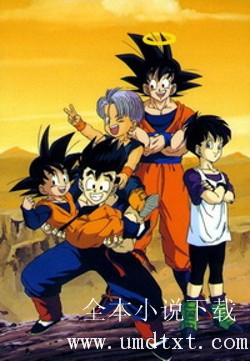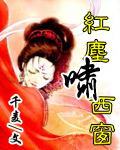西窗烛话-第1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道要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了,结果在长安街上呆呆的站了一天,都听得见天安门广场的“万岁”声,就是没有挪到那里去。
但我们还是见到了毛主席。那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的下午,我们还是在东长安街呆呆的等待。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有点太阳,长安街上人山人海,随着街旁高音喇叭里响起庄严的《东方红》乐曲,我们一起向空旷的街心拥去,而两边是解放军用粗壮的胳膊组成的警戒线。
一长溜吉普车鱼贯驶来,我在阳光里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魁梧的站在吉普车上,一身戎装,满面红光,挺神气的向浪潮似的人群招手致意,车行的很快,就在那一瞬间,我还是看见了最高统帅的嘴角露出笑意,眼神有些疲惫。我在一个新买的日记本上的第一页写道;“1966年10月11日下午,我在北京东长安街上见到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当天晚上,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就从崇文门接待站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是被一帮南方的学生鼓吹着,糊里糊涂的在北京站登上一辆南下的红卫兵专列的。当车在天津站暂时停靠时,主席接见的**仍然在激荡着我们。我们还得意的向另一列进京的红卫兵专列上挤的满满的学生大喊大叫;“主席不再接见了”。
史料记载,“1966年10月10日上午,6000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在天安门上;10月11日下午2点30分,毛主席乘车检阅。是为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发表‘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最新指示。”
时隔二十多年的一年夏天,假借出差的名义,携妻儿又一次来到了北京。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季,儿子还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妻子也还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那时的竹器厂已经由我主管销售和采购,所以我就有了不小的权利,也可以用公款游山玩水了,当然不能说是带着妻儿,也不能说是到北京。
又一次从北京站出来,一辆如今载着老外逛胡同的那种人力三轮车把我们拖到珠市口。一条僻静的胡同,一个僻静的小院,一个凉爽的单间,旅社里有一个公用浴室,抽的是井水,沁凉的,劳累一天回来,冲个凉水澡,再惬意不过了,买来一堆水果,用井水一浸,好吃的滋味如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在北京尽情的玩耍,参加一日游,登上八达岭长城,大声朗读“不到长城非好汉”;和人流一起钻到地下宫殿,看十三陵中的定陵的地宫;天还没亮就起床,一溜小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晨光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万众齐唱“前进,前进,前进进”;妻子领着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我带着儿子步入人民大会堂,一家三口在毛主席纪念堂里向这位人民大救星致以崇高的敬意……
还记得,故宫那雄伟壮丽的宫殿楼阁之中曾留下我们游览的身影,北海公园的白塔边曾记录过妻子的笑脸,颐和园万寿山的佛香阁上曾摇动过儿子细嫩的胳膊,香山长长的下山甬道上曾响起过我们全家人爽朗的笑声;还记得,天坛那天圆地方的祈年殿,利用声学原理的回音壁和三音石;当时轰动一时的所谓根据《红楼梦》的描绘而新建的北京大观院里的幽幽庭院;中山公园里那苍劲的古柏,铺有五色土的社稷坛;悠闲的在北京动物园里看熊猫,还有河马,犀牛;好奇的望着有着巨大弥勒佛立像的大佛楼,由此知道了雍和宫后来成了一座喇嘛庙;在军事博物馆那些抗美援朝的战机面前,在珍宝岛缴获的俄制坦克面前,我们流连忘返……
我们成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穿行,乘着地铁,公汽四处奔波,用眼睛观看,用嘴巴品尝,用照相机记录。从东四到西四,从东单到西单,从大栅栏到王府井,逛了不少街景,吃了不少北京土产,果脯,烤鸭,啤酒,最感兴趣的是煎饼果子,一个鸡蛋向平底锅里一敲,手中拿一铁铲一旋,裹上一根油条,挺有味道的;还有北京的水蜜桃,个大,水多,甜的舒服,去的时候,也许是大上市的当头,又便宜又甜,我们也就大吃特吃了……
按照我的计划,我们还应该去避暑山庄和北戴河,妻子却说假期不够了,只得作罢,恐怕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最为灿烂的就是儿子倚在长城边的笑脸,一副墨镜,身后是万里关堑,有些兴奋,无忧无虑,天真浪漫。
六六大顺 2.龙盘虎踞今胜昔
算起来,我前后到过三次南京。
还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十月,初秋,我从北京就开始乘坐的那趟红卫兵专列走走停停,终于在某个晚上到达了浦口车站,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修建,京广线依旧有铁路用轮渡连接京浦线和沪宁线。那个晚上的情景就是到了今日,也犹如昨夜,江水里晃动着粼粼灯光的倒影,隔岸相望的南京城灯火辉煌,耳边传来轮船与火车的汽笛,或低沉或高亢,在夜晚听得那么真切……
我是胡里胡涂跟着一大帮素未谋面的红卫兵涌出车厢,涌出车站的,而那趟车的终点站是上海,我就这样第一次与上海失之交臂。后来发生过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知道那是的南京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将我们送过了长江,把我们安排在鼓楼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依然是地铺,稻草,解放军,一日三餐。后来我还曾努力回忆过,却只是记得那所学校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小巷的地面铺着鹅卵石,清晨起来,巷道里湿漉漉的,而南京城里像这样幽静的小巷何止万千?
到过首都北京,见到毛主席,自是每一个参加大串联的学生的最大愿望,实现了这一个夙愿以后,一切都变得平淡许多。我是想随便到上海玩,却误在浦口下了车,于是就有了我与南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住了几天,不记得了;去过那些地方,大多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南京街头那绿荫如盖的街道树,典型的江南生活,还有雨花台烈士陵园。之后,我就和其他人一道被塞进一艘用拖轮拖着的两艘货驳的冰冷的货舱里,慢吞吞的,冒着黑烟,顺江而上,走了好几天,一直到武汉。
第二次来是和当时厂里的陈师傅买舟去上海,假借出差之名,偷偷的从武汉登上了一艘快船,南京只是停了几个小时,我们两个人靠在船舷上,抽着烟,悠闲的望着南京港的码头上忙忙碌碌的工人,还有在我们身边挤来挤去的乘客,那是一个阴天,江面上雾气很浓,有一艘美国人援助国民党,最后到了共产党手了的登陆艇笨重的驶过。
第三次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或者是九十年代初,我们一家三口从武汉买舟东下,就到了南京。我们住在离南京港不远的一家旅馆里,那是一栋庄严的,却也陈旧了的大楼里的旅馆,高高的,透过窗棂能看见对面人家美丽的窗帘,窗外晾晒的衣物以及在屋里走动的人影,还能俯视楼下街道上无声驶过的车辆。
从我们住的旅馆出来,经过几个路口,就可以看见一个街心广场上耸立着的一尊塑像,犹如一艘乘风破浪前进的帆船。这是渡江胜利纪念碑。每每乘车经过这里,总能想起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能想起“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丽场面。我突然想起曹雪芹,《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石头城,于是就兴致勃勃的沿着江边寻觅了好久,一无所获,也问过不少南京人,依然是一无所获。
我们还是先去的雨花台,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烈士陵园,青松翠柏,曲径通幽,有号称全国最大的烈士雕塑群像,高耸入云的的纪念碑,装严肃穆的陈列馆,这么些年过去,换了人间,只是恽代英,邓中夏等人留下的豪言壮语仍然叫人肃然起敬。妻儿感兴趣的是那些混杂在泥土里的雨花石,已经比我印象中稀少多了,路边有人摆摊叫卖,妻儿却持意要自己捡,买了一个铁盒装的薄荷糖,糖吃完了,雨花石放进去了。
我们去过中山陵,乘车从市区出发,一路绿荫如盖,梧桐高耸,加之是早上,有些微微晨风,很舒服的。走过孙中山手书的“博爱”牌坊,穿神道,到“天下为公”的陵门,碑亭里“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石碑上金字闪闪发光,,登上石级,就是孙中山的坟墓了,祭室为立像,墓室为卧像,尸体今在否,谁也不知道。但蒋介石为自己选定墓址的“正气亭”游人不断,想想这个门徒也够孝顺的,邓小平之流连面子都不要了,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正是如此。
我们在秦淮河边流连忘返,还是先进的夫子庙,孔庙,学宫,贡院到处都是虔诚的进香者,我们也不能脱俗,向孔夫子祈祷保佑我们的儿子学业进步,高中榜首。儿子却对人潮涌动的店铺很感兴趣,钻进钻出,累人的很,就随便把他拉进一个快餐店里,胡乱点了些沙拉,俄罗斯甜汤,还有意大利通心粉,目的还是歇歇脚。等到再回到秦淮河畔,望着对岸高大粉壁上的“秦淮人家”,迈过文德桥,走不多远就是乌衣巷。板壁房,条石路面,悠闲的人群,妻子不感兴趣,儿子年龄还小,只有我在拼命的回想刘禹锡那首脍炙人口的名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为中华门里瓮城中的藏兵洞的巨大规模而惊讶不已,登上城墙,野草萋萋,视野开阔,还有彩旗飘飘;我们在长江路上的“总统府”转来转去,这里先是太平天国天王府,池塘的石舫据说是洪秀全经常逗留的地方,后来是国民政府的总统府,孙中山,蒋介石的声音曾在这里回响;我们从鼓楼边擦身而过,在新街口仰望没什么特色的,高高的金陵饭店;我们从玄武门进入玄武湖公园,逛了逛樱州和梁州,感觉除了一些土丘上竖立的树丛,就是一个大游艺场。乘快艇在湖中疾驶,船头浪花四溅,船尾一道白花花的水纹;出来就是南京火车站,乘车过中央门立交桥,就到了江边。
我们没去莫愁湖,因为行程匆匆,我们也没去南京长江大桥,因为当我们乘船到上海去的时候,轮船在夕阳的映照下,正庄严而幸福的穿过大桥的桥墩,而儿子也正津津有味的啃着南京的盐水鸭……
六六大顺 3.十里洋场大上海
有幸找到一张当年长航客运南京港的时刻价位表。表上显示,南京港18点15分开船,第二天清晨6点10分到南通,中午12点到上海,四等舱船票票价是8。30元。
中国人把长江上游称作金沙江,然后是川江,荆江,一致认为过了九江就是扬子江了。我却认为只有过了南京才能真正称作是扬子江。江面变得宽阔,宽阔到两岸的岸线都显得飘渺起来;江水变得浩瀚,浪花一直撞击着船身。宜昌那刚刚冲出西陵峡的狭窄江面与这里相比,才懂得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远远望去,岸畔有摇曳的芦苇,似乎还有成片的柳林,一艘喷着浓烟的拖轮从我们船边吃力的驶过,后面拖着长长的、数量惊人的货驳,船尾飘着国旗,重载的船舷几乎快和粼粼金波的江面零距离接触。
我到过两次上海,第一次是假借出差之名与竹器厂的浙江来的篾匠陈师傅一起去的。那年风传上海流行甲肝,闹得人心惶惶,也是我们有些忐忑不安,在武汉市还犹豫过,最后还是好奇战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