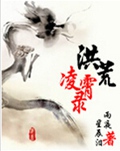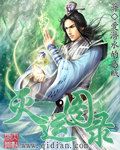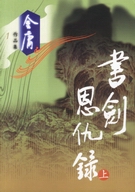近思录-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己,善则唯恐不归于今,积此诚意,岂有不动得人。”
问:“人于议论,多欲直己,无含容之气,是气不平否?”曰:“固是气不
平,亦是量狭。人量随识长,亦有人识高而量不长者,是识实未至也。大凡别事
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江河
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时而满,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
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资也。天资有量须有限,
大抵六尺之躯,力量只如此,虽欲不满,不可得也。如邓艾,位三公,年七十,
处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动了。谢安闻谢玄破苻坚,对客围棋,报至不喜,
及归,折屐齿,强终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后益恭谨者,只益恭谨便是动了,虽与
放肆者不同,其为酒所动一也。又如贵公子,位益高,益卑谦,只卑谦便是动了,
虽与骄傲者不同,其为位所动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待勉强而成。
今人有所见卑下者,无他,亦是识量不足也。”
人才有意于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选,其子弟系磨勘,皆不为理,此乃
是私心。人多言古时用直,不避嫌得,后世用此不得。自是无人,岂是无时?
(因言少师典举、明道荐才事。)
君实尝问先生云:“欲除一人给事中,谁可为者?”先生曰:“初若泛论人
才却可,今既如此,颐虽有其人,何可言?”君实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
又何害?”先生终不言。
先生云:韩持国服义,最不可得。一日,颐与持国、范夷叟泛舟于颍昌西湖,
须臾,客将云:“有一官员上书谒见大资。”颐将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
颐云:“大资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来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为
正叔太执,求荐章,常事也。”颐云:“不然,只为曾有不求者不与,来求者与
之,遂致人如此。”持国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职,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转运司状,颐不曾
签。国子监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状,岂有台省倒申外司
之理?只为从前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体,直得恁地。须看圣人欲正名处,见
得道名不正时,便至礼乐不兴,是自然住不得。
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思虑当在事外。
圣人之责人也常缓,便见只欲事正,无显人过恶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产一事不得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为者,
患人不为耳。
明道先生作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常曰:“颢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见人论前辈之短,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
刘安礼云:王荆公执政,议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尝被旨赴中堂
议事,荆公方怒言者,厉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议,愿公平
气以听。”荆公为之愧屈。
刘安礼问临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输其情。”问御吏,曰:“正己以
格物。”
横渠先生曰: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
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
《坎》“维心亨”,故“行有尚”。外虽积险,苟处之心亨不疑,则虽难必
济,而“往有功也”。今水临万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复凝滞之。在前惟知有义
理而已,则复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于其所难者则惰,其异俗者虽易而羞缩。惟心宏,则不
顾人之非笑,所趋义理耳,视天下莫能移其道;然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
者义理不胜惰与羞缩之病,消则有长,不消则病常在,意思龌龊,无由作事。在
古气节之士,冒死以有为,于义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况吾于义理已明,
何为不为?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时,力未能动,然至诚在于蹢
躅,得伸则伸矣。如李德裕处置阉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于志不忘逞,照察
少不至,则失其几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数,己亦了此文义,二
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忧,则不敢惰,
四益也。
卷十一 教学之道(凡二十一条)
濂溪先生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
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
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
其中而止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
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
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说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
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
《观》之上九曰:“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传》曰:君子虽不在位,然以人观其德,用为仪法,故当自慎省,观其所生,
常不失于君子,则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
也。
圣人之道如天然,与众人之识甚殊邈也。门人弟子既亲炙,而后益知其高远。
既若不可以及,则趋望之心怠矣,故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临丧,不敢不
勉,君子之常行。不困于酒,尤其近也。而以己处之者,不独使夫资之下者勉思
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明道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
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
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
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民、治
兵、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
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
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今朝夕歌之,
似当有助。
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
语学者以所见未到之理,不惟所闻不深彻,反将理低看了。
舞射便见人诚。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
自“幼子常视毋诳”以上,便是教以圣人事。
先传后倦,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是先传
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伊川先生曰:说书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学者须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
之自得。今一日说尽,只是教得薄。至如汉时说下帷讲诵,犹未必说书。
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
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在学之养,若士大夫之子,则不虑
无养;虽庶人之子,既入学,则亦必有养。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
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
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
只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人有养,便方定志于学。)
天下有多少才!只为道不明于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如今人怎生会得?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巷
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
怎生责得学者,是不得兴于《诗》也。古礼既废,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
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
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孔于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
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学者须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初学者,
须是且为他说,不然,非独他不晓,亦止人好问之心也。
横渠先生曰:“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仁之至也,爱道之极也。己不勉明,
则人无从倡,道无从弘,教无从成矣。
《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人未安之,
又进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节目。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
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圣人之明,
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馀地,无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为,但以其不
由于诚,则不尽其材。若曰勉率而为之,则岂有由诚哉?
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
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
君心,至于朋游学者之际,彼虽议论异同,未欲深较。惟整理其心,使归之正,
岂小补哉!
卷十二 改过及人心疵病(凡三十三条)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
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德逾于禄,则虽盛而非满。自古隆盛,
未有不失道而丧败者也。
人之于豫乐,心悦之,故迟迟,遂至于耽恋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
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终日,故贞正而吉也。处豫不可安且久也,
久则溺矣。如二可谓见几而作者也。盖中正,故其守坚,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为多。
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则骄侈生,乐舒肆则
纲纪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乱之至也。
《复》之六三,以阴躁处动之极,复之频数而不能固者也。复贵安固,频复
频失,不安于复也。复善而屡失,危之道也。圣人开迁善之道,与其复而危其屡
失,故云“厉无咎”。不可以频失而戒其复也,频失则为危,屡复何咎?过在失
而不在复也。(刘质夫曰:频复不已,送至迷复。)
睽极则咈戾而难合,刚极则躁暴而不详,明极则过察而多疑。《睽》之上
九,有六三之正应,实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虽有亲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