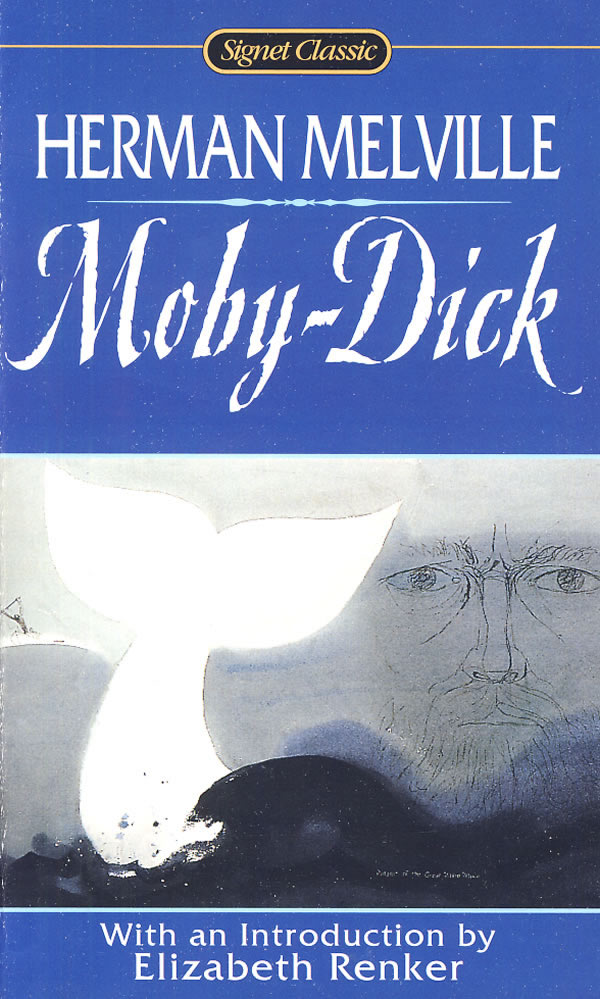白鲸-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嘿,你,你想干什么?你那样干会弄死他的!懂吗?”
“他在讲什么?”
魁魁格不紧不慢地回过头来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小伙子弄死?”
我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个哆哆嗦嗦的小伙子。
“什么?弄死?不,不,不,他,太小了,小小的鱼!魁魁格不杀小鱼,魁魁格杀的是大鲸鱼!”
魁魁格蔑视地说。
“好了,你这个野东西!再捣乱我就弄死你,小心点!”
船长的话还没说完,海上便吹来一阵狂风,主帆离了杠,帆杠飞快地左转几圈、右转几圈。那个毛头小伙子一下子被扫到了海里!
大家慌做一团,有的往舱里奔,有的伸手想抓住帆杠却又怕那东西力量太大把自己也带到海里。
帆杠飞转着,以一股不可阻挡的疯狂劲儿横扫着一切,就像一条被激怒的巨鲸的下颚。
人们围着它,束手无策。
魁魁格灵巧地匍匐到帆杠的下面,一伸手拽过一条绳子来,把一头系在舷墙上,另一头挽了个扣,在帆杠又一次扫过他的头顶时,他迅速将绳子扣抛出去,不偏不斜正好套住了帆杠!
一看套住了帆杠,魁魁格手里便用上了劲儿,帆杠乖乖地停住了。
大家悬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一拥而上,收拾起残局来。
魁魁格从帆杠下面坐起来,甩掉了上衣,走到船的一侧,一个漂亮的弧线形的人水动作,跳入了大海。
波涛之中,他的头顶时隐时现,显然他在找那个落水的小伙子。
三四分钟以后,他还是一无所获。
猛的一下,魁魁格又冒出了水面,换了口气,瞅准方向,又扎了下去。
几分钟以后,他又冒出来了。一只手划着水,一只手拽着那一动不动的小伙子。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两个人拉上了船。
人们称赞魁魁格的英雄行为,船长还向他道了歉,那小伙子也慢慢地缓过气来。
魁魁格没有理会人们的赞誉,他用了些淡水洗净身子,穿上衣服,靠舷墙坐了下来,点上他的烟斗斧,散淡地看着周围的人们。
他的目光是柔和的,似乎在说:
“这没什么,我们野人就应该这么帮助你们文明人!谁让咱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呢。”
14.南塔开特
一路无话,我们安抵南塔开特。
你可以找一张地图,在上面找一找,看看南塔开特在哪儿。
是的,它远离大陆,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山丘,一片沙滩而已。
有人开玩笑说,南塔开特人要想种点杂草也得种在沙滩上,因为这里寸草不生;还有人说他们从加拿大运来了野草;为了堵住一个漏油的桶,必须远涉重洋才能买回那堵洞用的木塞;这儿的人都在门前种上几棵蘑菇,为的是夏天乘凉;还说这里有一叶草即可称绿洲,三叶草就可以叫草原了;说这里人家的椅子上、桌子上经常可以看到粘上去的小贝壳,就像海边的乌龟身上粘着的贝壳似的。
所有这些不无善意的调侃,都是在极言南塔开特的弹丸之大和寸草不生。
最早定居于这块不毛之地的是红种人,关于此,还有一段传说呢。
说是很早很早以前,在新英格兰的海岸上,一只鹰突然冲了下来,叼走了一个印第安婴儿。
婴儿的父母悲痛欲绝地看着老鹰叼着孩子消失在大海上,他们毫不犹豫地划起独木舟追了上去。
经过千难万险,他们追到了这个岛上。在岛上他们发现了那个婴儿的一小堆儿白骨!
此后,这一对印第安人夫妇就居住在了这个小岛上,他们永远也不离开自己那化成白骨的孩子了。
他们就是南塔开特人的祖先。
祖先有着这样的经历,后代出海打鱼以海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们先是在海滩上捕蟹捉蛤,在浅水区拉网捕鱼,然后划上小艇到深海区作业,后来造了大船,开始了大洋上的巡弋。
他们一年四季漂泊在海上,同那些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巨大水兽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们世代征战,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到处都成了他们征服水下巨兽的战场。噢,随便你美国把墨西哥画入德克萨斯州、把古巴送给加拿大、把印度吞入英国吧,在这个星球上,有三分之二是南塔开特人的。
广阔的海洋都属于南塔开特人!别国的水手只不过拥有海上通行权;商船是桥梁的延伸;兵舰是浮动的炮台;甚至海盗也只是劫掠海面上的船只,绝无本事攻占海底世界。
只有南塔开特人是住在海上,海洋是他们的农场,他们反复耕作与收获,他们以海为家,他们的生活与事业都在海里。
他们常年栖息于海上,对陆地感到十分陌生,偶尔登上大陆,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就要远离大陆,他们要躺到大海的怀抱里,让海象群和鲸群从身下掠过才睡得香甜安稳。
15.鳘鱼与蛤蜊
暮色之中,“摩斯号”靠了岸。
先找地方住下吧。鲸鱼客店的老板科芬给我们介绍了他表弟荷西亚·胡赛开的客店,说他的客店在南塔开特属第一流,而且他的客店特别以杂烩做得好而闻名遐迩!
他表弟的客店叫炼锅客店。
然而,看来这家一流的客店并不在繁华之地,左拐右拐,这儿问那儿问,我们俩曲曲折折地走了很久,才来到这看样子不会再错了的地方。
一座陈年旧宅门前,竖着一杆桅杆,横木上一边一个木锅,悬挂在空中。这与绞刑架倒是别无二致了。
噢,我在那边住鲸鱼客店,碰见一个叫棺材的老板;我在这儿住炼锅客店,又碰到了绞刑架!这可不是什么吉兆。
直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黄袍子的女人,我才从这阵心虚之中缓过神儿来。这个一脸雀斑的女人所以吸引了我,是因为她正破口大骂,骂一个穿紫衣服的男人。
“滚,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门檐上一盏昏暗的小灯,像一只受了伤的眼睛,瞪着这快嘴快舌的女人。说完刚才这句话,她的咒骂似乎告了一个段落。
“走吧,魁魁格,这肯定是胡赛太太。”
我赶紧抓这个空儿说。
我的猜测完全正确,这一位正是在胡赛先生不在家期间全权处理客店事务的胡赛太太。
她听说我们要住店,就暂时停止了叫骂,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让我们坐在一张杯盘狼藉的桌子边儿。然后猛地扭回头来,问:
“鳘鱼还是蛤蜊?”
“什么,太太?”
“鳘还是蛤蜊?”
“蛤蜊?那种又冷又粘的东西可以当晚饭吃吗?鳘鱼是什么样的?”
胡赛太太似乎并没太在意我说什么,她恍惚听见我先说了个“蛤蜊”,便向里屋大喊了一声:“两个人一只蛤蜊。”
看样子她很急,她急着去骂那个穿紫衣服的男人,所以这么喊了一声以后人就不见了。
“噢,魁魁格,一只蛤蜊,够吃吗?”
我的疑虑很快就被厨房里飘过来的浓郁的香气打消了。等那热腾腾的“杂烩蛤蜊”端上来时,我们俩心中的愉快是无以言表的。
这是用那种比榛子人不了多少的蛤蜊做出来的东西,掺着些碎面包和细细的咸肉条儿,又放了够量的牛油、胡椒和盐!
面对如此美妙的食物,我们俩一句话也顾不上说,三下五除二就一扫而光了。
我们身子向椅背上一靠,显然意犹未尽。我学着刚才胡赛太太的口气,向后面喊了一声:
“鳘鱼!”
一会儿,鳘鱼就端上来了。
这鳘鱼杂烩的味道与蛤蜊杂烩略有区别,不过,人们一吃起来就忍不住狼吞虎咽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我用勺子在碗里舀了舀,对我的伙计说:
“哈,魁魁格,你看,有一条活鳝鱼!你的标枪呢?”
我们俩都笑了。
炼锅客店可以说到处都充满了鱼的味道。厨房的锅里永远在煮着鱼杂烩,早中晚一天三顿,顿顿杂烩,吃得人担心身上会戳出鱼骨头来。
客店里到处都是蛤蜊壳,胡赛太太的项链是用鳘鱼脊骨做成的,胡赛先生的账本也是用上好的鳘鱼皮制成的,就连牛奶里也有股鱼味儿!
这就有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直到早晨散步时我看见奶牛在吃鱼骨头时,心中才豁然。那奶牛不仅在吃鱼骨头,四个脚上还套着四个鳘鱼头,像拖鞋似的。
晚饭后胡赛太太给了我们一盏灯,指点了去客房的路。我们刚要走,胡赛太太一伸手,拦住了魁魁格。
“不能带标枪!”
“为什么?每个真正的捕鲸者都是和标枪共枕同眠的!”
我辩解着。
“这很危险!自从那位可怜的小伙子斯替格死在客房里以后,我就不准客人带标枪进房了。”
“他的标枪插入了后腰!”
“唉,他出海四年半,只带回三桶鱼杂碎来。”
“好了,魁魁格先生,放心交给我吧,明天一早我就给你。”
“对了,明天早晨吃什么,鳘鱼还是蛤蜊?”
“都要!再加两条熏青鱼,换换味儿。”
我说。
16.“裴廓德号”
在床上,我们开始商量具体的出海计划。
让我吃惊的是,魁魁格已经有了些不可更改的“主意”。这主意来自于他身上的那个小木偶,它叫“约约”。
约约告诉他,我们俩不能一起到码头上去找捕鲸船,这个任务应由我以实玛利一个人去完成,它约的暗中相助云云。
它还暗示,已经在岸边为我们选好了船,就是那艘我最终一定会挑定的船;而且,我会抛开魁魁格,一个人先去上船做水手!
魁魁格非常相信他身上的这个木偶,凡事都要向它请示,它的任何一点表示,魁魁格都会像听到圣旨一样去执行,尽管有时候它也许是出之于善良的本心恰恰弄出些相悖的事来。
今天这事我就有些看法,魁魁格有经验,应该让他去挑一艘船;可魁魁格一意孤行,雷打不动地让我去。
没有办法,第二天,留下魁魁格和他的约约在屋里鼓捣些什么仪式,我一个人去了码头。
随便问了问,得知近期内启航、航程三年的船有三条:“魔闸号”、“美味号”、“裴廓德号”。
“魔闸”不知典从何出,“裴廓德”却略知一二,这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一个已被斩尽杀绝的种族的名称。
我在三条船上转了转,最后决定上“裴廓德号”。
船有多种,你也许见过那些横帆船、舢版、帆桨两用船……可我相信,像“裴廓德号”这样的老船,你肯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是一条闯荡过世界各个大洋大海的老船,日久天长的风吹日晒、雨打浪激使它浑身的颜色墨一般黑,就像那些在埃及和西伯利亚身经百战的法国兵。
斑驳的船头,仿佛有一副很威风的大胡子,而那来自日本海岸的桅杆——因为原来的桅杆就是在日本海岸被暴风雨摧折的——高大挺直,似乎再不会被摧折了。船的甲板有的地方已经断裂了,又小心地用木板钉在了一起,好像有千万人践踏而形成的凹痕则是无法修补的。
船长法勒,原来在船上当大副,后来去另一条船上当了船长,如今还是“裴廓德号”的大股东。
法勒当大副时,在船体的装饰上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又是嵌又是镶,把整个船体弄得像一位脖子上套着沉重的象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似的。
这条船的装饰物都是几十年以来它的战利品,就像吃人部落的战士,用他杀死的敌人的骨头做饰物。
船的舷墙像大鲸鱼的下颚,而舷墙上用来拴绳子的木桩确确实实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