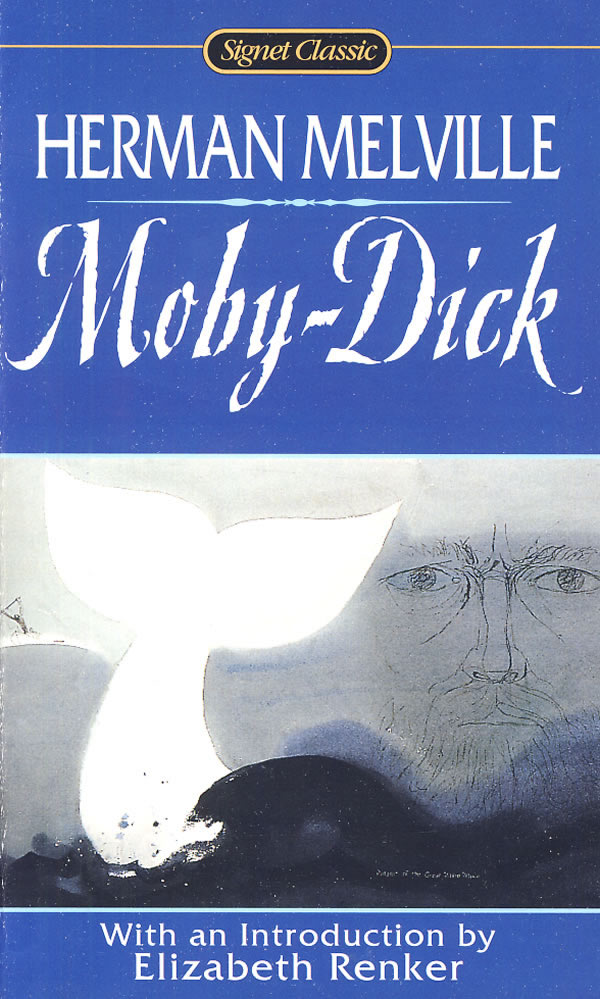白鲸-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拐了个弯儿,他也跟着拐了过来,他这无疑是在跟踪我们!不过,他要干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闪烁其辞的话、“裴廓德号”、亚哈船长以及他失去的那条腿、我们签的合同……我心中将这些翻来覆去地想了个遍,还是理不出头绪来。
为了判定一下这个以利亚是不是真的在跟踪我们,我拉着魁魁格走到了路边,看着后面走过来的他。
他却旁若无人地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们俩。
20.慈善姑妈
数日之后,“裴廓德号”上呈现出一片忙碌景象:帆布、绳索等一应需用之物都陆续搬了上来。
法勒船长可能从来也没离开过船,他在监视着船上的所有准备工作。到码头上采购的事就由比勒达负责了。他们和那些被雇来干活儿的人一样,每天都一直工作到很晚。
在我们签约以后的第二天,岸上各个旅店便都接到了通知,让“裴廓德号”的水手们把行李送到船上去,因为开船的日期是不定的,也许明天就走。
我和魁魁格把行李送上船以后,又返回岸上的旅店,我们计划开船时再上船。不过,即使他们通知你要开船,你上了船,船却要好几天以后才能开。因为船上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临时想起来就又得延期开船。
捕鲸是一项远离尘世的事业,一去数年,锅碗瓢盆、食品药品以及衣物都要拿上够三年用的。
而且,捕鲸船出海作业的危险性最大,小船、圆木、绳索、标枪都要有备用的,连船长也有一位后备的。
负责准备这些东西的,是比勒达船长的妹妹,一个小老太婆。她是个很干练的人,仿佛永远不知疲倦地往船上搬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牛肉、面包、淡水、铁桶、燃料、钳子、餐巾、刃叉、锤剪……
这是一位以慈悲为怀的老人,她以她的善心和体贴入微的行动,关怀着船上的每一个人:这回她手里拿的是厨房里用的一罐酸菜,下一次她拿着的又是为大副记航海日志而准备的一大扎鹅毛笔,再下一回拿着的则是给得风湿病的人护腰用的法兰绒……
大家都叫她“慈善姑妈”。给人以爱是她一生的生活准则,何况这船上还投着她劳碌一生积攒下来的几十个银元呢!
比勒达和法勒自然也没闲着:比勒达身上带着一个船上需要物的清单,每当一样东西运上船,他都要在清单上相应的位置打个勾儿;法勒则在不停地东游游西看看,看到有什么不顺他的眼的地方,便要咆哮一顿。
我和魁魁格几乎每天都要上船上去一次,问问准备的怎么样了?亚哈船长的健康恢复了吗?他什么时候能上船?我们又什么时候能开船?
法勒和比勒达每次都说准备的差不多了;亚哈船长已经恢复了健康;随时都可能上船,我们随时也都可能开船。
噢,我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了,试想一下,你就要和这条船一起扬帆入海,可以说你的生命在几年之中就完全交给这条船了,可直到现在,你还没见过能主宰这条船的命运的人一面!
人类的疑虑往往是在他已成为局中人时最为强烈,可面对这无奈的局面,他自己却还要自欺欺人地加以掩饰。
我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境地。
最后的通知终于来了,“裴廓德号”明天的某一个时候将准时出发。
21.登船
第二天早晨,我和魁魁格早早地来到了码头上,天刚蒙蒙亮,大概还不到六点钟吧。
“我说魁魁格,前面好像是有几个水手在向咱们的船猛跑吧!”
“我想太阳一出来船可能马上就开,快点吧!”
“且慢!”
一个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一个人的两只手搭在我和魁魁格的肩上,同时他的身子也挤到了我们俩的中间,是以利亚。
“就要上船?”他问。
“你最好把手拿开!”
我一点也不客气地说。
“走开吧!”
魁魁格说。
“你们不是上船吗?”
“我们是上船,这与你有何相干,你不觉着你有点失礼吗?”
“不不,我没有这种感觉。”
以利亚平静地说,同时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们俩。
“好了,以利亚,请让开,我们要走了,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你们要走吗?早饭前就回来吧!”
“真是个疯子!魁魁格,咱们走!”
“嗨!”
我刚走了几步,站在后面的以利亚又吆喝起来。
“别理他,咱们走。”
我招呼着魁魁格。
可是以利亚又悄悄地跟了上来,他拍了拍我们的肩膀,神秘兮兮地说:
“嗨,我说,你们刚才看见有些人一样的东西向船上走去了吗?”
“看见了,有四五个人吧!不过比较模糊。”我耐心地回答了他。
“噢,很模糊,很模糊!好吧,早上好!”
我们加快了脚步,可他又跟了上来,低低地问:
“试试看,你们还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吗?”
“什么影子!”
“好啦,早上好,早上好!”
“不过,我想告诉你们一下,今天霜很重,是吧?不过没关系,咱们是自家人,不用客气。再见!”
“不过,咱们再见得好长时间了,除非是在‘大陪审团’面前……”
他疯疯癫癫地讲了一遍,走了。
我们登上“裴廓德号”时,发现船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舱盖锁着,甲板上有一堆烂绳头,海风掠过,一片凄凉的景象。
灯光从小舱的舱口处射了出来,我们迈步过去,却见一位穿着破烂的老索匠,侧身躺在两口箱子上,睡得正香。
“哎,魁魁格,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些水手哪儿去了呢?”
对于我的问题,魁魁格并不以为然,因为刚才在岸上他压根儿就没看见什么。
“算啦,咱们就守着这个老索匠坐一会儿吧!”
我无奈地说。魁魁格在那老索匠的屁股上按了按,好像在试够不够软。
“噢,这可是个好座位!我按我家乡的方法坐,不会压扁他的脑袋的!”
“行啦,看看,你快把他坐醒了!”
魁魁格挪了挪屁股,坐到了那个人的脑袋边儿上,点上了他的烟斗斧。
我则坐在那人的脚边儿。于是,烟斗斧就跨过那个人的身子,递过来又递过去。
魁魁格告诉我,按他们那儿的习惯,国王和贵族都是坐在那些养得肥肥胖胖的仆人身上的。外出时也是如此,在大树的阴凉下,喊过一个仆人来,让他趴在潮湿的地上,然后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到仆人的背上了。
魁魁格讲着他家乡的故事,不时地从我手里接过烟斗斧去,顺便在那酣睡的人头上晃两下。
“魁魁格,你这是干什么?”
“噢,砍下去很简单!”他是握着烟斗斧在作很自然的想像,这斧子往下一砍,便会人头落地。
烟气越来越多,那梦中的人被熏得咕哝了一句什么,翻了个身,终于坐了起来。
“嗨,你们,你们是谁?”
“水手。船什么时候开?”
“噢,你们是这条船上的水手?船长昨天夜里上了船了,今天就开!”
“船长?亚哈船长?”
“当然,没有别的船长了。”
我刚想继续问下去,甲板上却传来了脚步声。
“听,这是大副斯达巴克,他可是个好人,身强力壮、心地善良。他起床了,我也该干活儿了。”
索匠边说边走上了甲板。
太阳升起来了,船上的人们开始了最后的忙碌,大副、二副、三副指挥着水手们帮着从岸上把最后一批家什运上船来。
船长还是没露面,他在船长室里。
22.起锚
日近中天,船上的工匠们陆续上了岸。
慈善姑姑给船上的二副,她的妹夫斯塔布送来了一顶睡帽,给另一位送上来一本《圣经》,然后坐着捕鲸的小艇上了岸。
“裴廓德号”就要起锚了。
法勒和比勒达从船长室里走了出来,法勒对大副说:
“怎么样了,斯达巴克,亚哈船长刚才说不需要什么东西了,你把大家集合起来吧!”
“好啦,斯达巴克,执行使命吧!”
比勒达帮着腔。
这两位语气强硬、威风凛凛,俨然是船上的最高指挥官。可真正的指挥官——亚哈船长到现在也没露面。
这在普通的商船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船只启航离港用不着船长做什么具体的指挥,那是领港人的事情。他们只要坐在船长室里就可以了,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是这样,在船长室里和自己的亲人做着告别的交谈,直到亲人们坐上小艇和领港人一齐离开大船为止。
“嗨,斯达巴克先生,让他们到船梢儿来,这些狗娘养的!”
法勒船长催促着看样了有点懒懒散散的人。
“拆掉那个破棚子!”
这个命令是同“起锚”一样重要的命令,“裴廓德号”三十年来每次出航都是如此。
“转绞车,起锚!快!快!”
这是第三道命令。
三道命令一下,大家忙碌了起来。
按照惯例,起锚时,船头是领港人的位置。可此刻法勒和比勒达两个人并肩站在那里。他们俩也是这个港上领有执照的领港人,不过他们从不为别的船领港,所以有人怀疑他们所以要做领港人,不过是想为“裴廓德号”节省一笔领港费。
随着绞车的转动,铁锚被缓缓地从水里拉了起来。比勒达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个过程,嘴里哼着一首凄婉的曲子。
水手们也在唱歌,不过不是离别的凄凉之作,更不是圣歌,而是一首关于一个什么港上的姑娘的歌。
法勒现在站在船尾,他没唱歌,他在不停地吼叫,让人担心船还没出港就会让他给骂沉了!
我靠在船舷上,很自然地想歇一歇,可还没回过神儿来,屁股上就挨了重重的一踢!
“混蛋,在商船上你就是这么干活的吗?”
他对着我破口大骂,马上就又扭向了别的水手,不依不饶地吼着。
“使劲绞,笨蛋!”
“绞呵,你,刮荷格,你这个红胡子鬼,绞啊!”
他边说边走,脚落在几乎每个人的屁股上。
在比勒达船长的歌声中,在法勒船长的叫骂声中,“裴廓德号”起了锚,扬了帆,驶上了荒凉的大海。
时值隆冬,圣诞节将至,船舷上的冰栏,像一排大白象牙,在月光中闪着冰冷的光。
海浪滚滚
远离了家乡
绿茸茸的田野
仿佛犹太人心中的圣地
约旦河啊,
奔流不息
比勒达船长凄凉的歌儿显得十分动人,尽管冰冷的海上寒风刺骨,我还是感到了一阵内心中的轻松。
春意朦胧,万物复苏,莺飞草长的幻象出现在我的头脑中,让我沉入无比甜美的憧憬或者说回忆之中。
大海的胸膛辽阔了起来,领港人已无存在的必要了。比勒达和法勒要下船了,一直跟在船后面的小艇靠了上来。
两个人在远离船的最后时刻,依依不舍地在甲板上徘徊,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瞅着这艘投入了他们毕生积累的财富的大船,他们实在不忍离开。
比勒达一会儿下到甲板下面的船长室道别,一会儿又跑到甲板上来不放心地审视一遍所有的设备,一会儿又站到船头上,遥望茫茫无际的大海,然后机械地捡起一根绳子头儿,拴在了桅杆上,继而猛地抓住法勒的手,表情复杂地看着他的伙计。
法勒的态度一向有哲学的味道,不过此刻他的眼中也饱含了泪水。
经过一阵惶惶然的忙碌,两个人逐渐平稳了下来,法勒以一种无比坚定的口气说:
“比勒达,咱们该走了!老朋友,咱说一声再见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