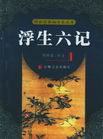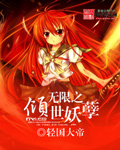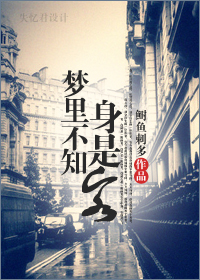梦里浮生之倾国作者:梦里浮生-第1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罪,表示以后将功赎过,清议的苛论也就能平息下去,这个分歧危机便可以度过了。
但刘秉忠始终默不作声,或许并不认为不发援军救房山是战略错误;或许被清议骂得狗血喷头恼羞成怒,实在下不来台认错;又或许他已经干脆下定反叛的决心,不屑于再分辩名声,要拿武力来解决一切?种种可能,使众人猜测不已,并随着刘氏拒绝发言的缄默,越发忐忑不安。
在这样的惶恐气氛之中,日子不知不觉滑到了正月底,京中流言满天飞,甚至有人开始言之凿凿的说刘太师当真打算叛乱,连旗号都制好了,只待选个日子动手将文官们全部绑架,劫持太后改朝换代。连殷螭也以此为借口,整兵控制住了南城外门,不再接受刘氏调遣,刘氏也同样扼住了内城三门,拒绝与殷军往来。城外蛮族逼近,城中有内乱分裂可能,市民们想跑都没法跑,不禁哀声一片,只催促大臣们赶紧想个办法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太学生们自然也要做努力,由国子监祭酒带头去拜访闲住在家的前首辅刘崇义,希望他从大局着眼,劝说兄长侄子们不要叛乱,忠心为国,抵御外敌。刘崇义在内阁的时候吃够了言官攻讦的苦头,对清议派人士难免保持着戒心,一再称病不见。太学生们便连日堵着他居住的米面胡同请见,闹嚷得四邻不安。同时因为刘崇义的嗣子刘楝也是国子监出身,诸监生同他有同学之谊,想要托他向父亲进言,刘楝未置可否,于是也挨同学们大骂了一通,纷纷表示和他割席绝交。
然而刘楝并非不想挽回自己家族误入歧途的处境,在国子监同学骂过他之后没两日,便有人流传出一份刘楝所写的《上父书》,乃是刘楝对嗣父刘崇义与亲父刘秉忠同时作出诚恳悲痛的劝谏,从刘氏自国朝定鼎以来历代所受国恩写起,分析眼下局势,劝告家族中人,纵使逼于无奈也万万不可行差踏错,遗臭万年!不救皇陵之事,父亲的确有着诸多顾虑,在情势不明之下,不敢贸然出师也是情理之常,并非有意要陷先帝陵寝于敌手,但保住京城虽是至关重要,皇陵失陷却也委实愧对先帝,便自认过错又有何妨?人臣的委屈,难道不能置于国朝体面之下?
《上父书》最后是一段极其悲怆无奈的话:“不孝男楝,亦久受公论之欺,背负盗贼之名,如堕荆棘丛,动辄挂碍,复有何乐?然人之所寄于一世者也,非权非利非名,乃耿耿自明之心矣!为公者庇万民之福祗,为私者敬慎独之诚挚,公焉私矣,其实一也,又何惑哉!伏幸豁然,以悟大是,至望至望!”
刘楝自清和五年壬申乡试夺取状元,被指责有弄权舞弊嫌疑之后,便一直处于舆论的讥评之下,哪怕覆试洗刷清白,哪怕他愤然不再参与会试,自己杜绝仕途之路,也逃不脱权臣子弟仗势夺魁的恶劣名声,连平素最交好的同学徐翰也回避往来,划清界限,心里是何其冤愤?而冤枉他的,却并不是什么恶人,而是“公论”——公众的舆论将他钉上耻辱柱,定性如盗贼,到处都遇到怪异眼光,自己觉得人生直如堕在荆棘丛里一般,动辄得咎,痛苦不堪,因此以这样的比喻来劝说刘秉忠不要因为言论的苛责、个人的委屈,就一怒铤而走险,置大是大非于不顾,将国家、家族、个人,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封《上父书》流传出来的时候,刘秉忠与刘崇义不消说都已经收到了儿子的劝谏,这两个做父亲的有无感想,外人不知,但了解刘楝遭遇的人读到这些话语,却均为这个一直含冤蒙垢的不幸状元扼腕叹息一回,同时舆论对刘氏的压力也无形中改变了一些,从谴责转而为要求——要求他们为国为民负责。
《上父书》乃是私信,却遭泄露,同时给家族带来议论,对父亲名声产生影响,做儿子的刘楝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在书信泄露、满京流传后一日,刘楝便留下“扬父之愆,博己之名,不忠不孝,何以为人子?”的遗书,自缢身亡。
这遗书以血写就,呈到宫中之时,林凤致暨内阁诸大臣都在太后御帘之前,互相传看那业已凝固的血书字迹,都不觉沉默。因为刘秉忠是刘楝的生父,所以血书中的“忠”字是避讳缺笔的,却没有缺末笔而缺了下面“心”字的中间一笔,看在眼里,恍惚让人觉得自己心里也缺了一块,空空荡荡。
刘楝是晚辈,按照“父在,子先死,不得为正葬”的风俗,本不该大操办,但刘楝的《上父书》言辞沉痛,他这一死又是给刘氏家族加以道德的束缚,不使为乱——所以这般怨愤无奈的死,却使京城市民无比叹惋,自发去吊唁的官员和举子挤满了米面胡同,人人都不惜言辞,对刘家丧子之痛表示出诚恳的慰问。
林凤致到刘家吊唁的时候,看见刘崇义业已悲痛得站不直身,由家仆扶住颤巍巍却还要在儿子灵前答礼。刘秉忠也来了,这个腰板挺直性格刚毅的老将,竟也似乎受不住晚年丧子的打击,露出冠沿的双鬓已花白一半,陪在他身边的是长子刘槲和侄子刘栋,都为兄弟服着丧,默然无语。
林凤致想到刘秉忠前几年已经遭受过一次丧子的打击,是次子刘松战死于朝鲜。但那一回刘秉忠何其悲愤交加,怒冲冲在御前破口斥骂主张撤兵害了他儿子的林凤致与前兵部尚书朱光秉,显然是怒盖过了恸;而这回却是连怒气也发作不出来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整个人都已颓然不振。
刘秉忠其实子息众多,妻妾所生的儿子共有九个长大成人,刘楝只是幼子,况且还早早过继给了兄弟为嗣。按殷螭的说法,刘秉忠定然不在意这个体弱好文、不似刘家人的出继儿子,但林凤致却觉得,也许正因为将这个儿子从小就出继给别人,所以做父亲的心里会更怜更疚,因谏父而戕生的刘楝,也会使刘秉忠感到世界崩塌般的剧痛。
所以刘楝以性命呈上的谏言,终究是打进了刘秉忠心里——也同时打进了朝野各方面言论之中。
这样的代价并不轻松,至少林凤致一步一步走向灵前拈香致悼的时候,心情和步伐都是同样沉重的。与他交好的徐氏父子这日也来了,徐照重伤才愈,只是脸色蜡黄的和老朋友打个招呼,徐翰却哭得满脸是泪,心神显然极不安宁,居然在灵前向林凤致忽发质问:“林大人!难道……言论杀人,一至于此?嘉木……何其无辜!”
二十岁年轻人毫无掩饰的悲痛与愤恨,使得林凤致不禁退了一步,一时无语。殷螭正在他身边,于是回了一句嘴:“你还是人家好朋友,不是也照样和他绝交?我看言论逼迫害死刘嘉木的也有你一个——若非你死活不谅解,害人家心灰意冷,他也未必索性自寻短见!”
林凤致觉得这话未免过分,于是轻声劝了一句:“王爷言重了。”但徐翰到底被殷螭这一句话说得苍白了脸,忽然扑地跪倒,握紧双拳,全身只是颤抖,却再也哭不出声。
灵床后孝幔遮住的乃是刘家女眷,刘楝正室未娶而夭,仅有一个妾生的儿子,见到徐翰下跪,里面便也抱着婴儿回礼,刘楝的嗣母嫡母生母都在,又是一片哭声震天。
满堂吊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火盆中纸灰化作白蝴蝶,一片片卷起飘扬,外面是阴沉沉的天,正月最后一日,西来铁骑已自武清抵黄村,即将与南面会合同攻京城。营州右屯卫的守兵快要抵御不住,蓟州不日便要失陷——这样的形势之下,终于以刘楝的死为契机,朝野与刘氏达成了部分和解。
虽然这和解不无缺憾,不无危机,然而在这样情势下,还能有什么值得苛责?世上本无完美事,为国为民为自己,都要以部分的丢弃来换取成就大局。
正如刘楝血书上,缺笔写不完的那个“忠”字。
三之31
战乱的时候,京城中实施宵禁,所以入了夜后街面上除了巡逻士兵,便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影。林凤致这晚没有值宿,却到了天黑才返家,因为心情抑郁,没有乘轿,连随从也先打发回去,自行提灯回家。他未穿官服,所提宫灯却有御赐的标记,巡逻的士兵望见也不加盘问,让他慢慢穿行过警戒严密的大街。正月底的时候,京中积雪已消融,拂面的风却还是那么寒冷,犹如地狱中吹将出来,干燥而凛冽,刮得头面生痛。
绕过灯市大街向东安门方向走的时候,背后有人骑马追了上来,过片刻便驰到身侧,勒了缰绳,笑道:“你今日怎么也一个人了?也学我不戴风帽,仔细头痛。”林凤致嗯了一声,继续自己走。殷螭问道:“要不要上马来,我再送你回去?”林凤致道:“多谢了,我想走一走。”殷螭于是跳下马来,说道:“一个人走多么闷!我陪你。”
他说到做到,果然将马丢给街头巡卒,陪林凤致并肩漫步。过一会便关切一句:“冷不冷?你最近老是不见人影,弄得我好不想念——这么晚一个人回家,危险得紧,你也知道城中奸细没准还在。”林凤致道:“行刺我又无益处,缺了我,朝政一切照常,你又不是不知。”殷螭笑道:“我可不信!这些事明面上都不是你做的,却又哪一桩跟你没干系?叶德明他们那几个,哪有你那么狡猾机变,捣鬼多端。”
说着话转入另一条街道,沿街灯火闪亮,勾勒出一栋形式古怪的建筑,殷螭不觉啊了一声:“怎么走到我家——不,是抢了我家地皮的洋和尚庙来了!小林,你要去拜洋和尚?”林凤致摇头道:“不,我也是随便走走,没想到走到你王府旧址来了。”望着那西洋建筑中透出的灯光,还隐隐有音乐歌唱之声传来,他不禁叹了口气:“泰西先生倒是热心人,一样忧虑京城被破,这几日都在替国朝祈祷。他们教徒唱的那歌曲,叫做什么赞美诗,徐年兄译过几段给我听,大意是天神有灵,垂悯世人——如今这世道多灾多难,也真盼有神灵大发慈悲,垂悯普照!”
殷螭嘀咕:“那还不如去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莫不成西洋来的和尚好念经?”林凤致倒是一笑:“是,或许菩萨更灵验,更慈悲。”他走了两步,又道:“其实我不信佛道,更匡论西洋教派?但是今日徐年兄在刘家同我叹惋,说起他们的教派最是严禁自戕,自杀之人,永远不得升天极乐,要堕地狱——然而人世间忠孝节义,却又有不得不死。”
这句话其实说到了刘楝之死,殷螭一时说不出话来,悄悄伸手过去,在袖底携住了他手,紧紧握牢,林凤致居然也没有挣脱,两人默默无言的路过那西洋传教堂,从灯光笼罩的街面复又走入黑暗,只有林凤致所提宫灯飘忽的亮。
林凤致忽然道:“你知道罢?刘楝那封《上父书》……不是他人泄露,而是他自己流传出去的。”殷螭哦了一声,林凤致轻声道:“那样的文章,写出来就是准备公开的,不公开也无以生效如此——所以嘉木世兄,自从作书谏父的时候,就是决意一死了……”
子不言父过,所以刘楝“扬父之愆”,便须得以死谢罪,才能对得起公论与良心,可是这般道德的绝境,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