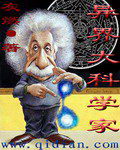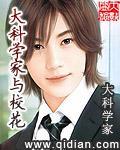哲学科学常识-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物理学的实在问题(3)
不过,这种由自然而然之感而来的“实在感”从来不是判定实在的最终标准。不如说,它是一个起点。正因此,实在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不等同于自然概念。在日常经验世界中,实在的确立反过来也不断调整我们对何为自然的感觉。
在一个平俗的意义上,张三比中国实在:你可以实实在在拥抱张三,但你只能在比喻的意义上拥抱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数字所指的东西不像张三所指的东西那么实在。然而,这里的差别不是张三和中国是否具有指称,也不是这两个词所指称的东西哪个更多实在,――这种说法不过是把我们平俗意义上所说的实在转化成为形而上学的说法,把原本明明白白的话变得无意义或至少意义含混;这里的差别是具体和抽象的差别,或是在讨论哪些概念就理解而言依赖于哪些概念。实数比虚数实在,大概不外是说:我们不掌握实数就无法理解虚数,而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些叫作实数的实体却没有虚数这种实体。我们用称称出了黄瓜的实实在在的分量,我们通过计算得到地球的重量,或氢原子的重量,那也同样是实实在在的分量。
数学通过远程推理达到某些结论,这本身并无伤于这些结论的实在性。麦克斯韦方程描述的内容无法用自然概念充分翻译出来,但它仍然是关于实在的方程。世界的一部分真相只能用一种特定的语言表述出来。如我们在“力、加速度、质量”一节所表明,牛顿的术语并非一般而言更好地揭示了自然的真相,而是适合于让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自然的某种真相。
不过,数学通过远程推理达致的结论的确已经远离了可感可经验的自然世界。它们由于缺乏自然感而缺乏实在感。但这毋宁是说,随着理论离开自然世界越来越远,实在这个概念本身改变了。在数学物理世界里,自然对实在已经没有多少约束力。这使得在物理学中谈论对象的实在性和日常所谓的物体的实在性颇为不同。我刚才提到,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触觉最能印证实在,而验证物理学对象是否实在,触觉很少派上用场。科学理论通常通过观察来验证实在,但如科学概念章所言,在很多情况下,所谓观察也是非常间接的观察。某个理论是否只是假说抑或它揭示了物质实在的结构,其所依的标准和我们通常在看得见、摸得着意义上的实实在在有了很大区别。我们对炮弹确切沿着何种轨迹飞行可以发生种种争论,但炮弹穿过这片田野的上空却不会是争点。然而,如果把电子视作炮弹那样的实体,电子的很多行为就无法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子不具有实在性。不如说,实在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把关于身周物体的实在观念直接套在量子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上。
总体上说,近代科学之所以面对特殊的实在问题,是因为它逐步远离了我们的经验世界。遥远是由论证的数理力量造成的,数学推理可以一环一环达乎遥远的结论而不失真,然而,感性却随着距离减弱。除了检查所采用的数理推论的过程是否正确,用实验结果来验证推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确定它所通达的对象是否实在。而如何判断理论的正当性、判断其结论是否与实验结果相吻合,如上所言,是物理学内部的工作。
哲学…科学是关于实在的认识的专门发展。然而,科学在加深对实在的认识的同时改变了一般的实在观念或真实观念。就好像现代专业体育的发展改变了体育的观念,与一般强身健体的原初目的已经相去很远。关于物理学实在性的争论,大一半由此而来。
既然实在这个概念在应用于科学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干吗还在物理学里谈论实在呢?我们另选一个词何如?这是关于概念选择的一般问题,须另加讨论。我一般认为,换用一个新概念并不会使问题消失,反倒掩盖了观念的延续发展,使我们更难看清实质问题所在。物理学的确仍然面对实在问题或曰真实问题。在物理学内部,一个对象或一个理论是否真实始终是可争论的。在物理学和常识之间,关于谁是实在或谁是首要的实在的争论也是有意义的,是有重大意义的。当然,如果我们决定不采用实在不实在这些语词来言说物理学对象,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说物理学对象是非实在的了。
从一开始,哲人就探求实在。他要找到不含杂质的的实在。多少世纪以后,通过科学,他终于找到了纯粹的实在,它们原来是些远离实在的公式。这时,他也许幡然醒悟,并没有不含杂质的终极实在,并没有不可错的真理,那个混杂着虚幻和虚伪的世界才是最实在的,我们必须连同虚幻和虚伪,必须针对虚幻和虚伪,才谈得到真实。
哲学的终结?(1)
常识、哲学、科学
哲学的终结?
哲学…科学的目标是为世界提供理性的整体解释。亚里士多德体系是哲学…科学的最伟大的典范。近代科学延续了这一事业。但它以根本相异的方式来从事这一事业。现在看来,至少就自然界的结构和机制而言,科学提供的才是正确的解释。地球不处在宇宙的中心,恒星不镶嵌在天球上,倒是组成各种星系,它们有生有灭。水不是基本元素,也没有它自然的位置,水往低处流,是因为地心的吸引力,在宇宙飞船上飞四处横飞。
所以说,科学既是哲学…科学的继承者,又是哲学的“终结者”。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口气谈到这一点。海德格尔说:科学的发展定型“看似哲学的单纯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的完成。”哲学的终结意味着科学技术世界以及适应于这一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哲学的终结意指:基于西欧思想的世界文明的开始。”西文的telos或Ende,本来就有终结和目标的双重含义。阿多诺认为,一方面,哲学把科学当作自己的榜样,另一方面,哲学和科学,从亚里士多德起,就隐含着矛盾,而到笛卡尔那里,这一矛盾凸显出来。只要存在着宇宙论方面的思辨,科学就不断地剥夺形而上学要据为己有的东西。哲学有一种向科学转化的倾向,然而,“哲学变形为科学,……这并不是可庆的成熟,仿佛思想蜕去了它身上的稚气,蜕去了主观的意愿和设想。倒不如说,这一变形也葬送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
不管我们怎样描述或估价这一转变,下面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在实证科学以它的方式提供了世界的整体图景之后,哲学何为?
按照笛卡尔的看法,形而上学是学问体系的根基,各门科学都是从这个根基生长起来的。笛卡尔并不是说,从历史看,近代科学继承了哲学…科学的事业。他是说,哲学为科学提供了原理基础,不妨说,科学大厦尽可以高耸入云,但科学大厦的基础是哲学提供的。本书想表明,这个主张实在很可疑。近代科学毋宁是在不断摆脱、反对形而上学原理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如普特南所断论,科学一直反对形而上学。到今天,这一点应当十分清楚,尽管还有个别弄哲学的人仍然妄想着为科学奠基。有谁能相信连科学常识都不甚了了的人能为科学奠基呢?诚然,西方的科学家比中国的科学家富有哲学思辨的兴趣,差不多所有大科学家都熟悉柏拉图和康德。但这恐怕不能作为证据表明哲学是科学理论的基础。
不说提供基础吧,说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只怕科学家不买账。温伯格说:“好的科学哲学是对历史和科学发现的迷人解说,但是,我们不应指望靠它来指导今天的科学家如何去工作,或告诉他们将要发现什么”。温伯格愿意承认“哲学家的观点偶尔也帮助过物理学家”,不过,这“一般是从反面来的――使他们能够拒绝其他哲学家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哲学家照样看得清楚,怀特海说得简明干脆:“科学拒绝承认哲学”。
那么,不说奠基和指导,哲学也许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后总结和概括?把科学上升到一个哲学的更高层次上?且不问哲学怎么一来就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只问问这种上升这种概括有多大意义?再说,你哲学家连一门科学都不精通,你怎么概括全部科学?
逻辑实证主义不承认有高于科学的哲学,也不认为哲学和科学并列。哲学该做的是另一件事情:“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真有哪个科学家等到哲学家澄清了命题的真正意义才开始去证实它吗?也许他等不及哲学家澄清就开始去证明一些意义含混不清的命题了?科学事关一种狭义的真理而哲学事关意义和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提法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浅薄框架中窒息了。哲学和科学并非分别关心同一些命题的意义和真理性,它们是用不同的语言或曰“命题”开展其工作的。
也许,关于自然,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理论,一种是科学理论,一种是哲学理论。到了十八世纪末,物理科学在各个分支中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而就在同一个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家重新兴起了自然哲学。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一个代表。科学研究时间、空间、力、粒子、化合,哲学在另一个上下文中也研究这些。用伽达默尔的话说,那是最后一个意在综合自然和历史、综合自然和社会的宏大哲学体系,其秉持的理想是“最为古典的诉求”――“通过存在的逻各斯来思考”。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在当时也很快成为笑柄。黑格尔哲学在他身后很快没落,成了“死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自然哲学太牵强了。在科学革命之前写自然哲学是一回事,在那之后还写自然哲学是另一回事。今天,我们眼前摆满了前所未知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复杂科学理论引导下所设计的实验产生出来的,只有那些复杂的科学理论能为之提供合理的说明。我们的自然理性或曰“存在的logos”无法把这些事实容纳到条理一贯的理论体系中去。如果能够,一开始也不会出现从哲学到科学的转型了。
相形之下,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讲演录》、《自然哲学概论》是更地道更传统的自然哲学。但奥斯特瓦尔德把自然哲学视作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的最普遍的分支”。自然科学里该有这样一个分支吗?“最普遍的分支”这话本身就费商量。自然哲学不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前实证科学的关于自然的理论体系,面对成熟的实证科学,自然哲学总体上已经丧失了生命力。诚然,我们随时都可以在实证科学尚未到达的领域里继续富有成果的哲学思辨,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可以成为引导科学进入这一领域,并在最初为实证研究提供启发,但说不上是系统的理论,一旦实证科学在这个领域内建立起可靠的理论,这类先知类型的著作,智慧仍在,其具体内容则不再重要。
哲学的终结?(2)
十九世纪,一大批哲学家尝试在Naturwissenschaften和Geistwissenschaften之间划出界线。我们可以建立实证性质的物理学理论、化学理论、生物学理论、生理学理论,但我们无法用实证方法建立人的理论,国家的理论和社会的理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