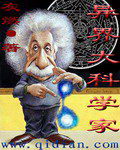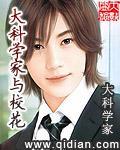哲学科学常识-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演化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一个科学史的内部问题,并不涉及一般的实在问题――我们能认识实在还是不断接近于对实在的认识还是根本不能认识实在?
科学理论中的名词是否实有指称?很多反实在论者指出,看似指称性的名词其所指的东西经常变换得那么剧烈,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各自始终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语词指称的问题当然与实在问题相关,或不如说,它本来就是实在问题的一种特定形式。但这是一个一般的语言哲学问题,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以澄清。日常语言中的指称性名词所指的东西也经常变换,例如“户”从前指称门,现在指称别的什么了。诚然,日常名称的指称变化一般是缓慢的,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
说到预测尽管保障了理论的正确性却并不保障理论的实在性,我们要讨论的是正确和真实这两个概念的一般同异问题。
上述争端,以及其他许多争端,涉及的主要是一般实在概念问题,而不是科学史的专业问题。固然,从科学史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有可能做出别有新意的贡献,但我们分清问题的层次,很多争端会变得比较鲜明可解。
物理学的实在问题(1)
物理学的实在问题
关于实在的争论,关于真实的争论,是哲学的首要的、永恒的话题,物理学的实在性争论是一般的实在问题的一例。关于一般的实在与真理问题,我曾在别的地方做过一点儿讨论,本节要讨论的是:怎么一来物理学的实在性就特特成了问题?为什么古典理论不发生实在的问题?这里谈到对物理学实在性所生的怀疑,是以肯定日常对象的实在性为一般背景的。于是,我们需要澄清的就是,物理学对象和日常对象有何种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科学怎么一来就接触实在了,而是科学怎样一来就似乎离开了实在。通过前面对操作、假说等等的讨论,我们应该为思考这个问题有了相当的准备。
科学是理论,理论的真实性从来就和日常对象的真实性不同。我们知道并接受这种区分,所以并不一般地对理论的实在性提出质疑。自古以来人们就从各种角度争论实在问题,然而,总的说来,希腊人争论感觉是否实在等等,而理论对象是否实在则不形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古典理论是依赖于经验的理论,其真实与否可验之于经验。当然,经验、感性是否实在本身也可以成为问题,但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不是理论对象是否实在的特殊问题。实际上,哲学…科学本来意在确切认识实在。如果把实在一般地区别于神话、幻觉、主观感受等等,那么,哲学…科学正是关于实在的认识的专门发展。
科学理论的实在性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物理理论首先是以假说的形式提出的,假说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种观察或实验结果能够对假说加以验证,则都是由数学来说明的。
这造成了物理学特有的实在问题。我们须得警惕,不要把它泛化为一般的实在问题,把假说…预测…验证…实在当作讨论一般实在问题的模式。那样一来,我们似乎会说,我看见了一串葡萄,于是提出这是一串实在的葡萄的假说,我把这串葡萄拿到手里、吃到嘴里,验证了原来的假说,肯定了这串葡萄是真实的。
这里的叙述方式有点儿别扭,但似乎道理并不错。然而,凡遇到这类别扭的叙述方式,我们都要提高警惕。把一种普普通通的情况用相当理论的语言重述出来,往往不只是重述,而是塞进了某些东西,或者隐藏了某些东西。
这个叙述默默地预设了,事物是否实在原则上是需要验证的。上文已经表明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实在观念不是建立在假说…预测…验证之上的。实在并不一般地需要验证。而科学假说之所以需要验证,主要因为它是间接得出的,与资料的关系是外部关系,它不是资料本身的应有之理。
与资料相符但看不出什么道理的定律被称作“经验定律”。这不是个良好的用语,但我们姑妄沿用。经验定律的实在性的确是可疑的,也很少有科学家把经验定律当作对实在的把握。它们是“操作性的”,无非是符合资料罢了。
然而,科学探索并不满足于停留在经验定律上。我们曾引用柯瓦雷,“科学思想总是试图透过定律到达其背后去找出现象的产生机制”。机制才是科学所探求的实在。柯瓦雷的这句话本来是要说明,操作态度只是暂时的,科学探求实在,其方式是从定律走到机制,而这就是说,从操作走向真实。
科学理论集中探索的是机制。机制是不是实在的呢?首先须提醒,日常世界里也有不同种类的存在,或说得更适当,在日常环境中,我们也在不同意义上说到存在。旗子存在,旗子的各部分存在,风存在,力存在,风对旗子的作用存在,某种因果致动关系存在,某种力学机制存在。力和旗子的实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我是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确定旗子是否存在和力是否存在。要确定旗子的实在,我们看一看、摸一摸,但力却看不见摸不着。这当然不表明我们无法确定某种力是否存在。
日常世界里有不同种类的存在,同样,科学对象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能量、磁场、夸克的存在方式和电子的存在方式不同。把粒子理解为场,当然不是把它视作某种不实在的东西。场不是空洞的、仅仅具有几何性质的空间,而是具有物理性质的空间。场就像风一样实在,只不过在这里,实在和虚空的截然两分被取消了,我们发现质子并不是像米花糖球里的一颗小米花而是更像一个电磁场,这丝毫不渐少质子的客观实在,除非是说,风不像旗子那么实在。
但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物理学理论中,存在物和机制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在我们的日常理解中,物体是实在的原型,而在现代物理学中,物体的观念越来越淡,所谓描述微观“物体”,其实就是描述一个机制。而比较起对物体的描述,对机制的描述更多依赖于我们的概念方式。
物理学对机制的描述,包括对微观物体的描述,依赖于它所特有的一套语言。如上章所述,这是一套用数学定义的语言,或者干脆就是数学语言。物理学的实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数学世界”是否实在的问题。数学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世界、实在的世界?常识眼中的世界和数学世界哪个是真实的世界,或哪个是更真实的世界?
“数学世界”也许是和“桥牌世界”、“丝绸世界”的用法差不多。数学家沉浸在数学世界里,桥牌迷沉浸在桥牌世界里,这时候谈不上数学世界是否真实。
物理学的实在问题(2)
“数学世界”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数学是一种语言,它描述世界, “数学世界”即由数学描述出来的世界。我们问数学世界是否真实,就是问数学是否能真实地描述世界。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会问,汉语是否真实地描述了世界;我们可以用汉语真实地描述世界,也可以用汉语歪屈世界。我们不会问,汉语和英语所描述的世界哪个更加真实。我们会问,汉语的长处何在,汉语的短处何在。一个双语者在有些场合觉得说甲种语言达意,有时说另一种语言达意。我们可以像布鲁纳那样,把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视作“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双语”。
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特殊意义”这一点。语言使用是有规则的,但说话远远不止于一种遵守规则的行为。语词与语词之间的联系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形式逻辑化,它还包含其他多种联系,隐喻的联系乃至词源、情感意味、音色、字形之间的联系,言说是否通畅入理,所有这些联系都在起作用。眼下,我把逻辑关系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笼统称之为“感性因素”。而在数学中,只有一样东西决定符号之间的联系是否成立,即数字之间的相互定义。由于数字不再具有感性内容,所以数学表达是充分遵守演算规则的活动。我们通过努力可以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最后像母语一样亲熟。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最后极为熟练地使用数学语言,这意味着,极为纯熟地应用一套规则。但数学表达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母语。
所以,我们只有在一种严格限定的意义上才可以把数学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比作外语和母语之间的关系,英语和汉语是并列的两种语言,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是两个层次上的语言。
对于英语和汉语,不存在哪种语言描述的世界更加实在的问题。然而,由于数学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两个层次上的语言,就可能出现了哪种语言在描述实在世界的争论。数学和实在的关系曾一直是双重的。一方面,如数与实在一节所表明的,理论倾向于区分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理论把握实在,这个实在,强烈地含有“数”的观念。数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循环替代,数世界才是实在,数的运行决定现象世界的展现。另一方面,对自然的纯数学处理,曾一直被认作是操作性的。在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关键的转折。自然逐渐被理解为用数学语言书写的。因此,只有数学才能真正把握实在。前面曾提到,尽管牛顿出于当时应有的谨慎,把万有引力称作“数学的力”,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万有引力的“真实的物理的意义”。如“运动”一节所言,为方便计而引入操作定义是一回事,由于理解的转变而不得不重新定义基本概念是另一回事。新物理学家重新定义我们关于自然的基本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从数学上处理关于自然的问题。正是牛顿完成了从形而上学到数学物理的关键转变。从今以后,对物理学来说,凡合乎数学描述的,就是实在的,乃至惟有合乎数学描述的,才是实在的。
在伽利略看来,能够使用数学来描述的两个直线运动及其合成才是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曲线运动只是现象,乃至只是幻象;就像X光照出来的才是真相,脸蛋儿长得漂亮不漂亮不过是些主观的感觉。然而,对我们的感知来说,真实存在的似乎仍是单一的曲线运动,力学分析只是迂回的假说。我们早已普遍接受了数学物理的自治,但我们的自然理解仍然感到“数学的”和“物理的”两者之间存在区别,这一区别仍隐隐对物理学的实在性提出质问。关于数学世界和日常世界孰真孰幻的争论错失了要点。这里的区别不是真和幻,而是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可得到直观的、自然的理解。
在实在问题的讨论中,实在和自然的联系这一点较少受到注意。我们平常说到实在的时候,自然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一样东西的颜色来得自然,我们就觉得实在,这颜色来得不自然,就像是假的。在古希腊,人们觉得圆周运动是自然的,一个由圆周运动组成的宇宙图景容易让人觉得它在描述实在,一个由椭圆运动组成的宇宙图景就像是个操作模型。圆周运动的中心如果落在地球上,这个图景就像是实在的,如果落在地球之外的一个虚空点上,就像个操作模型。古代理论比较接近常识的自然,理论对象是否实在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现代科学离开这个自然很远,因此缺少“实在感”。
物理学的实在问题(3)
不过,这种由自然而然之感而来的“实在感”从来不是判定实在的最终标准。不如说,它是一个起点。正因此,实在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