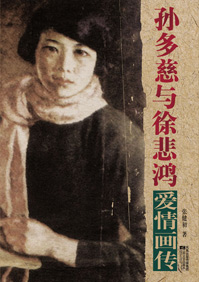�������챯�谮�黭��-��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档��Ů�����ر����⣬һ�����Ļ�Ҳ��˵��֮�ã����DZ��齨��ͥ����ʼ���������۵ķ������һ�����������������Ϊ��һ���������֣��ﴫ西���˵���Խ�Ѿ�����ʱ���ﴫ襣�����Զ�����룬�������ȹ��ң������������ڣ�Ϊ����ȡ�������������������Լ������������������һ������������Ů���ij�����������壬����Ҳ��������˼���м����ɷ֡������Ǻ��ܱ�������������������磬����Щ���ס���г��ƽ���Ŀ�����ΪŮ��ȡ������ȡ������������ֿ����ı��ס����Ȱ����������ơ������ȱ����������顱�����Ⱥ͡�����ϣ������Ů���������ʰ�֮�ģ���ů���Լ�����ů�������磬Ҳ��ů����������ġ��������˶�˵��Ů���Ǹ�ĸ������С�ް������ﴫ�Ҳ�����ĵ�С�ް��ˣ�������Ů�����ﴫ西����ֿ����ף��۰�֮�飬�������ϡ�
����1912�꣬�ڽ������ˣ�ʮ������챯�裬��һ��̤���Ϻ������ء�����ʮ�ߣ�ʼ���Ϻ�����ϰ������δ����;�����¶��顣Ϊ����ͼ���ں���֮������ѧ�����������İ���Ϸ�续��ʱǨ͵�������ڡ�ʱ���±����Ϸ�����������Ƚ�����Ҳ�������������ĵ�һ����Ʒ��
����
�����������ͷ����Ů��1��
����������̨�壬Ӧ̨�塰��ʷ�ݡ��ݳ�����ί�У����ƴ���������������ҺͿ���Ԫѫ���ͻ�����֪Ϊʲô��ֻҪһ���ʣ�������ǰ�����Ǹ��������������������������С������졣��ƽʱ���ж��ٴΣ����̿�ֽ������Լ�ӡ���еİ����ϳǻ���������ʼ�ղ����±ʣ������������̫�మ̫���̫����̫��������һ��ʣ��Ͱ��Լ��������ϳǵ�ӡ����嵭�ˡ�
��������̨����ͷ��������棬���ȵ����У�������������Ī���ij�������֪�������ֳ�����˼�硣�����������ˣ�������û�е�����ȥ��������ͯ�꣬�������꣬�����ഺʱ�������밲��ʡ�ǰ�����ܵ���ϵ��һ��
�������ȶ���ǵ���ʶ�����������еĻ��ʣ��������ӻ滭�ǶȵĹ۲졣
����ʲôʱ��Ի滭������Ȥ�ģ��Dz����ˣ�Ҳ�����������ɡ��Դ�һЩ�����###�꣬��ϲ����ģ�����ؼ���һ��С����������ֵ��ܣ�����ʲô���������������
����ӡ���������1921����һ��������������ӡ���֪Ϊʲô��СС������ͻ�����룬���������ų�¥��������ܦ֮�䣬���Ž�ˮ������������Ƭ��ɫ��
������ѧУ���Ͽε����գ�һ����ʹӼ���������ˡ������˽ֲ�Զ��ֻ�������ӵ�·�����ϣ����Ƿ���������¥���ؽֵ�����һ���Ż�û�п�������������ӿ����������������ʮ�����֡��������˸�����ɫ�˷ܣ���ʶ�Ļ��������Ⱥ����к���������Ϣ�𣿡���û�У����ڰ��־�ȥ�ˡ����ȼ�����Ⱥ�У����ϣ�������¥���ϵ����£�����֬��ɸ߸ߵ�ʯ������������������������ŵ��������ų�¥��
��������ʱ�������ȵ����������վ���߸����ų�¥��ʱ����ʹ��ź����ˡ����Ӱ����Ʈ�䣬������¶�ı۰��ϣ���һ˿����������ˮ�ܴ���Ľ����ϣ������ǻƵĽ�ˮ�����ư����ij�����һ˫����ˮ���ܣ��ȳ���ˮ�����ϣ�����ѹ��ˮ������
��������û�������������ĵط���
���������ij�ǽ�ϼ������ˣ������ij�ǽ��Ҳ�������ˡ���Ⱥ�У��г������ӵ�������ʿ��Ҳ�г��Ÿ첲�����Ұ�����ݲ�ͬ����ɫһ�£��������С��콫��������˹�ˡ�֮���ء����������ڳ�ǽͷ����ҹ��������������û�����ü�����������¥�µij��Ŷ��ڣ��������������������أ����dz��ǵ�ÿһ���˶���̲飬��ֵ��ǣ�����Щ�¹�������������ӣ��̲���ܵø�����ϸ����������һЩ����ȥ�����Ϳ຺�ӵ��ˣ������ӻ��־ͷ����ˡ����ֵ��ǣ��������̲�Ļ��DZ��̲�ģ���Ҷ��dz�����ضԴ���ǰ���£���û�з��У�Ҳû�е��ơ�
���������������۾�����ع�����һ�У������Ժ��С�������˸��������ˡ���ͷһ�����Ǹ����ﴫ襡�������СѾͷ�����ú��ڼ�����ţ��ܵ������ʲô���ˣ������쿪���ƾ��ڰ�գ��ƺ����Ͼ�Ҫ��������
�������������ţ�ɵɵ��Ц�ţ�֪�������������������أ���ô��ð���һ���ƴ�������
����������20�����������ֵ�������
������Ȼ����������������������������������������ֽ�ʣ���Ц�����������������Ǽҵ�С���ҵ����������ˣ�������Ҳ�ã������ѵõĴ��滭�������ô��֪�����ǰ�������ʲô���ij��У�֪�����ǰ�������Ⱥʲô����Ѫ�Ժ��ӡ���
����1921��İ��죬ע�����Ƕ���֮�����Ϊ��������֮�£���������ȫ���ġ��������Ұ���������ʡ����һʦ��һλ�н�������ѧ������ȥʡ���������˿۽�������һ����Ըʱ������ǹʿ�������ߵ����侭���ȣ����ջ��������ƹ��ض������������������������ڸ����������������ߵ��R��ʮ��ߣ���������������Ϊ����ʡʡ������Ϣ�������죬�����������ǿ�ҷ��ԣ����Dz�ȡ��ԭʼ����������֯��ǧ����˯�Խ�������ҹ���س��ţ������������°���Ǿ�ְ��
����������ǰ��һ�У����ǰ�������سǵij��档
�����������Ǻƴ�׳�۵ij�������ͯ�����ȵ��۹��У��ֱ����طŴ������������ǿ�Ҷ���̵�ӡ�����д��������������ɫû�л��ɣ�����һ����ʵ�Ļ���������һ����Զ����ס���������������ij��С������졣
�����������ͷ����Ů��2��
��ʵ�Ͼ�����һ�죬���������ij����ú��ִ��������죬�����������������µĴ������ֻ�װ��ũ����С����С�����ϰ����˳ǡ�������ˣ�����Ⱥ���Բ������ģ��̽���У�ѧ���տΣ���ͷ���˻������˰չ���������ʮ���죬����������Ժ��������Ҳ����û����˼������٣�����Ҳ�գ�������һ��������磬���������˰��졣
������������������һ����䣬�Ǹ��µ�25�գ�����������ʢ��###������������˰ɣ��ڻƼҲٳ�����ף���ա�����˶���ʤ����֮����еĻ��Ǵ����У������Ǹ����ң������Ǹ�׳�ۣ��ڰ���ǣ�����δ�С����ж����糱ˮ��ӿ���������Ŀںź����������Ĵ�����ɢ��������ӡ���������еģ���Ϊ��ʱ������˫���ֿڣ����ж����ѹѹ�����ˣ�ǰ�����ף���β���μ����е��ˣ�ÿ�����ﶼҡ��һ��С�죬�����ε�ֽ�������̻�ƣ�����Сľ���ϡ������ۼ⣬һ���ӿ�������Ҳ�����У���ƴ���غ���������û��������ֻ�������ڰ��֣��ָ������ж����߹�ȥ�ˡ�
����ͯ�����ȶԻ滭ֻ��һ�ְ��ã�Ҳ�������ڼ�ġ�¶��ѡ����������������dz���ġ�£�ȴ��������ǵľ��ȡ���һ�θ��������п����ˣ�Ҳ���治�ѣ����������Ǽ�Ѿͷ���ģ�����ɣ���Ȼ���������֣���
������������ֵĻ������ĵܵ��������
���������С������꣬��С�ͺͽ���ر��ף��������ȵ�����ȥ�����ܲ������ĸ��������������������С�������Ӧ����Ц����˵���ǽ�������С��ƨ�档������㻭������Ҳ�����м�����֣��ؼ����������Լ��ߣ�ֻҪ�����ʣ������ǻ�ʲô��ʲô����ʱ�����ո�װ��ƣ�һֻʮ��֧��ĵƹ⣬���������Ϸ������Ⱥ͵ܸܵ���һ�����ӣ�����ǽ����������������Ժ���������ⲽ�Ĵ���������ʱ������Ⱥ�����С�糵����ʱ���ܻ���Ի�����������ֽ�ϵĽ�㷽ͷ������ܵ�Ҳ��֪�����ʲô�����ˡ�
������ʱ����ĸ�����������Ҹ���ʱ�������ſ��ϣ������ؿ������ǡ������ڼ�ʱ��������������������������һ�࣬���ϵ�����һ��Ц�ݣ�һ�����ǰ��졣���벻��������ң�һ��һС����������λ��Ż��ң�����ĸ������������У�ʼ�������Ʋ�ס�ĵ��⡣
�������ȵ�ĸ�������ϡ���������1935�괺ĩ��
������ʱ���ﴫ��ڰ���ʡ���������鹤����ĸ��Ҳ��ʡ����һŮ�Ӹߵ�Сѧ���顣��ĸ������������ѧ���Լ����������ʶ��ͨ���ճ�����̸��ֹ������ӡ�����Ⱥ����ܵ����У����ɴ�Ӱ�쵽���ǵ���Ȥ���á����������ڡ������輯������ѧ���н����Լ��ijɳ���˵������������������ʱ�����Ḹ��ĸ�����գ��������������������У����������ڻ滭���֣��Ⱦ��о���֮��š�梵ܶ��ˣ����ڴ�ǰ���£�Ϳɫ���ɣ�ġд��Ȼ��������Һ����Ḹ��ĸ�˶���֮��Ϸ��Ϊ��С���ҡ���Ϊ������Dz��ֱ��Ȼ��֪Ҳ����
��������������Ȥ����ר��Ϊ�����˸����������ļ�ͥ��ʦ����ȻҲ�����ң����֣����ڣ����ɸ������ɸ��ǽ��������ˣ������죬�飬��̫���������Գ��Լ������������ס�ĵط��а�����ã�������������ң�ȴ�и����������֣��С�Х��¥������ʱ�����ɸ������Ů���ν̣���֯��һ���������磬ר�������й������������ȵĽ���������̾���ѣ�����Ϊ���ıʷ�̫Ұ���������Ѫ�Ե��к���������Ҳ�μӹ����ζ�������Ļ����ʼ�վ���û�����˼�������ͷ����ˡ�
�����������죬���ȴ��ʮһ����ɣ���������һλ���ˣ��������DZ�������һλ���ҡ����������������ϯ��ȸ��ˣ���Ҫ���Ȱ�ƽʱ������Щ�����ó������ÿ��˸����������������廹�濴�ˣ�����ͦ��ϸ���ؼ��ǿ��˺�˵�ã��ڿ������������ף�˵���ǧ���Ժ��������ⷽ�淢չ���뷨����ȥ����������
�������Ȳ������棬����С�죬������м����̬��
����������������������Ѿͷ����֪��ߵغ��ڱ������ڰ��죬�ж����������������ѧ���������������أ���txt���������ƽ̨��
�����������ͷ����Ů��3��
������λ���ѣ��ǰ��춫������ʯ�����ˣ���������������ǫ�У���Ŵ���ɽ�ԡ��ڱ����������dz����Ĵҡ�������꣬����ͳ������������ǫ���뵽�ң�ר��Ϊ�Լ���������ǫ��ɽˮϲ����ī�����С�������֮�ơ������ھ�ס��������̳������������Ͳ���Ϊ���ϱ�����������ǫ�лذ���ʱ�������DZ�ƽ����ר��ѧУ�Ľ��ڣ����ﴫ�һ����ʣ��Ĺţ��Ľ��Ĺ�ѧ��ʮ��Ͷ����һ���ˣ��ﴫ襾Ͱ��������������ˡ�
�����������ȿ�����ǫ�е�ɽˮ������������ϲ������Ϊ�������࣬�������㡣��������о�˵�븸����ʱ����������Ц���������Ѿͷ��ʲôҲ���������������ˣ���
�������Ǹ��װ����Ƚе����ߣ���ͬ����������һ��������dz������Ů��̸��ʫ��̸��ʣ�̸���ģ�̸��ʷ��̸ʫ����ʷ��滭�Ĺ�ϵ������������һ˫�������۾����ƶ��Ƕ�����һ��һ�䶼��������ȥ�ˡ��ڡ������輯���ġ���ѧ���У����dz���л�������������յ�ʽ������
�����Գ����Ḹ�����ԡ�ëʫ����Ի������ʫҲ���˼�֮����Ҳ��Ȼ�Ҳ���������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