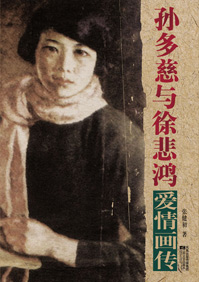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徐悲鸿笑了起来,“头一次见面,双方都不熟悉,你让人家怎么对你‘意思’?难不成要她上来就直白地向你表示爱意?不可能嘛!”
盛成说:“那当然不可能。但她的言谈举止,也没有给我什么可乘之机呀!”
“你们头一次见面,我又没有说破,她当然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想法。”
“问题是,你听好了,我说的是……问题是,” 盛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徐悲鸿,“她对某些人是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有意识无意识,表露得十分清楚。除非是傻子,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徐悲鸿望着他,筷子拿在手中反复转动,半天不说话。
“你别这样子看着我,我说的某些人,具体些,就是你徐悲鸿!”最后“徐悲鸿”的名字,盛成几乎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来的。
徐悲鸿愣了半天,最后不自然地笑笑,道:“这么说,你也看出来了?”
“我当然看出来了!”盛成非常肯定地回答。
话说到这个份上,徐悲鸿反而轻松地舒了口气。想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盛成。信是舒新城从上海寄来的,信封背面题有两句诗:“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什么意思?”盛成不明白,问。
徐悲鸿仰脖将杯中的酒一干而尽,然后从宗白华介绍认识孙多慈,栖霞乡村师范对她产生好感,到后来台城一吻,以及蒋碧微对此事的态度,通通说了出来。“本想把孙小姐介绍给你,断了我的一些想头,继续和蒋碧微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承想,你老兄以‘没有感觉’为由,一点忙也帮不上。你看看,这不是硬逼着我往火坑里跳嘛!”
盛成笑笑道:“相处多年,悲鸿兄那点心思,我还是看得透的。把孙小姐介绍给我,绝对是你的违心之举,或者说是你的虚招罢了。”又说,“我若真和孙小姐谈到一起,你徐悲鸿不拿刀杀了我才怪!我盛成再笨,也不会去做这个冤大头!况且,我也不想因为孙小姐,失去了你这位多年的好友!”
“知我者,盛成也!”徐悲鸿颇为悲壮地把杯子举起来,将满杯酒一干而尽。
话头一转,两人都有意避开孙多慈不谈。这段友谊插曲,也成为他们心中埋藏多年的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1934年,盛成再度去欧洲,临别之际,徐悲鸿到盛成南京住处“卷庐”送行。相聊之中,徐悲鸿突发灵感,当场作了一幅中国画,取名《石头》,强逼着要送给盛成。画上题款只有八个字,“吾心非石,不可卷也。”
盛成看了半天,先是不解,后突然领悟,知是暗指孙多慈之事,不由得开怀大笑。
为孙多慈牵线盛成之事,徐悲鸿本是想瞒着孙多慈的,但最后还是忍不住,以笑话的口吻,同孙多慈说了。其实内心他还有更“狡猾”的目的,就是以此来试探孙多慈,看自己在她心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孙多慈脸“腾”地红了,她抬起头,恨恨地盯了徐悲鸿一眼。当两人眼光相遇时,徐悲鸿一颗心立刻被融化了——那眼光是哀怨的,那眼光是深情的,那眼光是凄迷的。那一瞬间,徐悲鸿脑中闪过的惟一念头,就是今生今世,一定要用全部真情,全部生命,百般呵护面前的这位淳朴少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 恋爱倾向(9)
孙多慈察觉到了一时的失态,装着去倒开水,轻描淡写将话题转开,“先生是嫌学生丑,嫌学生老,怕她嫁不出去吧!”
徐悲鸿一笑,“你看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吧。这种尖刻话都说得出来!”
孙多慈索性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我说的是真话,既然又老又丑,也不值得先生动这样心思!”
徐悲鸿解释说:“因为欣赏你,关爱你,所以才会为你牵这根线,换别人,我肯做吗?”
孙多慈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便把杯中的水端过来,道:“说老实话,我对盛成教授也没有感觉,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徐悲鸿“哦”了一声,“那你说说看,你喜爱的男人,应该是什么类型?”
孙多慈想了想,答:“稳重一些,宽厚一些,年龄也要稍长一些。身子骨强健,性格开朗,为人处事,要有大男子汉的血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聪明过人的才气。”略略迟疑,又补了一句,“相比之下,盛成教授干瘦了些,人显得精明,不太适合我。”
徐悲鸿开玩笑说:“好了,知道了,以后就按这个模子为你寻一个婆家。”
孙多慈白了他一眼,但眼神中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温柔而多情的爱意。
徐悲鸿觉得自己从她的眼中,读到了一首关于未来的动人诗篇。
与孙多慈相聊时,徐悲鸿手中的画笔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手头的这幅作品,是国画人物《黄震之像》。孙多慈侧头看了半天,不知道画中的人物是谁,但从徐悲鸿的创作神态看,她知道他对这幅画十分看重,投入了很多精力。
徐悲鸿回忆说,“1915年我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准备报考震旦大学院,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差,经常饿着肚子画画。黄震之是位商人,得知情况,给了我很大帮助,要不是他,我绝没有现在这般成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徐悲鸿是不会忘记的。”说这话时,徐悲鸿动了真情,后来他在画上题款道:“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悲鸿写并录旧诗。”
诗是这样写的:
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
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
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愁早忘!
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
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
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末世欲何为?
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孙多慈立在一边轻声读完,之后半天无语。她的眼角,湿湿地闪有泪花。
徐悲鸿回头看见了,不解,问,“又触动你什么心思了?”
孙多慈摇摇头,“我是为老师的身世而感叹,也为老师知恩图报的这种品格而感动。”
这一刻,斜阳余辉从窗外射进,孙多慈整个身子浸于其中,宛若一尊披着金色霞光的女神。这一刻,本身就是一幅凝固的油画。
徐悲鸿感觉手有些痒,创作冲动如火花,如灵光,由此激发而出。“多慈,我要为你画一幅画,”他的言语有些激动,“我要为你画一幅我满意你满意并且要让许多人满意的油画!”他说。
孙多慈笑而不语。
孙多慈素描《瓶汲》,作于1930年前后,刊《孙多慈描集》。
此后一段时间,徐悲鸿完全沉浸在他新的创作热情之中。晚年蒋碧微回忆:“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因为他初到南京时,中大曾经在艺术系给他预备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他一直保留着,后来就做了他的画室,学生们当然也常到他画室里请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敏锐的感觉。”
1930年12月31日深夜,天上飘着雪花,南京街头,偶尔也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爆竹声。秦淮河两岸,灯红酒绿,低吟浅歌。但更多的地方,是无边无尽的夜色。
1931年的元旦,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悄悄地来了。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徐悲鸿完成了他的新作。他给它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叫《台城月夜》。画面上本来是没有月亮的,但后来他还是加上去了。他希望那轮清澈如水的月亮,能照亮他眼下这条铺满五色花的爱情小道。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八、 台城月夜(1)
八、 台城月夜
孙多慈知道徐悲鸿是在画自己,但徐悲鸿瞒得很紧。孙多慈每次来画室,徐悲鸿或是做《孙多慈像》最后的修改,或是以她为模特画一些素描,整体,局部,正面,侧面,身体各个部位。而里间书房,支起来的另一画板,永远用一块蓝布遮盖着。孙多慈也不多问,在画室,依旧默默做着她应该做的一切。而孙多慈这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善解人意的态度,更让徐悲鸿对她充满了好感。
新年后不久,舒新城从上海寄来他拍摄的六十幅西湖风景照片,请徐悲鸿帮他选二十多张,出一本摄影集。这也是徐悲鸿的主意,他觉得舒新城的西湖风景摄影,表现力,丝毫不亚于绘画。徐悲鸿为摄影集取名《美的西湖》,亲自设计了封面,还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专门为摄影集作了个序。
孙多慈这天过来时,徐悲鸿的“序”刚刚写好,从头至尾看了两遍,很满意。见孙多慈进来,立即招招手,把她叫到自己身边,然后大声读给她听,“夫百尺巍楼,万间广厦,大匠之功也,其结构不能舍规矩而为。桌椅橱架之工者,亦审知其材。又如植果木者与耕耘者,虽所事不同,要期其收之美之熟,无二致也。”读到此,他将自己认为出色的几幅摄影挑出来,让孙多慈在一边仔细欣赏。“吾友舒新城先生,既以其摄影《习作集》问世,道惬于人,不胫而走。吾虽叙之,例为楚声。庚午秋, 新城东游归,箧中益富,思陆续以所造公诸同好,因先辑旧稿,征意见于仆。仆乃于其叱咤之际,加以抑扬激越之后,和以曼声,犹楚声也。”
孙多慈之前也看过一些风景照片,但看了就忘了,并不认为它是一门多大的艺术。但看徐悲鸿为舒新城摄影集选出来的摄影作品,又听他深刻而独到的赏析,仿佛走进全新的艺术领域,惊讶不已,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徐悲鸿说,“无论绘画,还是摄影,美都是相通的。”继而,声调一提,半文半白,以吟诵形式,谈出他对“美”的理解。“美者,及造物组织自然之和,或在字,或在音,或在象,或在色,而造物不尽和美术者,乃撷取造物所以为和之德。而艺术不尽美,取舍者嗜向之,徵体者习守之调也。”
孙多慈无话可说,她的眼光始终盯在徐悲鸿脸上,一副崇敬之情。
徐悲鸿不由得伸手在她脸上拍了拍,“这是怎么啦?走火入魔?”
孙多慈一脸通红,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徐悲鸿一高兴,拽着孙多慈的手,把她拉到画室内间那始终遮着蓝布的画板前。“知道最近我在创作什么作品吗?”
孙多慈摇摇头。
“想不想看?”
孙多慈点点头。
“想看就把布掀开来。”
孙多慈疑惑地看着徐悲鸿,手不动。
“让你掀你就掀,怕什么呀!”
孙多慈手向前伸了半截,想想,又缩回来。望望徐悲鸿,见他眼里尽是鼓励,便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将遮在画板上的布的一角捏住,闭上眼,“哗”的一声,将它扯了下来。
画室一亮。天地一亮。
孙多慈眼睛一亮。孙多慈心头一亮。
画面上,徐悲鸿席地而坐,两眼望天,天际皓皓一轮明月。
孙多慈侧立其左,眼含柔意,脸浮温情。绕在脖颈间的一方纱巾,随风拂动。
关于孙多慈,同是安庆老乡的作家苏雪林曾这样描写她:“一个青年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