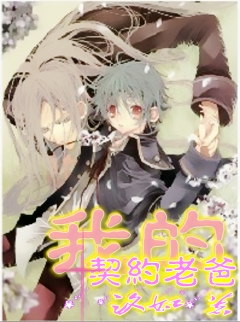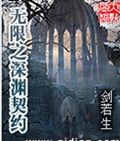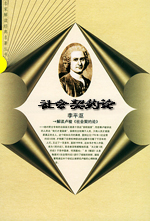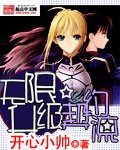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他们的行动已经不再是主权者,而是行政官了。这好像
是与通常的观念正好相反,但是请容许我有时间来阐述我的
理由吧。
我们由此应当理解: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
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因为在
这一制度中,每个人都必然地要服从他所加之于别人的条件。
这种利益与正义二者之间可赞美的一致性,便赋予了公共讨
论以一种公正性;但在讨论任何个别事件的时候,既没有一
种共同的利益能把审判官的准则和当事人的准则结合并统一
起来,所以这种公正性也就会消失。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明这个原则,我们总会得到同样的结
论;即,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以致
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
利。于是,由于公约的性质,主权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
一切真正属于公意的行为——就都同等地约束着或照顾着
全体公民;因而主权者就只认得国家这个共同体,而并不区
别对待构成国家的任何个人。可是确切说来,主权的行为又
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
体和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
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
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的幸福而
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别的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着
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只要臣民遵守的是这样的
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别人,而只是在服从他们自己
的意志。要问主权者与公民这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到达什么
限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于自己本身——每个人对于全体
以及全体对于每个个人——能规定到什么地步。
由此可见,主权权力虽然是完全绝对的、完全神圣的、完
全不可侵犯的,却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并
且人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自己的财富和自由。
因而主权者便永远不能有权对某一个臣民要求得比对另一个
臣民更多;因为那样的话,事情就变成了个别的,他的权力
也就不再有效了。
一旦承认这种区别以后,那末在社会契约之中个人方面
会做出任何真正牺牲来的这种说法便是不真实的了。由于契
约的结果,他们的处境确实比其他们以前的情况更加可取得
多;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一项割让而是一件有利的交易,也就
是以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的、不
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
代替了自己侵害别人的权力,以一种由社会的结合保障其不
可战胜的权利代替了自己有可能被别人所制胜的强力。他们
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并且当
他们冒生命之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事不也
就是把自己得之于国家的东西重新给国家吗?他们现在所做
的事,难道不就是他们在自然状态里,当生活于不可避免的
搏斗之中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以保卫自己的生存所需时,他
们格外频繁地、格外危险地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吗?诚然,在
必要时,人人都要为祖国而战斗;然而这样也就再没有一个
人要为自己而战斗了。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只需去冒一旦
丧失这种安全时我们自身所必须去冒的种种危险中的一部
分,这难道还不是收益吗?
第五章 论生死权
有人问:个人既然绝对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又
何以能把这种他自身所并不具有的权利转交给主权者呢?这
个问题之显得难于解答,只是因为它的提法不对。每个人都
有权冒自己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难道有人会
说,一个为了逃避火灾而跳楼的人是犯了自杀罪吗?难道有
人会追究,一个在风浪里被淹死的人是在上船时犯了不顾危
险的罪吗?
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谁要达到目的也就要拥
有手段,而手段则是和某些冒险、甚至于是和某些牺牲分不
开的。谁要依靠别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必要时就应当也
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公民也不应当自己判断法律所
要求他去冒的是哪种危险;当君主对他说:“为了国家的缘
故,需要你去效死”,他就应该去效死;因为正是由于这个条
件他才一直都在享受着安全,并且他的生命也才不再单纯地
只是一种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
对罪犯处以死刑,也可以用大致同样的观点来观察:正
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
己做了凶手的话,自己也得死。在这一社会条约里,人们所
想的只是要保障自己的生命,而远不是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决
不能设想缔约者的任何一个人,当初就预想着自己要被绞死
的。
而且,一个为非作恶的人,既然他是在攻击社会权利,于
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祖国的叛逆;他破坏了祖国的法律,
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甚至于是在向国家开战。这时
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两者之中就有一个必须
毁灭。对罪犯处以死刑,这与其说是把他当作公民,不如说
是把他当作敌人。起诉和判决就是他已经破坏了社会条约的
证明和宣告,因此他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了。而且既然他至
少也曾因为他的居留而自认为是国家的成员,所以就应该
把他当作公约的破坏者而流放出境,或者是当作一个公共敌
人而处以死刑。因为这样的一个敌人并不是一个道德人,而
只是一个个人罢了;并且唯有这时候,战争的权利才能是杀
死被征服者。
然而人们也许会说,惩罚一个罪犯乃是一件个别的行为。
我承认如此,可是这种惩罚却不属于主权者;这是主权者只
能委任别人而不能由自己本身加以执行的权利。我的全部观
念是前后一贯的,不过我却无法一下子全部都阐述清楚。
此外,刑罚频繁总是政府衰弱或者无能的一种标志。决
不会有任何一个恶人,是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使之为善
的。我们没有权利把人处死,哪怕仅仅是以警效尤,除非对
于那些如果保存下来便不能没有危险的人。
至于对一个已受法律处分并经法官宣判的罪犯实行赦免
或减刑的权利,那只能是属于那个超乎法律与法官之上的人,
也就是说,只能是属于主权者;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的权
利也还是不很明确的,而且使用这种权利的场合也是非常之
罕见的。在一个治绩良好的国家里,刑罚是很少见的,这倒
不是因为赦免很多,而是因为犯罪的人很少。唯有当国家衰
微时大量犯罪的出现,才保障了罪犯不受到惩罚。在罗马共
和国之下,无论是元老院或是执政官都从来没有想要行使赦
免;就连人民也不曾这样做过,尽管人民有时候会撤销自己
的判决。频繁的赦免就说明不久罪犯就会不再需要赦免了,大
家都看得出来那会引向哪里去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满腔幽
怨,它阻滞了我的笔;让那些从未犯过错误而且也永远不需
要赦免的正直人士去讨论这些问题吧。
第六章 论法律
由于社会公约,我们就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现
在就需要由立法来赋予它以行动和意志了。因为使政治体得
以形成与结合的这一原始行为,并不就能决定它为了保存自
己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事物之所以美好并符合于秩序,乃是由于事物的本性所
使然而与人类的约定无关。一切正义都来自上帝,唯有上帝
才是正义的根源;但是如果我们当真能从这种高度来接受正
义的话,我们就既不需要政府,也不需要法律了。毫无疑问,
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但是要使这种正义能
为我们所公认,它就必须是相互的。然而从人世来考察事
物,则缺少了自然的制裁,正义的法则在人间就是虚幻的;
当正直的人对一切人都遵守正义的法则,却没有人对他遵守
时,正义的法则就只不过造成了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
幸罢了。因此,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
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的。在自然状态中,一切都
是公共的,如果我不曾对一个人作过任何允诺,我对他就没
有任何义务;我认为是属于别人的,只是那些对我没有用处
的东西。但是在社会状态中,一切权利都被法律固定下来,情
形就不是这样的了。
然则,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只要人们仅仅满足于把形而
上学的观念附着在这个名词之上的时候,人们就会始终是
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纵使人们能说出自然法是什么,人们
也并不会因此便能更好地了解国家法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对于一个个别的对象是绝不会有公意的。
事实上,这种个别的对象不是在国家之内,就是在国家之外。
如果它是在国家之外,那末这一外在的意志就其对国家的关
系而言,就绝不能是公意;如果这一个别对象是在国家之内,
则它便是国家的一部分:这时,全体和它的这一部分之间便
以两个分别的存在而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其中的一个就是
这一部分,而另一个则是减掉这一部分之后的全体。但是全
体减掉一部分之后,就绝不是全体;于是只要这种关系继续
存在的话,也就不再有全体而只有不相等的两个部分;由此
可见,其中的一方的意志比起另一方来,就绝不会更是公意。
但是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他们便只是考
虑着他们自己了;如果这时形成了某种对比关系的话,那也
只是某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象对于另一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
象之间的关系,而全体却没有任何分裂。这时人们所规定的
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
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
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
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
及个别的行为。因此,法律很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
却绝不能指名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
若干等级,甚至于规定取得各该等级的权利的种种资格,但
是它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等级之中;它可以确立一
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它却不能选定一个国
王,也不能指定一家王室:总之,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
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
根据这一观念,我们立刻可以看出,我们无须再问应该
由谁来制订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我们既无须问
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也无
须问法律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