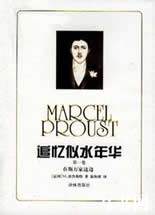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美]-第5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褪亲钛纤嗟难芯靠翁獾哪谌荩乇鹗堑彼ü鹕奖⒒蚺诘浠鞯耐垩蚁嗨频奈镏识暾奕钡乇4嫦吕础M胀鹕脚绶⒊隼吹钠逑嗨频闹舷⑼咚梗笤衩慌优喑堑谋浪茄谋浪缒芡暾奕钡乇4嫠心切┥形唇浠婊偷袼茉送驮寄散俚淖蠲笆У呐耍晕蠢吹睦防此到嵌嗝凑涔蟮淖柿希】銮遥荒暌岳矗皇且丫糠值乇湮优喑牵棵刻焱砩希庑┤俗甑降亟牙锶ィ皇俏舜永锩婺贸鲆黄磕峦āぢ尢叵6禄蚴ヌ┟桌撼戮脾冢俏税阉亲钫涔蟮亩骱退亲约阂黄鸩仄鹄矗拖蠛绽死张的发鄣哪切┥窀福诎嶙呤テ魇蓖蝗凰廊ァ6晕锏囊懒底苁歉加姓叽此劳觥0屠璨⒎侨绾绽死张的纺茄怯珊绽死账勾唇ǖ摹5慈绱讼嗨疲∥颐怯姓庵智逍训娜鲜叮⒉灰馕蹲旁谖颐堑氖贝扛雠硕家丫哂姓庵秩鲜丁H绻颐窍衷谌衔颐敲魈斓拿丝赡芎臀胀鹕礁浇哪切┏鞘邢嗤敲凑庑┏鞘性诘笔币惨迅械阶约赫艿绞ゾ斜蛔缰涞牧礁龀鞘械拿说耐病S腥嗽谂优喑且淮狈孔拥那缴戏⑾志哂衅羰拘缘奶獯剩核鞫嗄贰⒏昴ΧN也恢朗欠袷撬鞫嗄氛飧龅孛约八狡鸬南敕ǎ蛘呤嵌耘诨鞯南敕ǎ沟隆は穆浪瓜壬谄碳涮纺犹炜眨芸煊值屯纷⑹拥孛妗!拔倚郎驼獬≌秸械乃杏⑿郏彼怠!鞍。仪装模切┯⒐谡秸际蔽叶运堑目捶ㄓ械闱崧剩阉强醋髌胀ǖ淖闱蛟硕保聪嗟弊愿海晕约耗芡耙刀咏薪狭浚矣质窃跹闹耙刀影。∪欢獯用姥У慕嵌壤纯矗侵皇窍@暗木杭颊撸窍@暗模仪装模鞘前乩急氏碌哪昵崛耍蛘卟蝗缢凳撬拱痛锶恕N矣懈雠笥讶チ寺嘲海谀抢镉兴堑挠浚业呐笥芽吹搅似婕#嗣窍胂蟛坏降恼嬲婕!B嘲罕淞搜涑闪肆硪桓龀鞘小W匀灰灿新嘲旱墓懦牵写蠼烫弥邢莸氖ネ健5比秽叮庖埠苊溃馐橇硪换厥隆6颐悄切┏っ谋∥椅薹ǘ阅滴揖醯梦颐浅っ谋⒛切┬“屠枞擞性跹奈兜溃疲拖竽潜吖サ哪歉觯觳慌碌夭慌碌难樱槎只纳裉N页3=凶∷牵翘干霞妇洌嵌嗝戳槊簦嗝赐ㄇ榇锢恚《馐〉男』镒樱蒙嗉獠音,说话时带方言的切口,又是那么有趣、可爱!我过去总是在乡下住上很长时间,在那些农庄里过夜,所以我现在能同他们谈话;然而,我们对法国人表示欣赏,不应使我们因此而贬低我们的敌人,否则就等于是贬低我们自己。您不知道德国兵是怎样的兵,因为您不象我那样看到过德国兵检阅时走的步伐,走的鹅步,unterdenlinden④。”接着,他又重提他曾在巴尔贝克对我概述的阳刚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典型具有一种哲理性更强的形式,他还使用荒谬的推理,有时,虽说他刚才还显得才智过人,但这种推理却使人感到摆出的理由过于牵强,是出自普通的社交界人士之口,虽然这位社交界人士聪明。“您看,”他对我说,“德国兵是极好的小伙子,有强健的体魄,心里只想到自己的国家伟大。
……………………
①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专区政府所在地。
②穆通·罗特希尔德和圣泰米利昂均为法国波尔多的名葡萄酒。
③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区的古城,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所摧毁,后在火山爆发的熔岩上建立雷西纳城,现名为埃尔科拉诺。
④德语,意思是“菩提树下”,是柏林的一条大街。
Deutschlandüberalles①,这并不是那么蠢,而我们呢——当他们在作阳刚的训练时——我们却沉溺于艺术爱好。”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艺术爱好这个词的意思也许同文学相近,他可能想到我喜欢文学,并曾经有过从事文学的愿望,所以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拍的时候乘机倚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压得很疼,就象我过去服兵役时,七六式步枪的枪托反冲到肩胛骨上一样疼),仿佛为了缓和他的指责,并对我说:“是的,我们沉溺于艺术爱好,我们都是这样,您也一样,您记得吗?您可以同我一样犯您的meaculpa②,我们过去太爱好艺术了。”我对他的指责感到突然,但又不能进行敏捷的答辩,由于我尊重对话者,对他友好的善意表示感谢,就对他作了回答,仿佛象他对我要求的那样,我也要拍打自己的胸脯,这样做实在荒唐,因为我丝毫不需要责备自己爱好艺术。
“好吧,”他对我说,“我在这儿同您分手(在远处伴送我们的那群人终于离开了我们),我去睡觉了,就象一位年纪很老的先生那样,何况战争看来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习惯,这是诺布瓦喜欢使用的愚蠢格言之一。”我也知道,回到家里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因此而一直呆在士兵中间,因为他已把自己的府邸变为军医院,依我看,他这样做不是服从于他想象丰富的需要,而是服从于他心地善良的需要。
……………………
①德语,意思是“德国高于一切”。
②拉丁文,意思是“我的过错”。
那天夜里月光明媚,没有一丝微风;在我的想象中,塞纳河在那些拱桥之间流着,应该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相象,而那些桥则由它们的平台和河的反光构成。月亮或者象征着德·夏吕斯先生的失败主义所预言的入侵,或者象征着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同法国军队的合作,那月亮又狭又弯,犹如一枚西昆①,仿佛将巴黎的天空置于东方的新月符号之下。
……………………
①古代威尼斯金币。
然而,他在同我告别时,一时间把我的手握得象要握伤一般,这是感觉象男爵一样的人们的一种德国特点,他这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有几秒钟之久,戈达尔看到了会说是在按摩,仿佛德·夏吕斯先生想使我的关节恢复尚未失去的柔软。某些瞎子的触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视觉。我不太知道这时的触觉可代替何种感觉,他也许只是觉得在握我的手,就象他也许觉得只是看到一个塞内加尔人走到阴暗的地方,而没有发觉是在欣赏此人。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男爵都错了,他犯了握得过紧和看得过多的过错。“德刚、费罗芒丹、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全部东方不就在其中?”他对我说,仍然因塞内加尔人走过而一动不动。“您知道,我只是从画家和哲学家的角度对事物和人发生兴趣。再说我年纪也太老了。我们俩没有一个是土耳其皇帝的姬妾,不能作为画面的补充,多遗憾呀!”
男爵离开我之后,在我想象中开始萦绕的不是德刚乃至德拉克洛瓦笔下的东方,而是我曾十分喜爱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老东方;我渐渐走进这些网状的黑暗街道,不由想起在巴格达的偏僻街区寻找艳遇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另外,天气的炎热和行走后的炎热使我感到口渴,但所有的酒吧早已关门,而由于汽油匮乏,我所遇到的由东方国家的人或黑人驾驶的出租汽车,甚至对我叫车的手势不予理睬。我唯一能喝点东西、恢复体力以便回家的地方是旅馆。但是,我所在的街离市中心相当远,自从哥达式轰炸机对巴黎扔下炸弹以来,这条街上的旅馆都已停业。所有的商店也是如此,老板由于缺少店员或感到害怕而逃到乡下,在店门上贴了一张用手写的普通启事,宣布商店将在一个遥远的日期重新开业,但是否能兑现却很成问题。其他尚未停业的单位以同样的方式宣布,每星期只开门两次。人们可以感到,贫困、遗弃和害怕笼罩着整个街区。因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看到这些被人遗弃的房屋之间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内的生命仿佛战胜了恐惧和倒闭,保持着活跃和富裕。从每个窗户关闭的百叶窗后面,透出因警察条例而变得柔和的灯光,但却显示出完全不把节约放在心上。大门不时打开,以便让某个新的客人进去或出来。这是一座旅馆(由于其产业主赚得到钱),应该激起所有邻近的商人嫉妒,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在这时看到,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从旅馆里迅速走出一名军官,由于离我太远,我无法在黑夜中看得清楚。
然而,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惊讶,我惊讶的不是他的脸,因为我没有看到,也不是他的军装,因为军装外罩着一件宽袖长外套,而是有两点极不相称,一是他身体经过的各个点的数目是如此之多,二是他出来所用的秒的数目是如此之少,而他之所以出来,看来是被困在里面的一个人的意思。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从外形上——我甚至也不会说从圣卢的模样、苗条、步履和敏捷上——认出他的话,那么是从一种他所特有的分身术上认出他。能在如此少的时间里占有空间中如此多位置的军人,已经消失在一条横马路里,他没有发现我,而我仍然在想是否应该进入这家旅馆,旅馆简朴的外表使我十分怀疑刚才从里面出来的人是圣卢。我不由回想起圣卢曾受到冤枉,卷入一桩间谍案,原因是在从一名德国军官身上搜查出来的信件里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军事当局为他彻底平了反。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把这件往事和我现在看到的事联系起来。这家旅馆是否被间谍用作接头地点?
军官走后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好几个兵种的普通士兵走了进去,这就更增加了我假设的分量。另外我当时口渴到了极点。也许我能在这里找到喝的,我就趁此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虽说其中也掺杂着不安。因此,我现在并不认为当时是由于那次相遇产生的好奇心才决定登上只有几个台阶的阶梯,阶梯上面是前厅,厅门开着,想必是因为天热。我起初以为我这种好奇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为我站在阶梯的阴暗处时,看到有好几个人来订房间,得到的回答都是全部客满。然而,这些人订不到房间,显然只是因为他们不是间谍窝中的一员,因为过了一会儿,一个普通的水手来要房间,服务台急忙把二十八号房间给了他。我在阴暗处可以不被别人发现,却能看到几个军人和两个工人在一个闷热的小屋里平静地谈话,小屋用杂志和画报上剪下来的彩色女人肖像作为装饰,显得矫揉造作。
这些人平静地谈着话,正在阐述爱国主义思想:“你要我怎么办呢?得象战友们那样去干,”其中一个说。“啊!我当然希望不要被人打死,”另一个说。他是在回答一个我没有听到的祝愿,我听出他第二天要重返一个危险的哨所。“啊!二十二岁的人,只干了六个月,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叫道,叫声中不仅有活得长久的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论理正确的意识,仿佛只有二十二岁这个事实能赋予他更多的不被人打死的机会,仿佛他被打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巴黎真棒,” 另一个说,“看不出是在打仗。那你呢,絮洛,你“但是,霞飞是个跟所有部长的老婆睡觉的男人,他没做过什么好事。”——“听到这样的事真扫兴,”一个年纪稍大的飞行员说,并朝工人转过身来,因为那工人提出如下劝告:“我不希望你们在前线这样说话,长毛的兵很快就会把你杀掉。”这些谈话十分平常,所以我不想再听下去;我要么再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