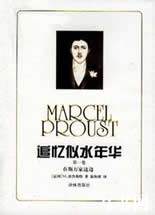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美]-第4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些上流人士,自称很有艺术欣赏力,对俄罗斯芭蕾硬作无谓的区分,认为《仙女》①的导演较之《天方夜谭》更为“细腻”、不难在《天方夜谭》中找到黑人艺术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十分高兴,高兴能亲眼看到这些艺术趣味和戏剧的伟大革新者,看到他们的艺术虽然比绘画略多一些做作,但是引起的革命却和印象派一样深刻。
……………………
①原为肖邦钢琴曲,改编为芭蕾舞剧,1909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演出时,斯特拉文斯基担任指挥。
回头再说德·夏吕斯先生。如果他仅把邦当夫人排在名册之外,那末维尔迪兰夫人也许不致于那么痛苦。维尔迪兰夫人在奥黛特家里发现她酷爱艺术,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她和丈夫到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来吃过几次饭。维尔迪兰夫人称他丈夫是个温吞水,因为他并不主张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他极为聪明伶俐,得意地和所有党派都串通关系。和拉博里共进晚餐时欢乐地表明他的独立态度。他对拉博里只是洗耳恭听,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但在关键之处悄悄插一句,赞扬饶勒斯为人诚实正直。这是任何党派都一致公认的。不过德·夏吕斯先生还除掉了一些贵族夫人的名字,她们是维尔迪兰夫人近时在隆重的募捐、赈济音乐会上新建立的关系;不管德·夏吕斯先生对她们作如何感想,她们远远有胜他一筹;她们是维尔迪兰夫人家新核心的构建因素,而且是贵族核心的基本分子。维尔迪兰夫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次晚会上,指望德·夏吕斯先生给她带些贵族夫人来,她另外加上一些她的新朋友。为此她事先就十分庆幸地想到,男爵请来的人可能是她新朋友的亲朋好友,要是她们在贡蒂河滨不期相遇,一定会喜出望外。他的禁令使她大失所望,愤懑不平。她觉得,按照这样的条件,举办晚会是有益还是有害,还值得考虑。如果德·夏吕斯先生请来的客人对维尔迪兰夫人起码都表现出极度的热情,那么损失还不至于太重,因为她们将会成为她的朋友。如果这样,还不算亏本。德·夏吕斯先生拼命想把上流社会这两部分人始终拆成两半。可是,不久有一日开晚会,有人自会把她们重新聚在一起,只是没让他来参加而已。维尔迪兰夫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男爵邀请的客人。她不久就会知道那些人是带着何种精神状态前来赴邀的,终于知道了能够和她们建立何种关系。眼下,维尔迪兰夫人正在和忠诚的门客们进行磋商,看见夏吕斯、布里肖和我一同走进来,立时收住了话头。
当布里肖对维尔迪兰夫人说,他得知她前挚友身体如此欠佳,他深表悲伤,她大出我们所料,回答说:“听着,我不得不承认,悲伤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自己没有的感情硬要装出来,这是无济于事的……”她无疑是精神不佳才这么说的,一想到整个晚会上她都要装出一副愁容,就已经觉得疲劳了;她这也是出于傲慢,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由于没有取消这次晚会在寻找歉词;不过她又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深于世故,因为她的缺乏悲痛,如果归之于对亲王夫人突然公开化的个人厌恶,那末总比众人事不关己的态度要高尚,不失气节,因为面对一种无可置疑的诚实,人们容易失去武装:如果维尔迪兰夫人对亲王夫人的故世不是真的无动于衷,难道她会给自己背上一个比这严重得多的罪名来为自己继续接待客人的做法开脱吗?人们忘了,维尔迪兰夫人本来可以承认,她确实非常悲痛,但是她没有勇气放弃一次欢聚的机会。但是,朋友的冷酷无情虽然是一件较为令人震惊、较为缺乏道德的事情,却又不是一件过于丢人的事情,因此比家庭主妇那种轻佻浅薄较为容易承认。从犯罪学的观点来讲,罪犯觉得哪里有危险,就避之不及朝有利的方向坦白;在免受惩治的错误面前,是自尊心决定坦白的内容。有些人为了不让忧伤中断他们欢乐的生活,便反复不休地说,内心的悲哀靠外在的服丧来表现是毫无意义的,也许维尔迪兰夫人觉得这种遁词已经是路人皆知的旧玩意了,因此她宁可仿效那些聪明的罪犯,弃绝者老一套的无辜表白,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作了一半坦白——的时候就说,凡是众人指责的事情,自己反而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不巧得很,自己迄今没有机会身体力行。也许维尔迪兰夫人在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采用了无动于衷的论点,她觉得自己既然已经踏上了怨恨的滑坡,不如把怨恨的心情表达出来,这样至少也有几分独特。把这种心情理清头绪,已不失为一种罕见的敏锐;把它公开表白出来,那就更能显示出某种“胆识”。因此,她故意强调自己毫无伤感,内心充满了荒唐的心理学家和鲁莽的戏剧家所有的那种骄傲与满足。“是的,这事很奇怪,”她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天,我不能说我不希望她活着,她不是一个坏人。”“她就是一个坏人,”维尔迪兰先生打断说。“啊!他不喜欢她,是因为他觉得我请她做客,有损于我。他为这件事情失去了理智。”“请承认我是正确的,”维尔迪兰先生说,“你们相互来往,我从来没有赞成过。我一直说,她的名声不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萨尼埃特回驳说。“什么?”维尔迪兰夫人嚷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不好,而是可耻,丢人。不,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感情。我对她并不厌恨,可是她对我们却那么冷漠,以至于当我们得悉她身体严重患病时,连我丈夫都大为惊奇地对我说;‘你对这事好象毫无感触似的。’这不,今天晚上他建议我取消晚会,我恰恰相反偏要举行,因为没有悲伤硬要装出悲伤,我会觉得是在演戏。”她说这番话是因为她觉得这奇怪得象“自由剧”,而且非常方便。因为冷漠无情或者坦白了的缺德跟浮浅的道德一样,都使生活变得简单了。她把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变成了一项诚实的义务,为之人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开脱的借口。底下的信徒们聆听着维尔迪兰夫人的话语,心头交织着钦佩和不适之感,犹如以前某些以残酷现实和痛苦观察为题材的戏剧所引起的感觉一样。许多人一边赞叹地看到,老板娘的正直坦诚和落拓不羁又变换了新的形式。一边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死亡,虽然他们心想,归根结底这不是一回事,但是他们还是在考虑,有朝一日自己突然死去,别人会是悲恸哀哭呢还是会在贡蒂河滨举行欢庆。“为了我的客人,晚会没有取消,我非常高兴,”德·夏吕斯先生说,他没有发现,他如此表达谢意,恰恰刺伤了维尔迪兰夫人。
这工夫,我跟那天晚上每个走近维尔迪兰夫人的人一样,闻到一股不太好受的诸美果耳利鼻油的气味,深有感触。事情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知道,维尔迪兰夫人表达她的艺术感情,从来不是使用心灵的途径,而是使用身体的途径,目的是使这种感情显得更加势在必行,更加深刻动人。如果有人跟她谈起凡德伊的音乐,即她最喜爱的音乐,她会一直毫无反应,仿佛她根本不指望凡德伊的音乐能够使她激动起来似的。她的眼神一动不动,几乎是心不在焉;这样停了几分钟以后,她却开始用准确、实在、近乎失礼的口气来回答你的话,仿佛在对你说:“您抽烟,我不在乎。我为的是地毯;地毯很漂亮——这我就更不在乎了——只是它很容易着火,我很怕火,我可不愿意因为您把一个没熄灭的烟头掉在地上,而把你们全都烧着了。”对于凡德伊也是这样。如果有人谈到他,她从不吐露半句钦佩之言,可是过了一阵,她却神情冷漠地对那晚演奏凡德伊的作品开始表示遗憾:“我对凡德伊毫无异议。据我看,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只是我听那些作品,一刻都不能停止哭泣(她说“哭泣”时毫无悲伤的神态,自然的样子倒象是在说“睡觉”。有些恶言恶语的人甚至还认为这后一个动词也许更为确切。其实谁也说不准,因为她听那些乐曲的时候,头蒙在手里,有些鼾声,说到底也有可能那是抽泣)。哭一哭与我倒没有害处,哭多久都行,只是过后这会给我添上要命的鼻炎,鼻膜充血,两天以后,我那样子简直就象一个老酒鬼了。要使我的声带恢复功能,我必须连续吸氧几天才行。总之,戈达尔大夫有个学生……”
“嘿!说到他,我还没有向您表示哀悼呢。他去得真快,可怜的教授!”“是啊,又有什么办法,他死了,跟其余人一样。他杀死的人够多的,这回是该轮到他举刀自戮了。嗯,我刚才对您说他有一个学生,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给我治过这毛病。他有一句相当独特的警句:‘治病不如防病。’所以他趁音乐开始之前。就给我的鼻子上药。这玩意儿彻底管用。我现在可以象无数失去孩儿的母亲那样放声痛哭,也不会再闹半点鼻炎。现在只是偶尔闹点结膜炎,仅此而已。药效绝对可靠。没有这贴药,我根本不可能继续欣赏凡德伊的音乐,还不是要一次接一次地患支气管炎。”
我再也按捺不住,终于要提一下凡德伊小姐。“作曲家的女儿是不是没有来?”我问维尔迪兰夫人。“还有她的一个朋友也没有来吗?”“没有,我刚刚接到他们一封快信,”维尔迪兰夫人吱吱唔唔地对我说。“她们不得不呆在乡下。”我心中一时升起了一线希望,也许她们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来。维尔迪兰夫人通告说,作曲家派这两个代表来,只是为了给乐队和听众一个良好的印象。“怎么?难道她们连刚才的排练也没有来吗?”男爵假装惊奇地问道,以便让人觉得他没有见到过夏利。夏利走过来向我道安。我凑近他耳边问他凡德伊小姐为什么不来的事。他好象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我示意他不要大声说话,并且告诉他我们过后再聊。他谦恭地答应说他将不胜荣幸地听凭我的吩咐。我发现他比以前有礼貌多了,恭顺多了。我当着德·夏吕斯先生的面赞扬了他——赞扬他是因为他可能有助于我解开我的疑团。德·夏吕斯先生回答我说:“他仅仅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跟贵人们在一起,行为举止如果还那么粗俗,那还有什么意思。”文雅的举止,按德·夏吕斯先生的看法,是法国人的传统举止,不带英国式的呆板。正因如此,当夏利从外省巡回演出归来,一身旅装回到男爵家中时,如果没有过多的人在场,男爵就会无拘无束地亲吻一下他的两颊。他如此炫耀他的温存,也许是想靠这个办法来消除别人脑中认为这种温存是有罪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接受一种乐趣,但更主要的,也许是想用文学的方式来维护和弘扬古老的法国礼仪,犹如他会用曾祖母的旧椅子来反对慕尼黑风格或者摩登款式,用见到儿子时毫不掩饰内心喜悦的十八世纪型温和慈祥的父亲形象与不列颠式的冷漠沉静相抗衡。不过这慈父般的恩爱是否蕴含着一丝乱伦的色彩?更有可能的是,德·夏吕斯先生自从丧偶以后,感情生活就一直十分空虚,他的行为方式虽然能满足他的恶习——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得到一些事实证明——但却不能满足他的感情需要。总之他曾多次考虑过重新结婚的问题,现在脑子又在打着主意,一定要继养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