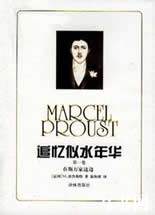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美]-第20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并不觉得“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觉得人的想象力,人的幻想具有伟大的力量,爱情的痛苦就是人的幻想造成的。罗贝看出我在激动。我扭过头去看对面花园中的梨树和樱桃树,好使罗贝相信是果树的美景使我动情的。而事实上,这些美景也的确打动我的心,把那些不仅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心感觉的东西呈现在我面前。我把在花园中看见的这些果树,当成素未谋面的天使了,我会不会和马德莱娜②一样看错呢?耶稣复活的那天,也是在一个花园里。马德莱娜看见一个人的形体,“以为是一个园丁”。这些向着适宜于午睡、垂钓和看书的树影俯下身躯的令人赞叹不绝的白衣少女难道不就是天使吗?这些白衣少女维护着我们对黄金时代的记忆,她们向我们保证,真实并不象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但只要我们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为报酬,真实也可能闪发出诗的光辉,纯洁而奇妙的光辉。我和圣卢的情妇寒暄了几句。我们抄近路穿过村子。房屋很脏。但即使在最肮脏的、象是被硝酸雨烧焦了的房屋前,也站立着一个神秘的旅客,要在这受到诅咒的城镇里停留一天。这个光辉灿烂的天使,展开令人眩目的白翅膀,保护着肮脏不堪的房子:这就是一棵挂满白花的梨树。圣卢和我朝前走了几步:
“我本不打算到这里来的,我们两人在城里等她,我甚至更乐意和你单独在一起吃午餐,一直单独呆到去我外婆家的时候。可是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她多么希望我们来接她呀!她对我太好了,你知道,我不能拒绝她。再说,她会使你愉快的,她很有文学天赋,很容易动感情。况且,和她一起在饭店共进午餐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朴实,总是对什么都满意。”
……………………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面值二十法郎的金币。
②《新约全书》中看见耶稣复活的女圣徒。耶稣遇难后,马德莱娜到耶稣的坟墓去给他涂圣油,发现尸体不在洞穴,她在寻找途中,遇见复活后的耶稣,错以为是园丁。
然而,我相信恰恰在那天上午,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罗贝在一瞬间摆脱了他通过一个个温存的印象慢慢地组合起来的女人,猛然看见不远处站着另一个拉谢尔,和他的拉谢尔长得一模一样,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小娼妓。离开爽心悦目的果园后,我们就去赶火车回巴黎了。在车站上,拉谢尔走在我们前面,相隔几步远。突然,有两个和她一样俗不可耐的“野鸡”认出了她,她们以为她是只身一人,便咋咋呼呼地嚷了起来:“是你啊,拉谢尔,和我们一起上吗?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都在车上,正好还有空位子。来吧,和我们一起去溜冰。”她们正要把各自的情夫,也就是把站在她们身边的两个“时装百货商店的职员”介绍给她,突然发现拉谢尔有点局促不安,便好奇地朝旁边张望,发现了我们,连忙道歉,同她告别;她也同她们道了再见,有点尴尬,但很友好。这是两个可怜的小野鸡,围巾是用假水獭皮做的。圣卢第一次邂逅遇见拉谢尔时,她差不多也是这个模样。圣卢不认识她们,也不知道她们的姓名,看见她们和他的情妇关系这样密切,便顿时生了疑团:他的情妇也许从前过着、甚至现在仍然过着一种见不得人的生活,一种同他和她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就是为了一个金路易而出卖肉体的生活。他不仅隐约看见了这种生活,而且还隐约看见了另一个拉谢尔,一个陌生的拉谢尔,和那两个小野鸡一样的拉谢尔,二十法郎身价的拉谢尔。总之,他感到拉谢尔在瞬间分成了两半,他在他的拉谢尔身旁隐约看见小野鸡拉谢尔,那个真实的拉谢尔——如果能说野鸡拉谢尔比另一个拉谢尔真实的话。此时此刻,也许圣卢心里在想,他本打算用自己的高贵门第去作一笔交易,同一个有钱的小姐结婚,以便能每年继续供养拉谢尔十万法郎,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他完全能轻易地摆脱他目前生活的地狱,花一点儿钱就可以得到他情妇的欢心,就象那两个时装商店的职员,用很少的钱就买到了那两个娼妓的欢心一样。可是怎么办呢?她没有什么过错呀。他给她的钱少了,她对他的热情就会减少,她就不会再给他说一些使他神魂颠倒的甜言蜜语了。为了炫耀自己,他常常把情妇信上的话念给同事听,要他们知道她多么温柔,却从不向他们透露他花了多少钱供养她:不管他送给她什么,一张照片上的题词也好,电报上最后的客套话也好,这些最简单、最珍贵的语言也都是金钱转化成的。即使他避而不说拉谢尔难得的温存是用高价买来的,我们也不能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尊和虚荣,尽管这个简单片面的推理常被人荒谬地用到所有花钱供养女人的情夫和许许多多丈夫身上。圣卢不是傻瓜。他清楚,那些满足虚荣心的一切快乐,凭他高贵的门第和英俊的面孔,他不花一分钱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相反,他和拉谢尔的暧昧关系只能使他同上流社会疏远,使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贬值。他这种想显示自己不花一分钱就赢得恋人绵绵情意的自尊心,不过是爱情的衍生物,是需要向自己同时也向别人表明,他被心爱的人深深地热爱着。拉谢尔朝我们走过来,那两个女人也上了车。但是,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的名字,如同她们的假水獭皮围巾和时装百货商店职员装模作样的神态一样,使新拉谢尔的形象延续了一会儿。在这一瞬间,圣卢想象出巴黎比加勒广场的生活,陌生的朋友,肮脏的钱财,盲目作乐的下午;他似乎感到连接克利希林荫道的各条大街上,阳光不如从前他和他情妇散步时那样明媚灿烂了,因为爱情和同爱情形影不离的痛苦,就象酒醉心明一样,能使我们的感觉变得细腻。他想象在巴黎似乎还有一个城中城;他觉得,同拉谢尔交往就象在探索一种一无所知的生活,因为尽管拉谢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象是他的同类,但是她和他的共同生活毕竟是她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宝贵的一部分,因为他给她的钱数不胜数,这能使她受到她的女友们的羡慕,同时又能使她有一天攒足钱后隐居乡下或跻身于大剧院。罗贝本想问她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是谁,如果她去她们的车厢,她们会给她讲些什么,她和她的女伴们在一起将怎样度过这一天。他想,如果他和我不在场,她们溜完冰可能会到奥林匹亚酒店寻找高级消遣。有一刻功夫,奥林匹亚酒店及周围的一切——他一向都很讨厌这些地方——使他既好奇又痛苦;科马丁街的明媚春光使他产生了一丝怀旧情愫,假如拉谢尔不曾同他相识,呆会儿她也许会到那条街上去挣一个金路易。可是,向拉谢尔提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意思呢?不用问他就知道,她的回答不是沉默,便是谎言,或是什么不说明任何问题却会给他带来痛苦的话。两个拉谢尔持续了很长时间。列车员要关车门了,我们赶紧登上了一个头等车厢。拉谢尔珠围翠绕,这让罗贝再次感到她是一个无价之宝。他抚摸着她,又把她嵌入他的心中,在心里默默地凝视着,就和从前一贯做的那样——除了他看见她在比加勒广场上那一瞬间的印象以外——火车开动了。
她确实有点“文学天赋”。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谈书,谈新艺术和托尔斯泰主义,只是偶尔停下来责备罗贝酒喝得太多。
“啊!要是你能和我生活一年,你瞧吧,我就光让你喝水,你活得会比现在更好。”
“一言为定,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
“可是你知道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她对戏剧艺术态度十分认真)。况且,你家里人会怎么讲?”
接着,她开始在我面前大肆谴责罗贝的家庭。我感到她的责备非常正确,圣卢也完全赞同她的看法,不过,他却违抗她的禁令,不停地喝着香槟酒。我也认为他饮酒不好,并且感到她对他的影响不坏,我准备劝他不必管家里人怎么讲。谈话间我不慎提到德雷福斯,这个年轻的女人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可怜的受苦人,”她呜咽道,“他们要让他死在那里。”
“放心吧,塞塞尔,他会回来的,他一定会释放,一定会得到昭雪。”
“可是等不到那天他就可能死了!不过至少他的子女会有清白的名声。可是一想到他受的苦,我心里就难过死了。您能相信吗?罗贝的母亲,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竟会说即使他无罪,也要让他呆在魔鬼岛。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是的,一点不错,她是说过,”罗贝确认道。“她是我母亲,我不好反驳,不过有一点我敢说,她不象塞塞尔这样富有同情心。”
圣卢对我说,和拉谢尔共进午餐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可事实上,这一类午餐总是不欢而散。因为圣卢同他的情妇一到公共场所,就会胡思乱想,总感到他情妇的眼睛老在男人身上打转,他就会变得闷闷不乐;她发觉他情绪不好,可能会开他的玩笑,给他火上浇油。但更经常的是,因为圣卢说话的语气伤害了她愚蠢的自尊心,她故意装出不想为他解除烦恼的样子,假装目不转睛地看这个或那个男顾客,再说,这也不总是在演戏。的确,当他们去剧院或咖啡馆时,只要他们的邻座——甚至是他们乘坐的出租马车的车夫——稍有一点风度,嫉妒心就会向罗贝发出信号,他会比他的情妇先注意到那个人;他立即把那人看作下流坯,也就是他在巴尔贝克同我讲起过的那种道德败坏、玩弄女性的人,他央求他的情妇不要看那个人,这样对她反倒是个提醒。但有时她发现罗贝的怀疑中蕴含着鉴赏力,她最后会不再开他的玩笑,让他放下心来,同意给她跑腿买东西,这样她就有时间同那个陌生人交谈几句,常常是订个约会时间或还来得及去偷一次情。
我们刚进饭店,我就发现罗贝露出了担心的神色,因为他一进门就发现——在巴尔贝克时,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领班埃梅站在他那帮平凡的同事中,显得容光焕发,彬彬有礼,毫不做作地散发出一股大凡长有轻盈头发和希腊式鼻子的人在好几年中都会散发的浪漫气息。正因为如此,他在那些侍者堆里显得与众不同。而他的同事几乎都上了年纪,猥猥琐琐,好似伪善的本堂神甫或假装虔诚的忏悔人。他们更象旧时代的喜剧演员,有一个方糖般的脑门,一般只有在观众很少的小剧院里,在陈列着一幅幅有不胜今昔之感的古老剧照的休息厅内,才能看到这种喜剧演员扮演的侍仆或古罗马大祭司长的剧照,只有在这些剧照上才有这种脑门;而这个饭店仿佛经过了精心挑选,也可能是在保存传统,把那些喜剧演员的庄重模式全都保留下来了。遗憾的是,偏偏是埃梅认出了我们,走过来给我们开票,而那些轻歌剧中的大祭司长们却向其他餐桌走去。埃梅问我外祖母身体怎样,我向他了解他妻儿的近况。他充满感情地给我作了介绍,因为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男子。他看上去聪明,充满活力,待人彬彬有礼。圣卢的情妇开始目不转睛地端详他了。但埃梅那双凹陷的眼睛深藏在毫无表情的脸中间,没有流露出任何反应,浅度近视使他的眸子看上去莫测高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