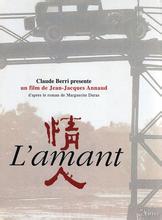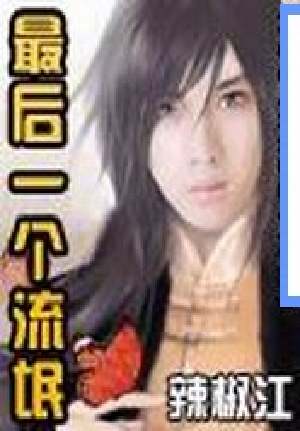一个人的圣经-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宁可相信。
“不妨一试,”这主摆掇你,笑容可掬。
你摇摇头,无心做这类蠢事。
“简直是天衣无缝,比花岗岩还坚固,好一块磐石!”这主围著石头转,咽舌不已。
磐石不磐石与你又有何相干?
“多麽牢固坚实的地基呀,不用真可惜!”这主止不住感慨。
你一不立碑,二不修墓,要它做甚麽?
“娜娜看,娜娜看呀,”这主双手抱住石头不放。
你横竖也没这麽大气力。
“那怕用脚踹也纹丝不动。”
毫无疑议,你自然承认,可不觉还是用脚尖碰了碰。
这主便来劲了,摆掇你:
“站上去试试!”
有甚麽可试的?可经不起这人鼓动,你站了上去。
“别动—.”这主围著石头,当然也在你周遭转了一圈,也不知审视的是石头还是你,你不免也追随他的目光,也转了一圈,在那石头上面。
此刻这主便两眼望你,笑眯眯,语调亲切:
“是不是?不可动摇—.”
说的当然是石头,而非你。你报以微笑,正要下来,这主却抬起一只手阻止你:
“且慢!”
抬起的那手又伸出食指,你便也望著那竖起的食指,听他说下去。
“你看,不能不承认这基础牢固坚实而不可动摇吧?”
你只好再度肯首。
“感觉”下!
这主指著你脚下的石头。你不明白要你感觉的是甚麽,总归脚已经站在他那石头上了。
“感觉到没有?”这主问。
你不知道这主要你感觉的是石头还是你的脚?”
这主手指随即上扬,指的你头顶,你不由得仰头望天。
“这天多麽明亮,多麽纯净,透明无底,令人心胸开阔!”
你听见这主在说,而阳光刺眼。
“看见甚麽?说说看,看见甚麽就说甚麽!”这主问。
空空的天你努力去看,却甚麽也没看见,只有儿最眩。
“再好好瞧瞧!”
“到底要看甚麽?”你不得不问。
““点不掺假的天空,货真价实,真正光明的天空!”
你说阳光刺眼。
“这就对啦。”
“对了甚麽?”你闭上眼问,视网膜上一片金星,站立不住了,正要从石头上下来,又听见他在耳边提醒。
“对就对在景眩的是你而不是石头。”
“那当然……”你已经糊涂了。
“你不是石头!”这主说得斩钉截铁。
“当然不是石头,”你承认,
“可以下来了吧一.”
“你远不如这石头坚硬,说的是你,”
“是不如——”你顺应他,刚要迈步下来。
“别急,可站在石头上看得比你下来看得要远,是不是?”
“自然是这样的。”你不觉顺应他。
一那麽,远方,你正前方,别顾脚下,说的是朝前看,看见甚麽了?”
“地平线?”一针一算会甚麽,哪里还看不见地平线—.说的是地平线之上,好好瞧瞧
“瞧甚麽呢?”
“你难道没看见?”
“不就是天?”
“再仔细看看,”
“不行!你说你眼花了。五任十。一…:
“这就对啦,要甚麽颜色就有甚风,这主提示你:
“这世界多么光辉夺目!”
你站立不住,弯腰趴在石头上求助,想呕吐。
“把嘴张开!该喊就喊,该叫就叫!”
你於是便在这主指挥下,扯直喉咙,声嘶力竭吼叫,又止不住嗯心,在这顽石或是基石上吐出一摊苦水。
正义也好—理想也好,德行和最科学的主义,以及天降大任於斯人,苦宜一心智,劳其筋骨,不断革命,牺牲再牺牲,上帝或救世主,小而言之的英雄,更小而言之的模范,大而言之的国家和在国家之上的党都建立在这麽块石头上。
你一开口喊叫,便上了这主的圈套。你要找寻的正义便是这主,你便替这主厮杀,你就不得不喊这主的口号,你就失去了自己的言语,鸡鹉学舌说出的都是鸟话,你就被改造了,抹去了记忆,丧失了脑子,就成了这主的信徒,不信也得信,成了这主的走卒,这主的打手,为这主而牺牲,等用完了再把你获到这主的祭坛上,为这主陪葬或是焚烧,以榇托这主光辉的形象,你的灰烬都得随这主的风飘荡,直到这主彻底安息了,尘埃落地,你就如同那无数尘埃,也没了踪迹。
21
林从大楼门口存自行车的棚子里低头推车出来,这些日子一直避他。他把车横在出口,故意撩拨前轮,碰了下林的车。林这才抬头看他一眼,勉强一笑,有点苦涩,还带点歉意,倒像是自己不当心碰上他的车似的。
“一起走吧!”他说。
可林无意骑上车,不像以往那样心领神会,二刖一後隔开段距离,去幽会的地点,再说这大革命弄得公园夜间全都关闭了。他们推车走了一段路,竟无话可说。沿街满墙这时都是大学造反派的标语,盖过了血统红卫兵横扫?切牛鬼蛇神的那类口号,点名直指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副总理。
“余秋里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谭震林你的丧钟敲响了!”
林已摘掉了红袖章二条青灰的长毛围巾包住头脸,尽量掩盖自己不再引起人注意,混同在街上灰蓝棉衣的行人中,也看不出她的风韵了。餐馆夜晚都早早关门,无处可去又无话可说,两人推著车在寒风中走,分明隔开距离。一阵阵风沙扬起大字报的碎片在街灯下飘。
他觉得有点悲壮,面临的是为正义殊死斗争,他同林的恋情却眼看就要结束,又不免感到凄凉。他不是不想恢复同林的关系,但怎样才能切入这话题,在平等的基础上扭转局面,不只是接受林赏赐的爱。他便问起林的父母,表示关心。林没有回答,又默默益望口走了一段路,依然找不到话沟通。
“你父亲历史好像有问题,”还是林先说了。
“甚麽问题一.”他吃了一惊。
“我不过是提醒你,”林说得很平淡。
“他甚麽党派都没参加过!;”他立即反驳,也是自卫的本能。
“好像……”林没说下去,打住了。
“好像甚麽一.”他停下脚步问。
“我只是听说那麽一句半句的。”
林继续推车并不看他,依然凌驾在他之上,是提醒也是关照,关照他不要犯狂,尽管也还在庇护他,但他听出这已不是爱了,仿佛他掩盖了身世,这关照也包含怀疑!受到污染。他止不住辩解:
“我父亲解放前当过银行和一个轮船公司的部门主任,也当过记者,是一家私人的商业报纸,这又怎样?”
他即刻能记起的是小时候他父亲藏在家中五斗柜底下装银圆的鞋盒子里那本毛遂纸的小册子,毛的一新民主主义论一,但他没说。说这也无用,他感到委屈为他父亲还首先不是他自己。
“他们说!你父亲是高级职员——”
“这又怎麽的?也还是雇口斗,还是给解雇了!解放前就失业过。他从来也不是资本家,也没当过资方代理人!—一
地义愤了,又立刻觉得软弱,无法再取得林的信任。
林不说话了。
他在一条刚贴上的大标语前踩下自行车的撑子,站住追问:
“还有甚麽?!谁说的?”
林扶住车!避同他绍面,低下头说,
“你不要问知道就行了!”
前面
“夥刷标语的青年男女拎起地上的浆糊和墨桶,骑上车走了,墙上刚写的标语墨汁还在往下流。
“你躲我就因为这个?”他大声问。
“当然不最,”林依然不看他,又补上一句,声音很轻,
“最你要同我断的。”
“我想你,真的,很想你!”
他声音很响,却又感到无力和绝望。
“算了吧,不可能了:….”林低声说,避开他的目光,扭头推车要走。红手抓住林的车把手,林却把头理得更低,说别这样,让我走,我只是告诉你你父亲历史有问题——”
“谁说的?政治部的人?远是大年?”他追问,止不住愤怒。
林挺身转过脸去,望著街上的车辆和马路边不断过去的自行车。刻父
“没划成右派——。他还企图声辩—这又是他要遗忘的。他记得她母亲说过—总算都过去啦,那是他母亲还在世他还上大学回家过春节的时候。
“不,不景这问题…”林扭转车把手,脚登上车踏子。
“那是甚麽问题?”他握住林的车把不放。
“他们说的是私藏枪一…”林咬住嘴唇,跨上车,猛的一蹬上车走了。他剽.—刘轰响—还似乎看见林泪眼汪汪闪而过—也许是错觉—也许是他顾影———林骑针J围加包住头的背影和路上那许多身影混同—灯柱下破纸一和尘土飞扬—不。会便无法分办了。大概就在那时候他蹭到了墙上刚贴的标语,弄上一衣袖的墨迹和浆糊,所以牢牢记得同林分手时的情景。
他心头堵塞,狼狈不堪,没有就骑上车。私藏枪技这沉重的字眼足以令他晕旋,等回味过来这话的含意,便注定他非造反到底不可。
他们”帮子二十多人闯到中南海边的胡同里,在警卫森严的一座赭红的大门口,要求那位声称代表党中央的首长去他们机关认错,为打成反党的干部和群众平反。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坐镇这要职之前早已有过上将军衔的老革命居然接见了他们,比起他们机关里躲在办公室里那些谨小慎微挤不出一句多话的领导干部,毕竟气度非凡,堂堂正正端坐在那异常宽大的办公桌前的皮靠椅上,也不起身。
“我不逢迎你们,我见过的群众多了,我干革命搞群众运动的时候,你们这些小青年还不知在哪里,这我倒不是倚老卖老。”首长先说话了,声音洪亮也不是装出来的,那番态度和腔调依然像在会场做报告一样。
“你们年轻人要造反,这好嘛!我也造过反,革过命,人家也革过我,我也犯过错误,比你们的经验总多一些。我讲了一些错话,伤害了”些同志的感情,大家有些义愤,我在这里向同志们道歉。还要怎样呢?你们就不会犯错误?就永远正确?我可不敢讲这话,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正确!不允许怀疑,你们哪一个就不会犯错误?哈哈—.”
这群乌合之众,来的时候一个个气势汹汹,斗志昂扬,这时都乖巧了,竟躬听教训,无人吭声。他听出了弦外之音,老头子的忿懑和暗藏的威胁。他还不得不站出来,谁叫他承担起这乌合之众的头头,於是问:
“您是不是知道,您动员报告之後当夜人人过关检查?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上百人,还有许多人都整了材料。您能不能指示党委宣布平反,当众销毁这些材料?”
“各有各的帐,你们党委是党委的问题,群众就没有问题?我打不了保票,我已经讲过了,我收回的是我讲的话!我个人讲的那些话!”
首长不厌烦了,站了起来。
“那么,您能不能在您做报告的同样场合,再说一遍这些诰?”他也不能退却。
“这要党中央批准,我是给党做工作嘛,也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可以随便讲话Q”
“那您做的动员报告又是谁批准的?”
这就到了禁区,他也感了这话的分量。首长凝视他,两道浓眉花白,冷冷说道:
“我讲的话,我个人承担,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