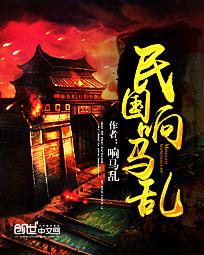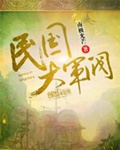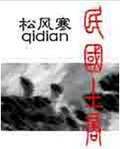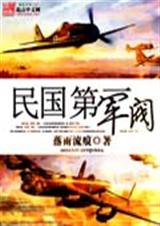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看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即静坐恭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脸上被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临终前,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
【传道】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阴阳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有次与学生讲《说文》,说了“荠”字之字形、音韵、训诂,最后忽然说:“你们记着,荠菜馅的饺子最好吃!”全班大笑,于是对这个“荠”字印象深刻。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
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姜亮夫惊叹于陈寅恪的语言广博,他对老师黄侃说:“我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寅恪先生无法比!”黄侃说:“这话你也不必这样讲,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够懂八九国的语言呢?他们难道没有成绩吗?王念孙虽然一样外文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学者吗?难道他没有成绩吗?所以学问的问题,只问你钻研不钻研,钻研总是有路子,你不钻研就什么路子都没有。个人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钻研。”听了这番话,姜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程千帆回忆老师讲课:“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程千帆还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弥留之时,他说不得话,手却指向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来,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师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大家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前几日学生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老师没能作答。原来,老师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所在。
【大节】
一九○三年,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在孙中山等人影响下,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一个思想重镇,文普通学堂则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此时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很快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后终因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后,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8年,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当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于揭示处,要开除田桓的学籍,全学堂一时哗然。黄侃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几天,田桓带头剪辫,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鄂督陈夔龙遣吏捕捉黄侃,黄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黄侃遭到清政府通缉,次年逃回日本,继续在报上鼓吹革命,先后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专一之驱满主义》和《讨满洲檄》等文章。
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1911年,黄侃在《大江报》上撰文,宣称:“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黄侃的文章引起广泛震动,结果导致《大江报》被封,主编詹大悲被捕。十月十日,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等人会于武昌,并参加军政府工作。武昌首义失败后,黄侃返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二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蕲春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会员、“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编、乡人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为黄设宴洗尘。席中,论及清廷的腐败、蓬勃高涨的革命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助酒性,撰写了一篇时评。
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卑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子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据言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黄侃的老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