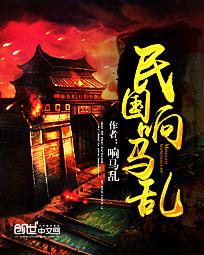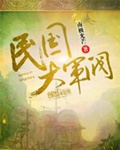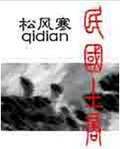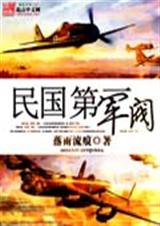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余英时挽老师钱穆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七、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辫子】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