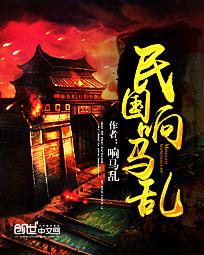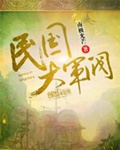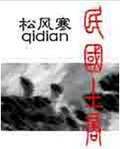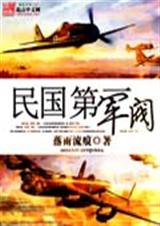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留学的吴宓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和表弟俞大维的一起去听了吴宓的演讲,陈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在与陈寅恪的交往中,吴宓很快为陈的博学所折服。吴宓发现,陈寅恪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吴宓对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空轩诗话》中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
在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下,吴宓学业日渐精进,特别是“红学”研究更是另辟蹊径,终成一代宗师。为此,吴宓终生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1944年,吴宓离开昆明,到成都度年假,他此行的目的是探望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好友陈寅恪,并和陈朝夕相处。此后,吴宓留在燕京大学任教,与陈寅恪成为同事。
1961年,吴宓从四川到广州探望陈寅恪。当时正值雨季,陈寅恪得知吴宓即将来访的消息后,忧喜参半。他事先写了一封信,不厌其烦地告诉吴宓,到了广州后如何排队搭三轮车,如何换车,随身该带多少粮票。并特地嘱咐,广州夜间很凉,要注意等等,无微不至。
这年8月,吴宓一路颠踬,夜里12点终于到达了中山大学校园内的陈寅恪的住所,入门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视物,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却坚持不去休息,要在客厅等待“雨僧兄”。吴宓见此情景,心中感慨万千。吴宓在广州仅仅逗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怕他路费不够,硬塞一些钱给他,并作诗一首相赠:“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71年,当时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顾自己的处境,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一去便如大海,让吴宓枉耗牵挂。然而,吴宓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唐筼夫妇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悲愤中离开世间。
【激恋】
陈寅恪曾说,吴宓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1918年11月,在美国留学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向吴宓介绍自己的妹妹陈心一。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在浙江定海县任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条件苛刻。陈烈勋在信中说,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在《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看到过吴宓的诗文,并见过《清华周刊》上刊登的吴宓的照片,对吴宓甚是仰慕,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认可,同时让同学朱君毅托其未婚妻毛彦文考察陈心一。
毛彦文考察后告诉吴宓:“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1921年8月,刚回国不久的吴宓便匆匆赶往杭州,与陈心一见面。吴、陈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相谈甚欢。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迅速“闪婚”。
吴宓婚后,与妻子育有三个女儿。陈心一“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称得上一个贤妻良母,但吴宓不满足于此,他对她思维迟钝、不善辞令、拙于交际和缺乏文学造诣等深表不满。婚后,吴宓对在清华读书时就神交已久的毛彦文很是倾心。在经过了多番思虑考量后,吴宓终于决定和陈心一离婚,这段勉强维持了八年的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1929年,为了筹集离婚费用,吴宓四处借贷,八方求援,甚至还向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行为,劝解无效后,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为此,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绝交。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虽与陈心一分居,但吴宓仍负担陈的生活,他每月领到薪水后,必到陈的住处交与陈。姚文青中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吴宓对于和陈心一的婚事,曾多次表示悔恨。当陈烈勋敦劝时,吴宓对于这桩未曾谋面的婚事,颇多犹豫,允婚后又毁约,但最后又由于汤用彤的一言成婚。吴宓多年后,对于婚事“悔之不及”,当时他本应留学五年,却因婚事只留学三年而提前回国。
毛彦文是吴宓痴恋一生的女子。毛彦文是吴宓清华同窗朱君毅的表妹,也是他的未婚妻。毛彦文9岁时,其父就将他许配给一位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结婚当日,毛彦文成功逃婚。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表哥朱君毅正式订婚。朱君毅为毛彦文退婚之事曾向同学募捐,故吴宓早知有毛彦文此人,并对毛极为钦佩。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好友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至为欣赏,久而久之便对毛暗生情愫,但碍于同学之谊,只能将爱慕之情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1921年,当吴宓到杭州与陈心一见面时,意外地见到了毛彦文。毛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陈心一告别,与吴宓不期而遇。毛彦文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给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宓婚后不久,朱君毅移情别恋,并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毛彦文无奈,只能求助于吴宓,请吴宓劝说朱。这次劝说,也让吴宓和毛彦文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他深深爱上了毛彦文。朱、毛二人分手后,吴宓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但毛彦文断然拒绝。令毛彦文更加反感的是,吴宓每次写给毛彦文的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的心境。
起初,吴宓深恐毁婚之举有损清誉,准备娶毛彦文为外室,欲享齐人之福。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陈寅恪时,陈道:“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此后,吴宓经历了离与不离得痛苦挣扎后,遂决定与陈心一离婚。吴宓离婚之举遭到朋友们的一致指责,吴父更是公开斥责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气馁。他一边与陈心一离婚,一边更加锲而不舍地追求毛彦文。他表示愿意资助毛彦文出国留学,毛彦文拒绝后,他又以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毛寄钱。在30年代的上海滩,吴宓教授单恋毛彦文女士的话题一时为小报津津乐道,而吴、毛之事经报纸好一番添油加醋的渲染,一时间人尽皆知。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毛彦文。但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在此期间,他又对燕京大学女学生陈仰贤,西洋女子h女郎和m女士心生爱慕。
1931年3月,时在巴黎的吴宓急电在美国的毛彦文,措辞强硬地要求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有人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毛彦文赶到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毛彦文失望至极,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他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说: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转而又去羡慕鲁迅、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回国后,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毛彦文写信给吴宓说:“先生当记得我们俩在东北大学相处的日子,先生在东北大学任教,彦文若不是真心爱先生,会有到东北大学看望先生的那种一举一动吗?”“我把先生送出门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