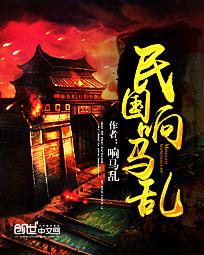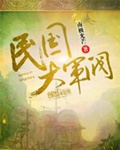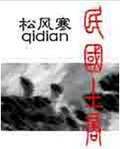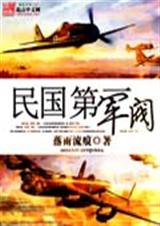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鲁迅病重时,他不看报,不读书,但有一张小画一直在他床边放着。这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画片差不多大,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奔跑,她旁边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怜子】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他说:“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许广平生产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问鲁迅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许广平母子出院回家后,夫妇二人准备给孩子洗澡。鲁迅特别小心,他将开水晾到他认为合适的温度,由许托着孩子,自己动手洗。二人都没有经验,水是温的,风一吹,孩子冻得面色发青,直发抖,两人狼狈不堪,草草了事。结果孩子着了凉,发烧感冒,只能上医院。日后,他们只好请护士来给孩子洗澡,护士提议他们也来学习一下,二人却再不敢自己动手。
许广平在信中曾称呼鲁迅“小白象”,孩子出生后,鲁迅便称呼儿子“小红象”。
周海婴说自己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一次,鲁迅正写文章,周海婴忽然过去,伸出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结果稿纸上立刻出现一大块墨渍,鲁迅虽然心疼自己的心血,但并不对儿子发怒,放下笔,只是说:“唔,你真可恶。”周海婴笑着飞快地逃了。
遇到周海婴淘气时,鲁迅会用报纸卷起来打他两下。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说,打起来声音响,却不痛的。在周海婴的记忆中,父亲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他。
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地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三次。面对一些人的非议,鲁迅显得很坦然,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父亲鲁迅留在周海婴脑海中的印象,是个一直趴在书桌前写作的长者:“他早上醒得比较晚,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蹑手蹑脚的,大家都让我别吵爸爸。这次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传》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小海婴给鲁迅装烟,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应该孝顺父亲,装支烟也是孝顺。”父亲慈爱的回答声还仿佛回响在周海婴的耳畔,“他会说小狗屁,挺乖的啊,好啊”。
上海夏天溽热,每到夏天,周海婴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鲁迅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周海婴遇到父亲写信时,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鲁迅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周海婴另选一张,而他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鲁迅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一次,鲁迅不知为何生气,躺在阳台上,许广平束手无策。三四岁的周海婴觉得父亲躺在阳台上很有趣,便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躺在鲁迅身边。鲁迅看见了,哼了一声“小狗屁”,气就消了,起身下楼吃饭去了。
黄源给鲁迅带去一个高尔基的木雕像,周海婴见后,问道:“这是爸爸?”鲁迅答道:“我哪里配……”许广平在旁提醒海婴:“你猜是谁?你知道,高……”周海婴马上答道:“高尔基。”鲁迅听儿子说对了,回头对黄笑道:“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鲁迅和朋友谈及儿子:“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有次,周海婴竟然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无奈道:“要吃是可以的,自然是不吃的好!”
鲁迅好骂人,却经常被几岁的儿子周海婴骂。朋友们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王映霞就说过:“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林语堂也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1936年,鲁迅病倒后,周海婴经常悄悄钻进鲁迅的卧室,他总想为父亲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火柴放到鲁迅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鲁迅往往故意不提。周海婴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鲁迅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墓碑上的“鲁迅先生之墓”是7岁的周海婴按照许广平的字样临摹的。
√
 ̄炫〃√
 ̄书〃√
 ̄网〃√
 ̄小〃√
 ̄说〃√
 ̄下〃√
 ̄载〃√
 ̄网〃√
【逸事】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父。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冢。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冢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留学日本时,鲁迅与许寿裳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依据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的日语很流利,朋友们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看病,总是请他陪着同去。这样一来,医院里雇的翻译以为鲁迅是来抢生意的,对他自然有意见;而账房先生一看病人有自带的翻译,以为是有钱人,便狠狠宰他们一笔。
1919年末,鲁迅到绍兴接母亲北上。他们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南站,一出车站,小汽车便来兜生意。他们上了一辆,谁知竟是“野鸡”汽车,到五马路被敲了竹杠,多花了好几块大洋。当晚,他们投宿的那家旅馆也是个“野鸡”客栈,住一晚要价8元,鲁迅很不高兴,连夜乘快车到南京,自己坐二等车厢,让母亲坐卧车,天不亮就到达了南京。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家中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时鲁迅刚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大,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