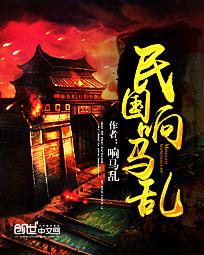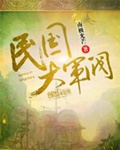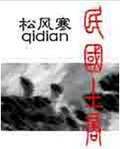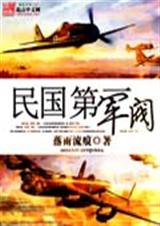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9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永玉回忆,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写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晚年,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文论】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感兴趣,是从医书中知道鱼刺卡喉可用猫口涎液治愈。第二次对书感兴趣,是读《西游记》时,培养了他的想象能力,使他“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以为自己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此书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觉得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趣。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之所以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独立】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两年半,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他并没有去求助亲戚熊希龄。湘西的上层以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熊希龄的弟弟熊捷三是沈从文的七姨父;沈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同盟会会员,护法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晚年有“湘西太上皇”之称)曾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四弟熊焘龄;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娶了田应诏的女儿;熊捷三曾想让沈从文成为自己的女婿……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感到头晕目眩,沈从文却对他说:“并不复杂。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
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工作,熊希龄对这位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经常同沈一起谈时事、聊哲学,畅谈到深夜。二人谈话,往往是熊提出各种问题,沈作答。后来沈回忆此事,认为是熊是有意在考他。一次,熊不经意地问道:“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沈答:“我想独立。”熊又问:“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沈答:“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熊打量着这位年轻同乡,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
内战爆发后,沈从文多次撰文,表示反对党争,反对内战,他对国共两党都颇有微词,认为内战时“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闻一多邀请沈从文参加民盟,还特地找沈谈话,但沈以“不懂”婉拒。1948年,萧乾邀请沈从文参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刊物《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的名单上签名。沈看着名单,轻轻又决然地说:“我不参加。”
沈从文常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
沈从文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多次撰文批驳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1946年10月,沈接受《益世报》的采访,说对一些到处“出风头”的作家“爱莫能同意”,其中包括: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他本意是举例说明许多文学天才都因政治而葬送了,但却把一干革命作家得罪了干净。此篇访谈见报后,引来一片攻击、嘲讽之声,默涵在《“清高”和“寂寞”》一文中说,沈从文与国民党的调调一致,“关麟徵、陈立夫是准会感谢他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的”。
1948年11月,沈从文与冯至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过一次争论。
沈:“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红绿灯是个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冯无言。
抗战胜利直至解放前,沈从文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他的立场让“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都颇为恼火。巴金、李健吾担心沈的处境,让汪曾祺写信给沈,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文,还是写小说为好。汪曾祺曾一连两次写信劝说老师。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时,沈从文应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之请,写了回忆熊的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其中叙述了湘西一带地主与佃户之间和谐共处的民俗风情。此文日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被指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
50年代,全国大批武训,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沈从文觉得这场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
1952年,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周培源、沈从文、冯至等人吃饭,席间,李维汉对众人说,希望他们积极入党,或者加入民主党派,比如九三学社。在场的周培源迅速加入九三学社,很快成为中央委员,后又担任副主席。对此,沈从文说:“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博物馆的领导找沈从文谈话,说上头交代过,沈有条件,政治上过得去,要争取入党,沈从文回答:“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一次谈话结束时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1964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率领师生于海甸区(今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做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
【感怀】
沈从文每读一本书,都喜欢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或记那天的天气,或是一点感慨。他在一本书后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適,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1946年8月31日,沈从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自承“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的情形,“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20世纪50年代末,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新中国成立后,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感慨道:“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浑朴】
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对北京极为失望,他发现,当官的管什么就卖什么,管北京市的拆城墙砖卖,管天坛的伐树卖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宫的卖雍和宫里的东西,管故宫的将善本书抵押到银行;财政部、外交部举外债;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个朋友,门房就要伸手要钱。
看门人向来访的客人要好处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沈从文发表文章的《晨报》的看门人也不例外,无论沈去领取多少钱的稿费,都要先给看门人送钱,他才肯进去通报。一次沈领了十几块钱稿费,看门人追着要钱,沈慌忙将支票递给他,就赶紧跑掉了。
对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学生杜运燮颇觉奇怪,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