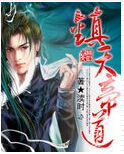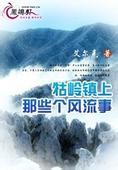南河镇-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被扇得眼花缭乱,佘大勇一时间什么也看不清。佘大花偷偷地左右看了看,发现跟他们跪在一起的,还有穿着孝衣孝裙的小姑明儿跟小姨余儿。她姑父马子亮跟她姨夫刘子明站在一旁,依偎在他们怀里的,分别是姑表妹马月盈跟姨表弟刘光复。
边鼓声有板有眼,板胡声悠扬婉转,唱腔更是如泣如诉。关中的大人们没有一个不是秦腔迷。送过纸的不论是男是女,都听得如痴如呆。把自己的事三锤两梆子干利索后,帮忙的也都加入到观众的行列。戏班子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近的都自己带着板凳。来得早的更是近水楼台,都坐在了前面。会抽烟的,都悠然自得地端着旱烟袋。烟尽了火也灭了,有的涎水都流出来了,也顾不上擦一擦。不会抽烟的,有的跟着鼓点拍着膝盖打起了节拍,有的甚至泪流满面替古人担起忧来。来得晚的在后面急忙看不着,于是只得放着板凳不坐而站了上去。
远道而来不方便带板凳的,可就委屈了双腿。关中人虽长于圪蹴,但时间长了也难免支持不住,于是干脆脱掉一只鞋垫在了尻子下面。他们的尻子有了着落,腿也得到了解放,却苦了他人的鼻子。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不得不用她们的手帕,不住地驱赶着那一阵阵袭向她们鼻孔的腌酸臭气。
碎崽娃子们最青睐的,是那些会翻没底筋斗的武生;最讨厌的,是那些咿咿呀呀没完没了的老旦。尤其怕她们坐下来唱,她们要是真的坐了下来,他们便再也坐不住了。
每过一会,老地主就要大声的提醒众人一次:“别光顾着看戏,照看好自家的门户!啊——”
多儿长眠后的第一个夜晚,竟是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辆牛车停在了佘福庄的门口。“小伙子都朝出走!枋送来咧。”随着老地主的一声吆喝,涌向门外的人们一时都看得呆了。送来的“五寸橔子”,看起来足有一大拃厚,大头差不多也有一人高,紫檀色的桐油漆闪着亮光,左右两侧沿一周用木条刻成竹节作为装饰,前档上还刻着一个斗大的“福”字。除过底,其他的五个面都微微外鼓,整体呈流线型,看起来既雄伟而又壮观。全虎等四个精壮的小伙子用上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地将棺盖揭开了。柏木散发出的异香立即直扑鼻孔又沁人心脾。整个棺木看不到一丝杂木楔楔,更看不到铁件,全都是用燕尾槽带着骨胶卯结为一体。里面已经糊上的红纸,更给人以温馨的感觉。中国的木匠尤其是枋木匠,讲究的是只用木头而不用其他,就连所谓的“银钉”,也都是用木头做的,两头大中间小呈“线板”型。
“果然是个好东西!”众人赞不绝口地说。
“这是县里一家枋店里的样品,也是老掌柜一手给他自己做的寿材。如今老掌柜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一开始出钱多少他都不卖,后来我跟他说了多儿的身世,听说后他心一软,这才松了口。”老木匠说。
多亏了全虎跟他伙计们!要不是这八九个精壮小伙子,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众人还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爪了。
第十八章陈致远投笔从戎 柳
在一片鼓乐声中,奠酒开始了。余儿、明儿和菊儿相继奠过后,轮到了孙兰玉。在离灵桌十步开外处,孙兰玉款款向前移动了三步后,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她便是优雅的一躬。在后退了两步后,她又款款地向前移了三步,接着又是优雅的一躬。如此反复多次后,她那轻盈的莲步,已经移到了灵桌的跟前。在连上了三炷香后她提了提长裙,先慢慢地跪下左腿,然后又慢慢地跪下右腿。仍然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又缓缓地弯下腰叩了一头。这时,有人将斟满酒的酒盅递给了她。孙兰玉将拿着酒盅的右手缓缓地举过头顶,并同时移到自己的左前方,当右手慢慢地从左前方移到右前方时,酒盅也刚好见底。地上,也立即出现了一条粗细均匀而且圆顺的弧线。周而复始,连着重复了三次后,她先起右腿再起左腿,起身后接着又是深深地一躬,然后才缓缓地退到了一旁。
奠酒在委婉的乐曲声中结束了,围观的人,也全都看得呆了。
“这哪里是奠酒?这简直就是演戏!”不知是谁,突然间冒出了这一句感叹的话。
晚上,自乐班赠送了几折戏后,大家纷纷起哄,一致要孙兰玉唱上一段。孙兰玉推托说自己从来没唱过秦腔,但众人哪里肯信又哪里肯依。见实在推托不掉,孙兰玉这才清了清嗓子,凭着日常所灌的耳音,她唱了《白蛇传》中的一段,叫做《断桥》。
“西湖山水——还——依旧——”第一句唱腔,孙兰玉就博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她不慌不忙,字字紧跟鼓点,句句紧扣板弦,吐字是那样的巧妙,嗓音是那样的圆润,韵味又是那样的地道。把白素贞对丈夫许仙的爱与怨,直表现得淋漓尽致。与那些牵强附会的男声女唱相比,她的女声女唱更显得格外的自然而又纯真。唱完后,掌声和欢呼声更是经久不息。
点戏开始后,余儿点的是折子戏《小姑贤》。小姑,多儿的小姑子,不就是明儿么?这出戏,显然是余儿替多儿点给明儿的。菊儿点的是折子戏是《打神告庙》。她显然也在为多儿打抱不平。最后,柳叶为女儿点了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的名著,十大悲剧之一的《窦娥冤》。全本唱完后,柳叶立即摸出大洋给艺人们每人各赏了一块。这时,架上的公鸡已经在报晓。
第三天迎祭时,八个乐人中两个打手鼓,两个敲手锣,四个吹唢呐走在前面。两个帮忙的抬着祭桌紧随其后,跟在祭桌后面的,是身着孝袍,手提丧棒,低着头弯着腰又趿拉着鞋的佘大勇。佘大勇的后面,是佘家门中的同辈和晚辈。同辈和晚辈先按辈分后按年龄依次排列,大约有十来个人。场面看起来,倒颇有些气派。
身着重孝的余儿,大放悲声地来到了村口。马子亮跟马月盈带着全套的纸扎,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搀孝子的中年女人们赶忙搀住了余儿。男人们也纷纷接过了马子亮带来的纸扎,有花圈,有堂堂,有金童,还有玉女。
“孝子!孝孙!孝侄孙!就——位——,鼓乐!齐——鸣——”老地主一声带着拖腔的吆喝声过后,鼓乐顿时大作,余儿更是放声大哭,马月盈也伤心地跟着嚎啕了起来。围观者亦无不唏嘘落泪。孝子们都跟在佘大勇的后面,依次地跪倒在尘埃。
“一叩首——”随着老地主的吆喝,孝子们跟着佘大勇应声齐刷刷地爬倒在地。在二叩首,三叩首后,受迎的人在前,孝子们紧随其后,又浩浩荡荡地返回了佘福庄。。。。。。
巳时许,开始入殓。八个乐人倾巢出动鼓乐震天。在孙兰玉跟菊儿的招呼下,七十子兄弟将多儿那已经僵硬的,轻飘飘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那口沉重的,异香扑鼻的柏木棺材。
蒙脸纸被拿掉了。绕着棺材,亲朋好友们慢慢地移动着脚步,向这个苦命的人儿,做着最后的诀别。看着多儿那跟巴掌一样大的面孔,那些不相干的人都心里一酸不由自主地抹起了眼泪。受到感染,佘大勇跟佘大花也失声恸哭。
柳叶跟余儿一声没哭出,先闭了气晕倒在地。慌得孙兰玉跟菊儿一人一个将这娘儿俩搂在怀里,一面掐着人中一面连声地呼唤着。柳叶跟余儿瞪着双眼又大张着嘴巴,却一滴眼泪没有,一声也哭不出来。众人更慌作一团,连鼓乐声,也戛然而止了。
紧急关头,老神仙不失时机地赶到了。急忙拿出银针,他一人一根地刺进了这娘儿俩的人中。柳叶跟余儿这才泪如雨下,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声吼喊后,全虎跟他的三个伙计,又将那扇沉重的柏木棺盖扣了上去。老木匠拿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斧头跟凿子,一边开卯一边将四个线板形的银钉砸了进去。
“多儿!是妈害了你。。。。。。”柳叶不住地捶打着棺盖。余儿跟明儿更哭得死去活来。刘子明、马子亮、孙兰玉跟菊儿顿时潸然泪下,众人也无不为之动容。
苍天啊!你既然把久别重逢的欢乐赐给了人间,为什么又将生离死别的痛苦,强加给了苍生?
多儿没有儿媳,“扫墓”一事,只能由门中的一个侄媳妇来代劳。这个侄媳妇也是一身重孝。她的娘舅左手提着放有高粱穗子的斗,右手搀扶着哭哭啼啼的外甥女已先行了一步,去履行那因隆重而必不可少的,却又完全是象征性的祭扫。
见银钉已经砸好,众人这才狠下心硬着手,将柳叶母女拖到一旁。一声更大的吼喊后,那口沉重的柏木棺材,终于被十几个小伙子抬了起来。全虎用双臂背着大头。因憋足了力气,他那粗壮的双臂上,肌肉已经暴成了一缕又一缕的疙瘩。
“抓牢!抬平!”小伙子们互相打着招呼。
“吃咧糠了。把劲给上!”他们又彼此的警告着。
庞然大物,终于被放在了棺罩的底板上。跟罩的几个人,先用四周描龙画凤的棺罩罩上了棺木,然后又分头整理着四角的挂钩和抬杠。
一条八丈开外的白布,一头被栓在了棺罩上,另一头通过跪在地上的男孝子们的右肩后,被斜拴在同样跪倒在地的佘大勇的身上。男孝子们每人拄着一根用白纸条缠起来的“丧棒”。除了白色的孝袍外,连脚上的鞋,也被缦上了白布,而且必须是趿拉着。看上去越是邋遢,也越好。大概人在悲伤过度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佘大花跟一帮女孝子们,分左右扶着棺罩的两侧。她们也是一身缟素。与男孝子们不同的是,她们头上的孝布,是平平展展地裹上去的,而且脸上多了一块面纱。
佘大勇没有舅舅,只好由他姨夫马子亮来陪同。右手拖着纸盆,马子亮紧紧地跟在佘大勇的侧后方。抬埋的小伙子已各就各位,每角四人共十六人。抬杠已被小伙子们抓在了手里。为随时替换以防不测,老地主还给每个角多配了一个小伙子。
一声吆喝后,男孝子们跟着佘大勇相继地爬了起来。在微微地晃动了一下后,棺罩也离开了地面。男孝子们用纤布拖着棺罩,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一个提着老笼的执事,赶到队伍的最前面。老笼里装满了纸钱,他一边走一边向空中抛撒着。跟在最后面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但却还能扛得起铁头锨的老汉们。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只听“啪”的一声,纸盆已口朝下被马子亮摔在地上打得粉碎。趁孝子们烧纸、化钱、行礼的当儿,抬埋的小伙子们也轻轻地放下了棺罩。他们稍事休息以养精蓄锐。
快到墓地时,那个扫墓的侄媳妇在她娘舅的搀扶下,又回过头哭哭啼啼地将送葬的队伍,迎到了坟地。
棺罩一落地,男女孝子们的哭声也戛然而止。他们纷纷围拢在墓穴的四周,并亲眼看着打墓的小伙子跳下去,又将墓穴象征性的重新清理了一番。在满意后,亲朋好友特别是女婿外甥们,便将事先准备好的铜圆麻钱纷纷地扔进了墓穴。打墓是出大力而又不挣钱的苦累活,亲朋好友特别是女婿外甥们,便变个法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们谢意。
金童和玉女,被放进了墓穴两侧的套穴。两根结实的槐木杠子,也随即横跨在墓穴上。三通沉闷的铳响过后,那口沉重的柏木棺材在一阵呐喊声中,又被小伙子抬了起来。
“玉团!小伙子的屎都叫你当出来了。把劲给足!”
“全虎!身子尽量向后背!”
小伙子们互相叫骂着,提醒着,招呼着。一时插不上手的,也都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