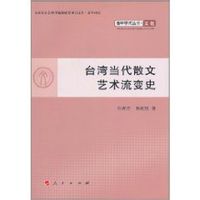余秋雨散文精选-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赌徒暴发户的包围之中,无法展现自身优势,至于为数不多的可以作为城市灵魂的大智者则更会被一片市嚣所淹没。没有构架,他们是脆弱的;没有他们,城市是脆弱的。
不能设想,在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他们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们伸发开去,一座城市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中国也拥有过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师,但他们为了逃避无秩序的拥挤,大多藏身于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里讲学,主持着岳麓书院或白鹿洞书院,与城市关系不大。这个传统,致使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法对城市文明作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扬,而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更是以农村或小镇为表现基点。
因此,突然热闹起来了的中国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们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数千年的封建观念和狎弄意识的战胜。
城市,还有被消蚀的可能。
四
就我个人而言,有时也会被身边的烦嚣搅得头昏脑胀,很想躲开城市,进而对呼唤城市文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经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我们是否一定要去钻别人已想钻出的怪圈?
由此,我又想起了发现渤海国遗迹的清代流放者们。他们被城市放逐了,离别城市那天还涕泪交加,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大都市的废墟,他们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大多会从废墟中领悟城市里功名的无聊,从而获得平静和超越,减轻心头的苦痛。
记得离开渤海国废墟后我们去了不远处的镜泊湖。面对着镜泊湖宁谧的美景,我曾想:废墟傲视着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镜泊湖则又进一步傲视着废墟的短暂。渤海国的废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镜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万多年。废墟是以往功业的遗留,镜泊湖完全离开了功业,因此也没有废墟,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妩媚,妩媚了上万年也不见老,被它妩媚过的建功立业者都一一化作了尘土,而它还是妩媚着。像镜泊湖一样冷清和漠然,多好。
这么一想,我似乎获得了全然解脱,就像老庄哲学曾经给过我的,但很快我又感觉到了这种解脱的虚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于万古湖山,事实上我就连在镜泊湖住上较长时间也会因寂寞、孤独而无法适应。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地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挤的表情来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识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说到底,我是一个世俗之人,我热爱城市。
我对城市的热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它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打扮的邪恶,因而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邪恶更让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恶终究难于控制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们即便无法消灭邪恶也能快步走过它,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大拥挤和大热闹,这便是城市的步履——一种形而上的人类学步履。
49、历史的母本
在中国文化史上,让我佩服的人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很少。
这很自然。因为文人毕竟只是文人,他们或许能写出不少感动人的故事,自己却很少有这种故事。
有时仿佛也出现这种故事了,例如有的文人舍己救驾,有的文人宁死不降,但这又与文化史关系不大。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以忠臣或守将的身份进入了政治史和军事史,而不是以文人的身份推进着文化史。
既能够牵动中国文化史,又能够牵动我们泪眼的人物在哪里?
还有比墨子和屈原更让我们感动的人物吗?
有。他叫司马迁。
我早就确认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却一直难于表达感动的程度。
读者诸君也许会想,司马迁的感人处,不就是以刑残之身写出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嘛,怎么会一直难于表达呢?
是的,我想表达的内容要艰深得多。
今天我想冒一下险,把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试着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前面,触犯了写文章绝不能“由深入浅”的大忌,望读者诸君硬着头皮忍耐一下。
我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因此,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二十五史》的总策划。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束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
这是又一个惊人的奇迹,因为其他民族留存的历史大多以事件的纪年为线索,各种人物只是一个个事件的参与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司马迁把它扭转了过来,以一个个人物为核心,让各种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并不是一种权宜的方法,而是一种大胆的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不是异代师生对已往事件的死记硬背,而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这种轻事而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这位史学家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时具备了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中国长久的专制极权常常会采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这种暴政实行的范围和时段都受到了制衡。人伦之常、人情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第三,他在为中国文化创建“以史立身”、“以人为本”传统的时候,自己正承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
他因几句正常的言论获罪,被处以“宫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生殖器。当时他三十八岁,作为一个年岁已经不轻的大学者,面对如此奇祸,几乎没有例外都会选择赴死,但是,就在这个生死关口上,让我产生巨大感动的吊诡出现了——
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
而且,他一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说到这里,我已经约略勾画了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然而,还是无法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经常会站在几乎占据了整整一堵墙的《二十五史》书柜前长时间发呆。想到一代代金戈铁马、王道霸道、市声田歌都在这里汇聚,而全部汇聚的起点却是那样一位男性:苍白的脸,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还会在各种有关中华文化的豪言壮语、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这种浩荡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逼人的孤独夜晚。
历代中国文人虽然都熟读《史记》,静静一想却会觉得无颜面对那盏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
我曾无数次地去过西安,当地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西安的文章,我总是讷讷难言,心中却一直想着西安东北方向远处滔滔黄河边的龙门——司马迁的出生地。我知道韩城还有司马迁的墓和祠,却又无法预计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迟早还会去一次。
那年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其他人类文明回来,曾到黄帝陵前祭拜,我撰写的祭文上有“禀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过壶口瀑布,黄河上下坚冰如砥,我也向着南边的龙门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为在我看来,黄帝需要禀告,司马迁也需要禀告。
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就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文化君主”。我对他的恭敬,远远超过秦汉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司马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
博学、健康、好奇、善学,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使以前读过的典籍活了起来。他用辽阔的空间来捕捉悠远的时间。他把个人的游历线路作为网兜,捞起了沉在水底的千年珍宝。
因此,要读他笔下的《史记》,首先要读他脚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着文化体质,又衡量着文化责任。
司马迁是二十岁开始漫游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五年。这里出现了一个学术争议: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种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种意见。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司马迁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