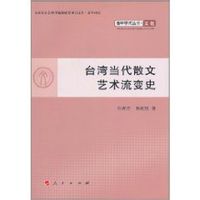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69、关于年龄
人生况味
在十几年前写的一本学术著作中,我曾把“开掘人生况味”作为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个重点,而在诸般况味中,年龄况味又处于独特的地位。
说起来这好像是一般常识,但还是遇到了有趣的驳难。
有人说,人生是为“事业”而存在的,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况味”可言。他们最常用的论据是前苏联的一本流行校旱,主人公在被迫或主动地失去了人生的许多常情常态后,说过一段有关人生的格言,他认为人们如果不为“事业”而牺牲,到临死就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在我看来,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在兵荒马乱中历尽艰险,致病致残,最后还能获得心理调适,十分不易,但人们不应以这样的特例来否定常态。常态往往比特例更难对付,因此也可能更深刻。这就像在饮食中,不能因为接触过了大辛大辣就否定寻常口味,而要把寻常口味调理好,则是天下一切大厨面临的难题。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人生的过程少不了要参与外在的事功,但再显赫的事功也不能导致本末倒置。莱辛说,一位女皇真正动人之处,是她隐约在堂皇政务后那个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身份。莱辛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直取这种身份。狄德罗则说,一位老人巨大的历史功绩,在审美价值上还不及他与夫人临终前的默默拥抱。其实岂止在艺术中,在普遍的人际交往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个自觉自明的人,也就是把握住了人生本味的人。
因此,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