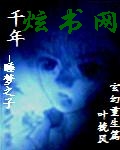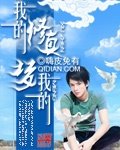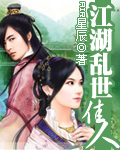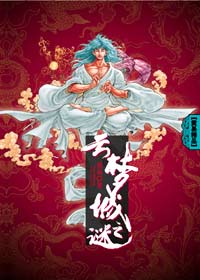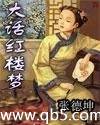乱世强国梦-第8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卷第一百零三章投案自首的尹昌衡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总结四川地区的政治、军事、地理,研究历史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像治国秘宝一样奉献给统治者作参考。其实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四川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充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立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或进入无政府状态;而当天下已定,硝烟散尽之时,这块窝在山地里的盆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版图,需要统治者尽最后的努力来收复它。
四川都督尹昌衡有些心下忐忑地随着蔡锷进了屋,见屋内无人,心中暗喜。他曾在广西任职,与蔡锷是老相识了,如今见与蔡锷单独相处,自然是要指点一二了。
说起尹昌衡,一米八六的个子,仪表堂堂,可做起事,确有点“那个”。咱们先说说这位小尹同志的经历:尹昌衡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先是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次年,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在日本与阎锡山、唐继尧、李烈均、李根源、刘存厚等人交往密切,先后结拜为兄弟。当时复兴会等各种团体都在拉拢争取这些留日士官生,可小尹同志全都摇头回绝,并说道:“本人性素迂,且家赤贫,从小到大,供养全靠清廷。食人之禄,背之不祥。”当然,这个立场与蔡锷所坚持的“军人不党”是不同的,而且很有些反动的意向。由此,他遭到很多讽刺,说他是保皇党。对此,尹昌衡也不辩解,只是冷笑道:“到时候才晓得锅儿是铁造的”。
表面上的沉稳,掩饰不了他内心的高傲,小尹曾有诗云:“我欲目空廿四史,以作胸中数万兵”。由此足以见出,尹昌衡并不想做庸常之辈。归国后,先是到广西任职,巡抚张鸣岐对留日学生戒心重,尹得不到升迁,索性张扬个性,纵情诗酒,狂放不羁,在一次宴会上,竟借酒壮胆,开枪打碎了窗玻璃,还打了时任广西提督的龙济光,如此狂狷,当然无法再在广西立足。于是,他只得重回四川混日子,继续当他的刺儿头。
时值四川操练新军第十七镇,赵尔巽任用亲信,高级官职几乎全部被外省军人所掌控,引起川籍军人的强烈不满。尹昌衡排外情绪尤其炽烈,无形中成了领袖,每于宴会场所,以尹为的川籍军人少不了使酒骂座,公开说外省军人无能。有一次,总督赵尔巽在场,尹昌衡照骂不误,赵尔巽大为惊讶,反问他:“依你说,哪个是知兵的将才?”尹昌衡大言不惭地拍胸道:“国中将才,只有三个:吴禄贞、周道刚,区区在下。”
尹昌衡的狂放,并非无本之源。会打枪带兵,能吟诗作对,文武双全,更难得的是,尹昌衡与遍布四川的袍哥组织关系密切。换句话说,他的本钱是哥老会,有夸海口的资格。
时势造英雄,不久,尹昌衡果然有了登场亮相的机会。成都光复后,当时的局势极为复杂,几种势力,既相互纠葛缠绕,又相互抵触排斥,各自怀有目的、抱负和野心。而文人出身的“长衫客”蒲殿俊大都督,并未察觉到平静水面下的凶险,竟然在东校场举行阅兵式。当说到事先承诺给每个士兵三个月的恩饷因为藩库财政吃紧,要等以后补时。场上便有人高声叫骂:“龟儿子,原来是诳人喽!”另有不少人高喊一声“打起”(四川话:绑票、吃大户之意)。乱兵蜂拥而起,枪声响成一片,涌入成都疯狂掠抢。
身为军政部长的尹昌衡,那天举行阅兵式时也在场,危难之际,军人的沉着和魄力让他脱颖而出。从东校场脱身后,骑马急驰奔6军小学,下令军校学生武装占领有利地形,防止骚乱扩大。稍事布置后,又在乱枪声中奔赴凤凰山,找到新军六十三标标统周骏求援,带兵返回城内平乱,乱乃稍定。
尹昌衡由于与哥老会关系密切,担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即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总舵把子。尹昌衡挂牌子后,并不急于处理堆积如山的公牍,而是成天到各街公口码头去拜客。各公口码头自然隆重接待,为他挂红进酒,阿谀奉承。尹都督有上等好酒量,再披一身红绸,更显得光彩夺目,威风凛然。
官场上的规矩,从来都是上行下效,有尹都督带头,属下也不甘落后。军政部长周骏挂牌“大6公”,巡警总监杨维挂牌“汉兴会”,新成立的公口还有“汉军公”、“福汉公”、“共和公”、“云龙公”、“同庆公”等。街道变成了戏台,到处是背刀挂彩、头顶英雄结、脚登线耳草鞋、腰缠飘带的人物,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此时的四川,俨然成了哥老会的天下。
直到广州军政府电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并且调动滇军和重庆蜀军政府的兵力,有向成都进的迹歇时,尹昌衡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于是,他忽然来了个大变脸,下令取缔哥老会,全成都两百多个公口的招牌一律没收,劈作了柴火。由此看来,军人出身的尹昌衡还有政客的潜质,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什么样的牺牲都在所不惜。经过一番改造,四川军政府成为一个由军人实力派、革命党和立宪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仅如此,尹昌衡还给自己的老同学李根源、李烈钧等写信电,表明自己忠于革命的决心,并一反过去瞧不上“党人”的立场,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想争取个火线入党,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
然而,复兴会却对此并不热烈响应,只是让他先维持好四川的治安,不可再出现类似成都兵变的祸事。而蜀军政府与成都军政府合并,当然也算是一种暂时和解的标志。
要说小尹同志还是很有些头脑的,而且为了好好表现,也是干劲十足。利用他哥老会总舵把子的影响,拉拢哥老会上层,委以官职,同时又巧妙地解散下层,倒也成绩显著。
然而,有了这样一个波折,小尹同志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临时政府会找个机会收拾他。而复兴会对他入会的事情,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态度,也让他坐卧不安。于是,思来想去,他来主动投案自了。当然,也有烧烧香,拜拜肖志华这尊大佛,请求宽大处理。
第一卷第一百零四章当初的理想
如果把尹昌衡看成是乖乖宝,那可就看走了眼了。生长于这样一个大时代,如尹昌衡之辈,何曾不想把握时代的命脉?不想做社会乃至国家的主宰?但当形势展已经不容许他们野心的无限膨胀时,有些人选择了对抗,更多的人则选择了退让,先保住自己已得的利益再说。
表现得恭顺,不给临时政府收拾他的理由,尹昌衡此行的目的绝不是躺倒挨捶那么简单。他现在唯一后悔的便是当初,为什么看不起“党人”,如果自己是复兴会会员,那就是嫡系,何必要担心这,担心那。
而对于蔡锷的好运气,尹昌衡是既羡且妒,又感到无奈。这就是造化,这就是命运,蔡锷和自己一样,也是无党无派,却平步青云,真没地方说理去。
“硕权,川中安定了?”蔡锷和老朋友寒喧了几句,直接问道,毕竟尹昌衡是一方大员,私自跑出来,如果地方出了事,那可是一条不小的罪名。
“应该不会出事。”尹昌衡也不敢一口咬实,含糊地说道:“我也不敢在外时间太久,拜望了总司令,便要赶回去。”
“那你——”蔡锷呵呵一笑,说道:“我明白了,你是心里不托底,跑来烧香拜佛的。”
尹昌衡尴尬地点了点头,说道:“趁总司令还没走,聆听些教诲,以免再行差走错。松坡兄,还请指点一二。”
蔡锷笑着摇头道:“尹长子呀尹长子,总司令说你是小精明,我还不信,没想到真让他给说中了。”
“小精明?”尹昌衡一愣,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蔡锷笑着解释道:“你装了赵尔巽的统子,先恭后倨,将巡防营一举拿下,这事是有吧?平定成都之乱,收缴那些被叛兵劫掠的库银、财物,你没少捞吧?调你在武备学堂时的老师胡景伊到重庆坐镇,而将原蜀军政府的张培爵召到成都任副都督,这是你的小心思吧?消极抵制滇军入川援藏,要‘藏事独任其难’,是害怕云南借机染指川中吧?硕权,你是想当川中王?”
尹昌衡嗓子有些干,起身强笑道:“松坡兄,这你可冤枉小弟了,待我解释,兄再替我在总司令面前分说一二。”
“你先听听我的意见,如何?”蔡锷摆了摆手,示意尹昌衡坐下,缓缓说道:“胡景伊,名声太不好。他老早就挂名同盟会前身的华兴会,可待他当上协统后,同盟会派人去找他联络谋反事宜时,他却恶狠狠地对来人道:‘你们赶快给我离开,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虽然同盟会不比复兴会,但此人官迷心窍,做人相当不仗义。”
“有这等事情?”尹昌衡嘴里苦,他确实不知道此事,此时心中十分懊悔。
蔡锷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杀赵尔巽,没错,用些手段,也无伤大雅,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有起义再加平乱之功,只要把扣下的钱财缴上来,我也可以为你说项开脱。但你拉帮结派,任用亲信,又将川地视为私物,有割据之心,并且影响到整个对藏的战略布局。这些罪名,你能担得下来吗?”
尹昌衡有些目瞪口呆,没想到对他的罪名是现成的,而且一抓一大把。半晌,他的狷介性子又作了,脖子一挺,说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并没有这些心思,松坡兄你是了解我的。”
蔡锷轻轻叹了口气,慢慢喝着茶水,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尹昌衡闷声闷气地问道:“我这次是自投罗网,不知道要如何处置我?”
“自投罗网?”蔡锷冷笑道:“就凭你刚刚组织起来那些由旧巡防营再加哥老会成员的两个师,躲在川中就奈何不了你?痴人说梦!只要新政府一个命令,你还不得乖乖地听从。还是总司令说得对呀,新时代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还有很多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如果不能挣脱时代和私欲合力制造的障碍,那么,昔日的雄鹰也会变成走地鸡。”
尹昌衡眨了眨眼睛,从中听出些有利的信息,急忙站起身,对着蔡锷深深一躬,诚恳地说道:“是我失态了,请松坡兄不要见怪。何去何从,还请松坡兄指点迷津。”
蔡锷伸手拍了拍尹昌衡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什么指点迷津,那都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好好想想,我们当初从军的理想是什么?为什么时过境迁,那种立志报国为民的理想会被扭曲,甚至已经被抛到脑后。你当初曾有诗云:‘我欲目空廿四史,以作胸中数万兵’,这股豪气和胸怀哪里去了?”
尹昌衡低头不语,他们这一批人从军之时,正是甲午之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国人皆曰维新,有志青年东渡日本求学,就是为了挽救这个古老的国家。但经过世事变迁,人事挫磨,理想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圆滑和市侩,是那种政客似的狡猾和猜忌……
“军人还是纯粹一些的好啊!”蔡锷半是感慨半是规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