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分久必合,合而有益。这是包括台湾人民以及海外几千万侨胞在内的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心愿――祖国统一,人民大团圆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那可能就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开端!
第四节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我们乘坐的军舰终于来到了台湾。在台湾的北部港口――基隆码头靠岸。
基隆市位于台湾岛的东北角,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一个港口都市,辖7个区、7个附属岛屿,总面积132。76平方公里,为台湾北部重要的国际商港,加上境内岛屿、港湾、山陵兼具,繁华的港都则局促于山海之间,无论功能及型态上皆具香江风情,犹如一个‘小香港‘。
基隆古名鸡笼,一说因基隆山象鸡笼形状而得名,又一说认为该地以前为高山族凯达喀兰人住地,“鸡笼”是“凯达喀兰”的闽南方言译音。明末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张燮著的《东西洋考》里,就有鸡笼社、鸡笼港、鸡笼城、大鸡笼街等记载。表光绪元年(1875年)设基隆厅时,才把鸡笼改为基隆,其含意是“基地昌隆”。
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鸡笼,1642年被荷兰殖民者所取代,1667年才被郑经(郑成功之子)率部赶走。日本入侵时期(1895年至1945年),设基隆郡基隆街,后来升格为市,1945年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接管后,成为省辖市。辖仁爱、信义、中正、中山、安乐、暖山、七堵等7个区。
市境东、西、南三面环山,但山势不高,多在250公尺以下,北面为港湾,入口处有和平岛和桶盘屿横扼门户,成天然防波堤。气候湿润温和,雨期长,雨量多,人们把基隆市称为“雨都”或“雨港”。温带海洋气候很显著。
基隆有街市始于1723年,1851年开始与外国通商,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正式辟为商埠。1887年建筑基隆至台北铁路,1891年通车。1889年建成第一座码头,日本侵占台湾后大举筑港,分四期于1935年完成,成为现代化商港,现有39个深水泊位,可停靠3万吨级轮船。1945年光复后,增建了仙洞的货柜码头和特种货物码头,以及八斗子渔港。基隆港是仅次于高雄港的第二大港。基隆渔港是台湾重要渔业基地,年渔产量约占全台湾渔产量的五分之一。基隆市在日本入侵时被划为要塞区,现为台湾当局的海军基地。
基隆市的重要工业主要有采煤和造船。基隆港口在台湾经济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市区三面环山,平地狭窄,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基隆亦是旅游胜地,主要游览地有观海亭、慈航寺、佛都图书馆和全身乳白、颇为壮观音菩萨像。有灵泉寺,建于1889年,为基隆最古、最大佛寺,有33尊观音石像排立。有社寮岛蕃字洞和千叠敷海蚀奇观,此外,还有海门天险、清代炮台遗址,以及“仙洞听潮”、万人堆、狮球岭炮台,暖暖水源地等旅游胜地。在自然景观方面,和平岛、八斗子望幽谷等海岸地质景观,情人湖、泰安瀑布、暖东峡谷等山林景观,也很值得游览。此外,基隆沿岸为曲折的岩岸湾澳,大小渔港密集,大武仑、外木山、八斗子、望海巷等各具特色。
基隆庙口小吃是指位于奠济宫附近仁三路和爱四路的小吃摊,约成“L”形,总长约4、5百公尺的区域,聚集不下300多个摊位,经过数十年的演变,这里的摊位不仅按顺序编了号,连招牌都整齐划一,各式小吃种类繁多,各家皆以独创口味招揽顾客,口碑远播,致使基隆庙口小吃名闻全省。
奠济宫建于清风吹清同治12年(1873年),乃漳州籍先民为纪念来此开垦的先祖而建,香火鼎盛,但自从小吃摊声名大噪后,已有油烟盖过香火之势;然于大啖美食之余,别忘到奠济宫细细鉴赏这座百年庙宇,一窥先民精致的雕琢艺术。
庙口小吃以仁三路的摊位历史较久,有很多是日据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共聚集了70多家小吃摊,皆有固定的摊位整齐的招牌,自白天就开始营业;著名的小吃有独树一帜的虾仁羹、天妇罗、泡泡冰和豆签羹等,都让人垂涎不已。
刚到基隆时,上峰将我们安排在市区信四路居往,不久就移居于基隆市的西南远郊--七堵国校官佐招待所(以下简称招待所)。
美其名曰:“校官佐招待所”实际上是不久前的一个大兵营。可能是因为近来台湾局势紧张,部队被调往澎湖、金门、马祖、舟山前沿驻防,兵营临时改为由大陆逃到台湾来的军人家眷暂时住所。实质上就是一个生活条件十分简陋的难民营。
在我的印象中,“校官招待所”地处基隆市的南部远郊,周边已和农户毗邻。不远处就有一些菜地和农民种的大片稻田。
招待所靠公路的北面和营房的西面是砖墙,而东边及南边都是用土坯筑的土墙。大门口还设有岗亭,每天都有士兵在值勤。大门外两边还有几个卖香烟、糖果、香蕉、菠萝、龙眼(桂圆)的小摊。
招待所大门里的左侧,临近北墙盖有一幢面积较大的饭堂,以前可能就是士兵就餐的地方。现在已改成我们几十家眷和孩子们铺张草席或垫点稻草,打地铺住宿的地方。
另外还有七、八个老汉,他们就住在后面伙房旁的两间小屋里。
冲着大门的南边,盖有几十间长长的一排营房(西屋),几乎向南延伸到两百米以外的南墙。
营房的前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操场。场地的东边就是军营的东墙,在墙脚下稀稀疏疏地长着一排既不太高也不太大的树。除此之外,在这个庞大开阔的院子里,你再也找不到另外的一棵树。
我们一批从大陆刚跑到台湾惊魂未定的眷属们,暂住在基隆七堵国的“校官佐招待所”里,每天都在忧心忡忡地过日子。一天三顿饭,中午是大米干饭,早晚两顿都是大米粥。吃的菜中午多是炖冬瓜,早晚拌点黄瓜或萝卜。除此之外,很少吃到其它的菜。至于北方的面食是很难吃到的。
炖冬瓜就是伙房的炊事兵把冬瓜削掉皮,剁成大块块。然后再炒菜的大锅里先放上几块肥大肉或放几片猪板油。在炒菜锅里把它炸出油,直至油渣变成焦黄色,再把冬瓜块倒进锅里,撒上一把盐和虾皮,加上半锅水,用小火慢慢的炖煮。
待到大米饭熟了,在中午12点钟左右,就由炊事兵抬出一桶桶大米饭(半桶),端出一盆盆的炖冬瓜(大半盆)。晴天摆在房前的空地上,雨天放在门前的走廊里。然后家眷们各自盛饭,两三家人蹲在地上围住一盆炖冬瓜,吃饭。
从开饭的场面来看,家眷们似乎也有点半军事化的训练。只是每天的饭菜有些过于单调简单。左一顿冬瓜,右一顿冬瓜。物稀为贵,物多为贱。想必在台湾的蔬菜中,冬瓜的价钱一定是最便宜的了。每天吃冬瓜,直吃得大人叫着没味口。开饭时孩子们见了冬瓜就躲的远远的,也不愿意吃上一口。
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认为台湾是冬瓜的故乡,冬瓜是台湾的土特产。大陆老家地里种的冬瓜,它的瓜种肯定是从台湾传播过去的。这个印象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脑海里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转眼到台湾一个多月了,人们吃饭除了打扫一下门前的卫生和洗洗自己的衣服外,基本上再没有什么事可干。女眷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在拉呱,互相说长道短。
那几个年过花甲的老汉,总是远远地蹲在房前屋头,在无聊地抽着旱烟白话旦。而孩子们每天总是无忧无虑地在玩耍。
至于海峡两边的形势变化和大陆那边的战事他们一概不知,只能望洋兴叹。这些长年累月的流浪逃亡,近乎麻木状态的人们,他们早就没有了八年抗战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目前唯一牵挂的就是他们滞留在大陆的亲人――其中有老人的儿子,女人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们在大陆有的还在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拼命厮杀。有的已经死于沙场,成了无人祭祀的亡灵。还有的已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变为阶下囚,这里面不乏有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战区司令长官。兵团司令、军长、师长,其中有的还被羁押在东北抚顺的战犯所里。更何况团营连排长以下的数以百万计的官兵,他们早已是溃败作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想必是脱掉军装,还原为民了。
这些让人伤心、发愁、担忧的事情,每天都在困挠着人们。在那风云多变,时局动荡,书信难通,无法联系的战争年代里,你在海峡这边,他在海峡的那面,要想得到一点家人的音信,多靠道听途说,然后你再去分析推测。至于事情的真象却无法证实,结果仍然是扑朔迷离……
孰不知?他们的亲人在大陆,有的早已命丧黄泉,战死沙场。甚至有的成为了无名之鬼,永远地踏上了不归路,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与他们的亲人相聚团圆了。
有的被解放军俘虏,有的被逮捕成为阶下囚,在当地服刑。还有的判刑后被押送到万里之外的大西北――宁夏、青海、新疆的劳改农场里去服刑,进行劳动改造,以此获得新生。
然而,基隆七堵国“招待所”的情况,仅仅是几十个因兵灾战祸而造成的难民营的一个缩影。
可怜而又凄凉的眷属们还认为他们的亲人会回来,总有一天团聚的愿望会实现。
纯朴的中国人有一个诚信的观念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即使噩耗传来,已经是老人们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还是希望他们战死的亲人能让别人由前方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绺头发,一根白骨或是一件血衣让他们亲眼看看,亲手给予安葬,使其入土为安,总算有个交待。否则他们会期盼等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只要自已没有死就会苦撑着一直地等下去。望穿泪眼,企盼着会有一天在她们的眼前会发生奇迹――她们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会突然地出现在她们的面前……
譬如在大陆福建沿海的寡妇村里的寡妇们(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不正是因为战祸兵灾给她们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吗?她们不就是这样地期盼等待的吗?
有的少妇等待海峡彼岸当兵的丈夫归来……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已变成了发白齿落的八十老妪,她们像古代的孟姜女一样仍然在痴痴地寻夫……
第九章 惊魂未定 梦断台湾(三)
更新时间2007…11…18 15:41:00 字数:4350
第五节
上个世纪的中叶,即1949年的夏天。在台湾基隆市的郊外――七堵国的国民党军队“校官招待所”里,我们几十家难民,老少一百多人在那里失魂落魄、担惊受怕地生活着,每天都在祈盼着自家的亲人能从大陆那边传来一点消息,或从大陆那面跑过来的人中捎回一封书信,转告一些近来的情况。那将是难民营中最激动人心,人们相互询问,谈论最多的一天。
基隆“招待所”的难民营里,从大陆跑过来的难民在不断地增多。只有极少数的家眷比较幸运,后来他们的男人也从大陆跑了过来,又到国民党的部队里去供职,这才把她们从“招待所”接走。从此,她们的境遇和命运也就随之改变了。
一天下午,在房头突然传出了四川腔调和河南口音的吵骂声……我们几个爱看热闹的孩子急忙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个外号叫“河南大裤裆”的六十多岁的李老汉和一个外号叫“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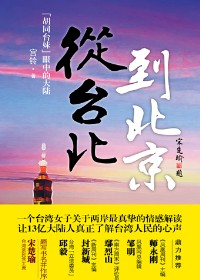
![(家教同人)[屏保系列]浪到底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83/18324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