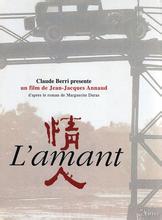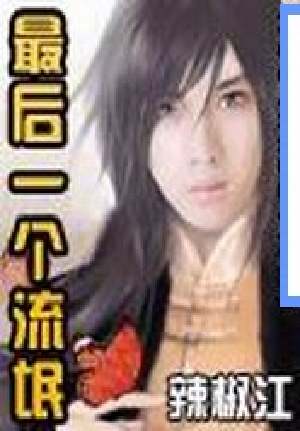一个人的村庄-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对村里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惊奇。他们好像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似的,悠然自若地在我打扫干净的房子里开始了他们的生活。我躲在一个破羊圈里,观察了这一切,直到我坚信再没有半间房子属于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贼一般逃离了那个村子。以后每去一个村庄,我总要仔细眺望一阵,看到炊烟才敢放心走去。
当时这个村子就像一条恭候主人的狗,远远地高翘着一根炊烟的尾巴。还听不到人声。有个两条腿的大东西在我之前穿过荒野,留下很深的两道辙印,我走在其中一条辙印里。身后已经看不到一个村子。我踩起的一小溜尘土缓缓沉落下来,就像曾经做过的、正在失去意义的一些事情。
半小时前,三个骑马人迎面而过时,我就想:我走过的路上不会有我的脚印了。三匹马,十二个钉了铁掌的蹄子一路踏去,我那行本来就没踩清楚的脚印会有幸剩下几个呢。一两天后,再过去一群羊或几辆大车,我的行踪便完全消失了。我的脚印不会比一头牛的蹄印更深更长久地留在大地上,很快我将从我走过的路上彻底失踪。一旦我走出去几十里地,谁也别想找到我。
“那么马二球呢,马二球的房子是哪间?”
我拿着七八个人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打问,开始他们一口咬定村里绝对没有这几个人,他们给我指了一个百里外的村子,让我到那儿去问问。这个村庄也太会打发人,我想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他们肯定像打发我一样,给每位来到村里的陌生人指一个百里外的去处──远远打发走他们。这个村庄因此变得孤远、孤僻了。
村子里只有一条路,路旁胡乱地排着些房子。
我再一次问过来时,有人明显动摇了。
“冯富贵?我咋觉得有这么个人呢。”
“胡扯,就几十户人的村子,有没有谁我不清楚。”
“我也觉得,咋这么熟的名字,越听越熟悉。”
天很快暗下来,夜色使我先前看清的东西又变得模糊,房子和人,正一片一片从眼前消失。我站在暗处,听见一大片慌乱的关门声,接着又是一片开门的声音。黑暗中有一群人走到一起,叽叽喳喳议论起这件事,言语黑糊糊地波动在空气里。
我想,他们大概已弄不清是我找错了地方,还是他们自己错住在别人的村庄。
我想在这个村里过一夜,又不认识一个人。
在我一生中经过的村庄中,有些是在大白天穿过的,那些村庄的形状,村人的长相以及牲口的模样都历历在目。至今我仍清晰地记着给过我一碗凉水的那个村妇,她黄中透黑的脸、粘着几根草叶的蓬乱头发、粗糙的不曾洗干净的双手和那只有一个豁口的大白瓷碗。我仍感激着一头默默目送我走远的黑母牛,我们是在一条窄窄的乡道上相遇的。它见我过来,很礼貌地让开小道,扭过头,目光温和地看着我远去。这是它的道。我在经过别人的村庄和土地,我对如此厚重的恩遇终生感激。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别人的村庄(2)
我尤其感激那些农人,他们宁肯少收些粮食,在他们珍贵的土地中辟出一条又一条路,让我这个流浪人过去。我相信他们不是怕别人留在村里才这样做的。这是人家的地,即使人家全种上粮食不让你过,你也没有办法。一年夏天我就被一片玉米地挡住过。一望无际的一片玉米,长得密密麻麻。我走了几个来回,怎么也找不到穿过它的路。或许种地人原想:不会有人走到这么远,所以没有留路。没办法,我只好在地边搭了个草棚,我打算住一夏天,等种地人收了玉米,把地腾开我再过去。反正我也没太要紧的事。
等待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看玉米的人,在给谁看守也不清楚。我看着玉米一天天成熟,最后一片金黄了,也不见人来收。第一场雪都下过了,还不见人来。我有些着急。谁把这么大一片玉米扔在大地上就不管了,真不像话。会不会是哪个人春天闲得没事,便带上犁头和播种机,无边无际地种了这片玉米。紧接着因为一件更重要的脱不开身的大事,他便把自己种的这块玉米给忘了。我想是这样的。很多人有这种毛病,种的时候图痛快,四处撒种,好像他有多日能。种出来却没力气照管,任其长荒,被草吃掉。或者干脆一走了之,把偌大一片不像样的庄稼扔在大地上。我盖了间又高又大的粮仓,花了一冬天时间把埋在雪中的玉米全收进仓中。这时候我已忘了我要去的地方,雪把我的来路和去路全埋了。我封死粮仓的门,随便选了一个方向又开始游荡了。以后经过这里的人们,看到如此巨大的一仓玉米耸在路旁,惊喜之余,他们会不会想到是我干的呢。
走出很远了,或者说事过多年,每当回头我都看到那幢堆满玉米的粮仓高高耸立在荒野上。我把它留给每一个走过这片远地的人,我知道我再不能回去。
快进村子时,路旁出现了一大片墓地,我数了一下,有上千座坟吧,有些是新堆的,坟土新鲜,花圈虽烂犹存。有些坟头已塌,墓碑倾倒。我断定埋在这儿的,都是我将要去的这个村子里近百年来死掉的人。我停下来,撒了泡尿,是背对着墓地撒的,这是礼貌。尿水到地上很快就不见了,只留下一阵哗哗的水声,在空气中。
这片地方很久没下雨了。
我自己说了一句话。即使一千年没下雨这泡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系好裤子,一屁股坐在一个坟堆上。我感到累了。我屁股下面的这个人可能早不知道累了,不管他是累死的还是老死的,他都早休息好了。我看了看墓碑上的文字:
冯富贵之墓 生于×年×月×日
卒于×年×月×日
我在这片荒野上第一次看到文字,有点欣喜若狂。我掏出本子,记下这个名字,又转了几座坟,记下另几个人的名字。当时没想它的用处,后来进了村子,实在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才突然想到记下的这几个人。
墓地看上去比村子大几十倍,也就是说,这个村里死掉的人远比现在活着的人多得多。这是另一个村子,独碑独墓,一户一户排列着,活人为死人也下了大功夫,花了钱。里面的棺材陪葬品自不用说,光这墓碑,我蹬了一脚,硬邦邦,全是上好的石料,收拾起来足够盖一大院好房子。我曾用四块墓碑围过一个狗窝。我把碑文朝里立成四方形,留一个角做门,上面盖些树枝杂草,真是极好的狗窝。墓碑是我从一个荒坟地挖来的,那片坟地也是多年没人管,有些坟棺材半露在外面,死人的头骨随处可见。我至今记得墓碑上那四个人的名字。奇怪的是在我离开黄沙梁的几年后,竟遇到和那四块墓碑上的名字完全吻合的四个人,他们很快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年,我带他们回到我的故乡──黄沙梁。那时我的一院房子因多年无人住已显得破败,院墙有几处已经倒塌,门锁也锈得塞不进钥匙,我费了很大劲才弄开它,那情景像一个离乡多年的男人回到家里,他的老婆又变成Chu女。我那时候还没娶上老婆,也怪我贪玩,村里有好多漂亮女人,我竟傻傻地没有反应。
别人的村庄(3)
人一生中的某些年龄可能专为某个器官活着。十七岁之前我的手和脚忙忙碌碌全为了一张嘴──吃。三十岁左右的几十年间,我的所有器官又都为那根性器服务,为它手舞足蹈或垂头丧气,为它费尽心机找女人、谋房事。它成了一根指挥棍,起落扬萎皆关全局。人生最后几年,当所有器官懒得动了,便只有靠回味过日子。
当时我所做的一切是否在为以后制造回味呢。我掀开狗窝顶盖,看见我的狗老死在窝里,剩下一堆白骨。它至死未离开这个窝,这座院子。它也活了一辈子。现在发生在这堆白骨周围的一切是不是它的回忆呢。在一堆白骨的回忆中我流浪回来,带了四个朋友,一个高个的,三个矮个的。下午的阳光照着这个破院子,往事中的人回忆着另一桩往事,五个人就这样存在了一个下午。这段存在中我干了件影响深远的事——我掀开狗窝,让四个朋友看多年前刻在墓碑上的他们的名字和生卒日期,四个朋友惊愕了。那个下午的阳光一下从他们脸部的表情中走失。后来他们带着各自的墓碑回去了。
他们说:留个纪念。
我说:有用尽管拿去吧,朋友嘛。
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我没有守好它们,现在都成了别人的。
听到狗吠时我已经快走出墓地,这个村子会不会留我过夜呢,我在心里想,我只是睡一觉就走,既不跟村里的女人睡,也不在他们干干净净的炕上睡,只要一捆草,摊开在哪个墙根,再找半截土块头底下一枕,这么简单的要求他们不会拒绝吧。万一他们不信任我呢,怕我半夜牵走了他们的牛,带走他们的女人,背走他们的粮食。一个陌生人睡在村里,往往会搞得一村人睡不安宁。
我曾在半夜走进一个村庄,月光明朗地照着那片房子和树,就像梦中的白天一样。我先走过一片收割得干干净净的田野,接着看到路旁一垛一垛的草。我想这个村庄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播种和收获都已经结束,我啥也没赶上。即使赶上也插不上手,他们不会把自己都不够干的那点活让给我一份。宁肯倒给几块钱也绝不让我插手他们的事情。
村庄安静得要命,我悄悄地走在村中的土路上。月光下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堆满金灿灿的五谷。院门敞开着。拴在树下的牛也睡着了,打着和人一样的鼾声。这时候,假若走进村里的不是我,而是一个贼,他会套上牛车,把村里所有的收成偷光,村里人也不会觉醒的。人一睡着,村庄就不是他的了,身旁的女人、孩子也不属于自己了。我蹑手蹑脚走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院子里几乎堆满了粮食,只留出一条走人的小道儿。我想找个地方睡一觉,却一点没睡意。这户人家有五六间房子,我推开一扇虚掩的门:是伙房。饭桌上放着半盘剩菜,还有一个被啃过一口的馍馍。我正好饿了,就坐下来吃光了这些食物。但没吃饱。我揭开锅盖,里面是半锅水和几个脏碗。出了伙房我又推另一个门,没有推动,好像从里面顶住了。门旁是一个很大的敞开的窗户,我探头进去,借着月光看见头朝外睡着的一炕人,右边是男人,紧挨着是女人和几个孩子,一个比一个睡得香甜。我真想翻窗户进去,脱掉衣服在这个大炕上睡一觉,随便睡在那个男人身旁,或者躺在那个女人身边,有一块被角儿盖着就满足了。第二天早晨我同他们一块儿醒来,一块儿吃早饭,他们不会惊讶这个在夜里多出来的人,我也不会在意夜间被女人搂错,浑身上下地抚摸。我没这样做,我还是照原路悄悄退出村子,在一堆稻草上躺了会儿,天没亮便远远地离开了。至今我仍不知道那个村庄的名字。在我心中,那个村庄永远在纯纯洁洁的月光下甜睡着,它是我心中的故乡。
一条狗一叫,全村的狗都围了上来,它们或许多少年没见过生人,这下过过嘴瘾。这种场面我见多了,只要装个没看见没听见,尽管走你的路,保管没一条狗敢上来咬你。
随着狗叫,那些面目淡漠的村人一个一个地出现在门口,这种表情我也见多了。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