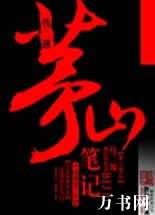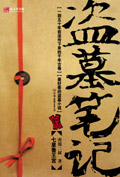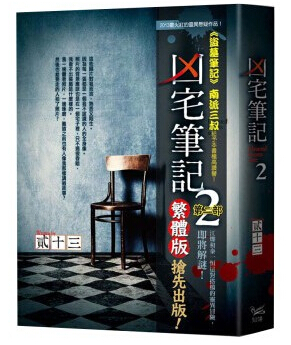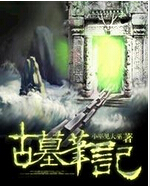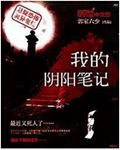山居笔记-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
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
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
,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
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
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
,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
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
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
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
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
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
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
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
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
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
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
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
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
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
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
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
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
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
昨日流莺在何处?
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
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
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
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
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
,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
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
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
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
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
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
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
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
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
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
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
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
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
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
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
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
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
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
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
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
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
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
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
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
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
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
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
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
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
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
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
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
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
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
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
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
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
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
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
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
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
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
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
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
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
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
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
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
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
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
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
,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
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
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
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
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
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
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
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
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