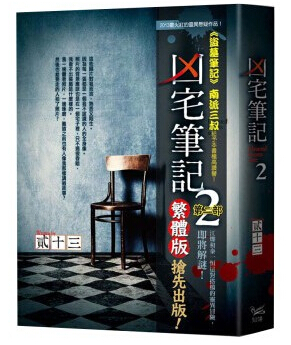山居笔记-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息,于是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
,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
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而对这种可怜,将军全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
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
得一干二净。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
昨天和今天。你看那个曹邺,得了喜讯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变化,然后
想到换衣服,而从旧衣服上又似乎还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时留下的泪痕,他把这些都
写在诗里,心思和笔触都相当细致。有的人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
生,例如韩〔亻屋〕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
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著背雨凄凄,
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
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萧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或许韩〔亻屋〕确实是个例外。对于多
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
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
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
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
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
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
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
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
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
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
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
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
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四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
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
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
格的急剧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
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
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
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
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
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
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
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
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
,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
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
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
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
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
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
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
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
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
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
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
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
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
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详和。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
,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
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偶尔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
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
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
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
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
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
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
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
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
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
、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
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
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
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
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
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
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
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
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
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
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
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
,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
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
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
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
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
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
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
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
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
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
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
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
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
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
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
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
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
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
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
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
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
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
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