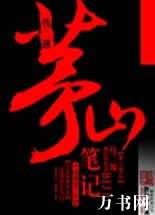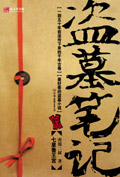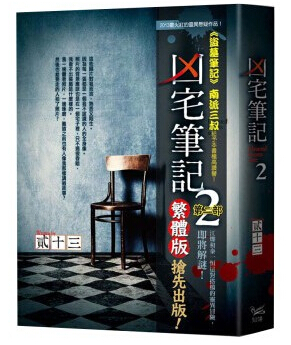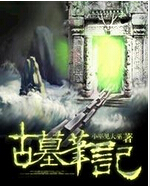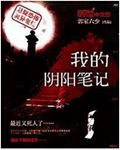山居笔记-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栻见过面,
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
教学的一种内容呢?1167年8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
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
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
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
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
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
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
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
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
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
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
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
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愉快
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
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文化
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
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受了
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
岳麓书院振兴起来,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联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
位青年俊才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
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
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
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
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
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
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
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
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
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
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
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
,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
灾难。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的
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
偏颇,志行邪伪”,“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
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命拆去”的事情(
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学者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
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
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简单描述了他以六十余
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
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
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
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
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
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
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
官兴学。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
,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
要求处死朱熹: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
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
“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
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但是,他还
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例如1197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
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
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
怨无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後
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
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
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
那个通宵。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
道道的学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
二年,1198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
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1199年,他觉
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
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
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
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
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
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
严,有所不避也。”(《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学说又备受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
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
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後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
漂亮。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
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
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
同乡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
点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木式
]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
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
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
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
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
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
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
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
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连正式出版的书上都说他“把历代的革命造反行为诬蔑为‘
人欲’,疯狂地维护反动封建统治”,如果朱熹还活着,没准还会再一次要求把他
“枭首朝市”;至于全国性的毁学狂潮,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谁能说,
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则这些
花朵又永不凋谢?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又
会响彻九州,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潮涨潮落。不知怎么回事,我们
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
之以官场寒喧、市井嘈杂、小人哄闹。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
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栻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一点,作为
教育家的朱熹、张栻预料过吗?而我们,是否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