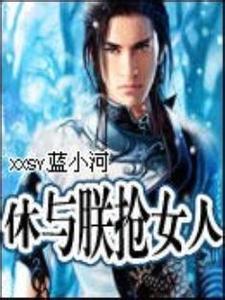洛杉矶的女人们-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厄苏拉不耐烦地等着。谁会对青春期前感兴趣?福斯特不会,大众不会,连她本人也不感兴趣。尼苏拉想跳过所有的预备阶段,达到富有刺激性的部分,封上保密线的那一部分。
“你能回想起几岁开始手淫达到兴奋状态的吗?”
厄苏拉皱起了眉头。这能登在《家庭生活》杂志上吗?
“谁能做这种事?”她装做轻巧地说。
“青春期,3至13岁之间,这是平常事,之后发生也不足为奇。”
这事真有些荒唐,甚至令人讨厌,不过,她立即记起来是什么时候。也许,那不是第一次,但这是她能清清楚楚记起的一次。那夜有一伙人,从起居室传来宏亮的大人说话声,一薄片亮光透过门缝照进她的卧室,她身穿圆点花纹的法兰绒新睡衣,完全醒着。“我在竭力回忆这件事,”她终于说,“我定是7岁或8岁——不,就算8岁吧。”
“你能描述一下使用方法吗?”
这半是忘却、现在由成熟的健壮身躯所高度明了的事,使她感到厌恶。这种幼年的琐事怎么会对任何人有用呢?然而,超越肉体的声音自然有超越肉体的耳朵来听,它们在等待着。
厄苏拉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职业般的音调描述了在8岁时的作为。
青春期的行为提问以这种格调进行了10分钟。厄苏拉难以掩饰自己的急躁情绪。从《家庭生活》的百万读者的观点看,这一切纯属浪费宝贵时间。厄苏拉的回答于是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她吐露12岁上来月经,从而使她宽慰地升级到婚前的动作上。她写了很有限的几页纸,不过现在她相信可以弥补上空白的。
“你怎么定义调情一词?”她听到霍勒斯问。
这可有趣了——它肯定会强烈地引起阅读《家庭生活》杂志的母亲和女儿们的好奇心——于是她考虑了一下。“怎么,我想,凡是能激发人们的情欲而最终没有做任何实质性行为的任何动作,就可以叫做调情。”
“说得对,不过,我想最好更确切一点。”
他对调情由哪些部分组成做了定义。对厄苏拉来说,至少以前她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些行为——并不是她不能确切地回忆——这种明确的科学词藻使得它变得粗欲、不可爱。话虽这么说,她还是记录了这段讨论。必须为福斯特服务。不过,她的打字机会将记录整理更有趣味,用沙纸打磨,用软皮擦。
再上光,直到这个小小的词藻为任何家庭的起居室所接受。
他问起了她有没有通过调情达到满足的情况。
“你指第一次?”
“对。”
“在中学,我是高中生时。我想你想知道我那时多大吧?
17岁。那不意味着我有些拖延吧?”
屏风那边对她的诙谐未置评论。接着问道:“方法是什么?”
又是该死的方法。她简短地作了解释。
“在什么地方做的?”他问。
“在他的汽车里。我们把车停在小山上,在后座上。我原想我爱他,可我后来改变了看法,所以——呐,我们仅仅抚摸了一回。”
屏风两边都作了记录,之后,问答继续进行。最后,他们到达了婚前的暧昧关系上。
“三个性伙伴。”她说。
“这些风流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头两个在他们的公寓里。和最后一个是在汽车游客旅馆里。”
“你最后是否与其中一个结婚了?”
“同第二个有暧味关系后——他成了我的第一个丈夫。”
“同你现在的丈夫有没有婚前性关系?”
“上帝,没有。哈罗德婚前绝不会想到干这种事。发生关系的第一个是位大学生,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后来——我另一个丈夫,写广告稿的这位——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这是我的第一件工作。最后一个是我不得不重新工作之后——我是他的秘书——时间很短。”
“在这所有的暧昧事件中你达到过性欲高潮吗?如果达到的话——”“没有。”她打断了话。
“在这些暧昧事件中,你是穿着部分衣服还是全裸?”
“全裸。”
“这种性行为最经常发生在什么时间,早上、下午、晚上、夜里?”
“哦,我想还是管它叫晚上吧。”
“通常避孕采用人工措施吗?”
“是的。”
“是你的性伙伴,是你,还是你们俩使用避孕用具?或者是你的性伙伴采用诺伊斯的男性节制理论?”
“那些男人总是用避孕用具。”
“好吧,现在回到具体动作上去,关于方法……”厄苏拉的上唇湿润了。上天保佑可怜的工作女郎。后来,她意识到,她的手指将铅笔握得太紧以致失去了血色,而且5分钟一点记录也没有作。她竭尽全力去放松、去回想、去记录。
“……说出那些最经常为你所用的人当中的一个来?”
她用一种陌生的非她自己所有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名字,不知道伯特伦·福斯特会作何感想。
※※※
厄苏拉·帕尔默2点20分出现在罗莫拉的阳光下时,稍有点放松而又担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她性交后常常出现,而写作后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是她无法精确地给下定义的。虽然她不能确切地想象它,但似乎仍有许多要说而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所提问的问题几乎涉及到每个可能的经历,她忠实地对所有的问题作了回答。然而,目下仍有一桩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还比较棘手,因为她不能肯定它涉及的是有关性行为呢还是行为本身。当然好处是,作了记录。临近会见结束,她已经成了行家,将每件事都记在了纸上,何况,她已经把握住了其中的窍门——既要字斟句酌,又要有想象力——文章定会写好的。
她原打算,会见结束以后,立即赶回家中,趁会见情景完全存活在脑海中时写下这次的全部奇遇。不过,此刻,她站在大楼入口前面,突然改变初衷,无心绪马上重温会见情景。这事可以等到晚上或明天去办。眼下她需要到户外走走,到人群中去,不想独守记录作文章。
她想起邮票差不多用完了,于是决定穿过马路到邮局去买一卷邮票。这之后,她明白,自从福斯特来后,她漏做了十几件家务事。她横过马路,正要爬上去邮局的水泥石阶时,突然看见凯思琳·鲍拉德出现在阶梯顶,正向下走。
她停下来。“喂,凯思琳。”
“哎呀,厄苏拉——”
“我刚要穿过马路——发表一篇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演说,题目是:年轻姑娘须知。”
凯思琳不知所措地穿过马路看过去,然后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厄苏拉。接着,她的眼睛睁大了。“你是说,你已经参加过会见了吗?”
“参加了。”厄苏拉平谈地说。
“呵,我亟想听听每件事情。我不是指私人的什么事情,我是想知道如何进行,他们问什么——”“你算碰到合适的当事人啦,你正对一位熟谙查普曼秘密作法的老手说话。”
“他们星期四下午会见我。可怕不?”
厄苏拉不想讨论这事,然而她又不想失去凯思琳。“让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她说,“你有时间吗?”
“戴利达丽在上舞蹈课,不过3点半以前我不用去接她。”
“那好,我会给你帕尔默的删节本看,轻轻跳过青春期性游戏及其琐事,主要集中于性交——不错,亲爱的,这是眼下的流行词,要学会热爱它——性交,婚姻的,婚外的,婚姻性交的某些种类。”
“你是说他们真让你——”凯思琳的急切心情变成了忧虑。
“他们让你什么事也不做,”厄苏拉干脆地说,“我们都是自愿参加人,记得吗?像少校里德的供黄热病进行医学实验的那些人一样。没什么,让我们到水晶宫去吧。照我的处方,按肚里有的东西对付着服下去就行。”
※※※
那些健壮乏味的年轻妇女,卡斯·米勒想。他无精打采地坐在卡片桌旁边,搭着二郎脚,铅笔对着他刚才问的问题上。
“你婚前有过暧昧关系吗?”他的铅笔在空白方框内勾了个“0”。这个“0”对他们四个人来讲代表“不”。当然罗,在下面的十几个提问中并不适用。
卡斯阴郁地疑视着那张长纸单,心里想,这些年轻的妇女全都是一个类型。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毫无二致。在东部,类型是身材小,为人热心,好赛马,很有教养,留着黑色前刘海,挺着大胸脯和长有适于曲棍球运动的大腿。她们去贝宁顿和巴纳德,会与名牌大学的男生们结婚。后来她们午餐时往往喝太多的酒,可总会成为尽善尽美的女主人。人人打网球,穿百慕大短裤,一般外向。在西部,类型是穿着考究,身高而苗条,长着一团男孩子似的头发,与其说是淡黄色还不如说是让太阳晒成的,胸脯平坦,骨嶙嶙的脊背和瘦削的屁股。她们去斯坦福和瑞士,会与热情的职业年轻人结婚,成为婚姻伴侣关系。上高尔夫球课,圣安那风格,过户外生活。
他抓到的是后者中的一位,卡斯扫视了一下写好的记录:玛丽·伊温·麦克马纳斯太太,22岁。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出生在洛杉矶,马钉路德信徒。按时作礼拜,现已婚,第一个丈夫,结婚两年,丈夫是律师,本人家庭主妇。
他继续向下瞅着调查表。青春期以前的异性抚弄,常规。
婚前调情仅限于接吻和短暂的乳房接触。平常,调情总是停止得早。而最后,眼下,婚前性交——从来没有过。乏味,不起情绪,像白开水。
卡斯知道,其余的回答是可以预料的。不过,必须为伟大的白人前辈和STh机服务,他抬眼看了看竹料折叠屏风,对后面的玛丽·伊温·麦克马纳斯太太不感兴趣。他用一种无精打彩的声音重新开始了提问,而她则误认为是为了科学的目的而进行的。“下面,我们有一系列的问及婚姻性交方面的问题——简言之,你的婚姻性史。现在你们的做爱频率是多少?”
“这个……”
“我知道频率是可以变化的,不过,你能划一个每周或每月的平均数吗?”
“我丈夫和我做爱每周平均三次。”玛丽又清晰又自豪地说。
卡斯觉察出这种自豪。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卡斯有点感兴趣起来。他把铅笔在纸上划过。这种阶层的孩子们,也许,这些年轻人大都如此,总是为她们的频率比感到骄傲,为她们的旺盛的精力、为她们那不知疲倦的花样动作感到自豪。倒好像是她们发现了性,把旗帜插在上面,并且专利权所有似的。20年后,将会一周一次,如果是那样,那她就会纳闷,为什么她的丈夫总是工作到深夜,而她就会浓妆淡抹,穿着轻薄,像是抱怨却又是希望她丈夫的年轻新伙伴对她更加注目。
“性交前互相调情吗?”卡斯问。
“哦,是的。”
“你能把做的动作描述一番吗?”
“我……我不知道——我是说,这很难描述。”
尽管如此,在卡斯的鼓励之下,她迟迟疑疑地描述了一下做爱前的预备过程。
她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好歹算脱离开这个大胆的讨论话题,令她欣慰的是不再需要暴露什么了。
然而,玛丽刚刚松了一口气,却又被一连串的新问题所吓倒,这是关于婚爱本身活动的提问。
“我很难准确说出来,”她发觉自己说道,“有那么一二次,”我们计算过时间,只是为了闹着玩。”
“呐,用了多长时间?”
“有一次,3或4分钟,后来是5分钟——约5分钟——另一次,最后一次,我看了时间,几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