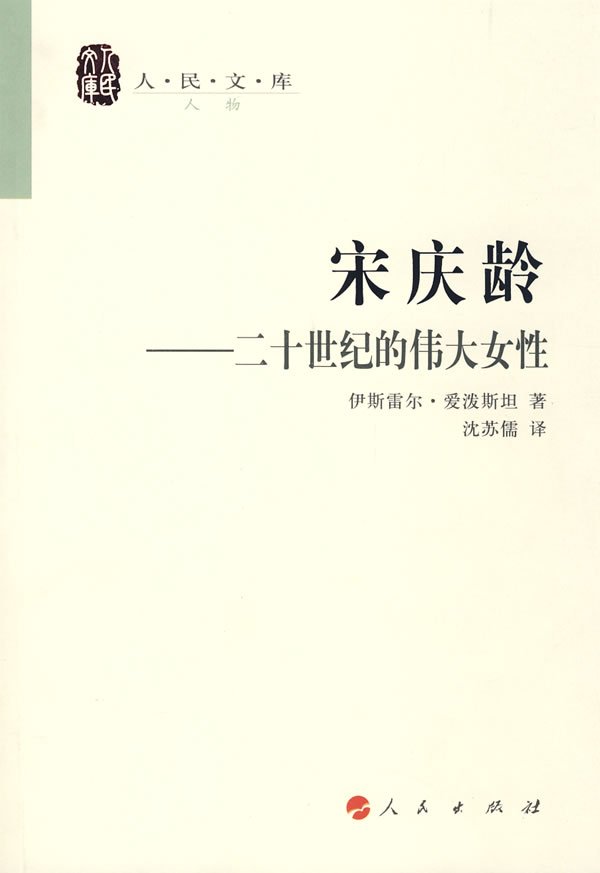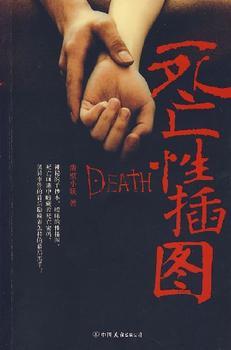永久的女性-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又说。
“我决不叫父亲再为难的。”朱娴说。
“小娴,你这话怎样讲?”
父亲抬起了眼睛望着她。
“他如果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尽管来质问我好了。我和他不过订的是婚约,并不是卖身契,我有我的自由的。”
“小娴,不许说这样的话,这算什么!”父亲的脸沉了下来,但过了一刻,却又和蔼的接着说,“你告诉我,认识姓秦的画家的事,到底为什么从来不告诉家里?你到底怎样认识的?认识的经过怎样?你要知道,这不是说几句孩子赌气的话就可以了事的。”
“我并不向谁赌气,我的行动并没有不能告人的地方。不过,你们哪里会了解我呢?”说着,她就将与秦枫谷认识以来,以及到他家里画像的经过,一一讲了出来。
“人家是很尊重我的,我也知道自重。敬斋如果要编造些谣言来污蔑我,那还是爽快一点,不必再过问我的事为好,他要怎样就怎样,我顾不得许多了。”
“那么,”父亲眼望着朱娴,缓缓的说,“那么,你怎样对得起家里呢?”
“就算我死了好了,我横竖……”这样说着,朱娴突然掩着脸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楼底下的门铃响了起来。
“也许是敬斋来了,我下去看看。娴,好好的,我了解你的。”
说着,父亲站了起来。
七六、自己负责
楼底下来的果然是刘敬斋,脸上显著不愉快的颜色,很匆忙的走进来就向朱彦儒说:
“老伯,你看看这上面的记载,这是我吃饭回去路上无意买到的。”
说着,递了一张报纸给朱彦儒。
朱彦儒接过来一看,是当日的《雏报》,是销行最广的一种新式小型日报,顺着刘敬斋手指的地方,他这样读了下去:
“……其中《永久的女性》一幅,更是青年画师秦枫谷之杰作。画中人是他新认识的女朋友朱小姐,美丽多情,真不愧是一位‘永久的女性’。闻秦君远居江湾,这位小姐为表示钦佩其艺术起见,每天总赶到江湾供其作画,二人感情极好,大有电影‘画室春光’之况云。”
标题是《独展外纪》,下面具名是“内史氏”。
“老伯,你看,我早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人家决不敢这样大胆的乱造谣言。你问过吗?”
说着,他背了手在客厅里来往的走了起来。
朱彦儒真不知道一时怎样回答才好,他眼望着手里的报纸,摇着头说:
“真孩子气得厉害,是完全胡闹!”
“她怎么说?”
“她说是认识的,不过是新近认识的。怕我们不了解她,所以不愿告诉我,也不愿告诉你。不过,敬斋,我想问你一声你们近来可闹过什么意见吗?”
“完全没有。她说了什么?”
“她好像很负气,总说我们不了解她,脾气完全变了。”
“那么,她说怎样认识的呢?谁介绍的?”
“说起来真好笑,”朱彦儒回答,他接着就将朱娴刚才所告诉他的,一一背述了出来。
“天下哪有这样笑话的事!又不是在做小说,她完全是说谎!”
刘敬斋很气愤地说。
“怎见得我是说谎?”朱娴突然从客厅后面转了出来。脸上的泪痕未消,她已经在楼梯上偷听了好久了。
“刘先生,我请你信任我的话,事情是确实的,正如我自己所叙述的一样。我不曾隐瞒什么,也不曾加添什么。我知道你们不会了解的,现在你们既然知道了,我也不用隐瞒,你们要怎样解决便怎样解决好了。”
“小娴,不许这样说!”
“我并没有责备你。”刘敬斋说,“不过,在我这方面,我觉得我有理由可以过问的。”
“我并不拒绝你过问。不过,我却不愿人家恶意的污蔑我!”
“谁污蔑你?”
“这是我个人的事,请你直接问我,不必向父亲交涉。我的行动是公开的,画一张画,决不致这样的严重。”
父亲沉了脸喝道:
“小娴,你上楼去,不许多说!”
“并不是多说,我不过声明我的行动由我自己负责。你们要怎么办,那也是你们的自由。”
说了,她回转身,补了一句:
“刘先生,对不起了。”径自上楼去了。
七七、三过其门
刘敬需和朱娴的争执正在紧张的时候,这时,在她们所住的房子的外面,在清源坊的弄口,有一个身材很修伟的青年男子,好像寻不到自己所要寻找的门牌号数一样,已经第三次从这里走过了。
这个人是秦枫谷,他一连往返走了三次,还没有勇气敢跨进清源坊的弄口。
展览会的第三天又过了,依旧不见朱娴的踪迹,他期待的结果,朱娴并没有来,罗雪茵却在今天下午像候鸟一样的如期飞来了。她要求秦枫谷履行他的条件,陪她看电影去,秦枫谷推说因了展览会的会务,白天没有空,晚上太疲倦,又有许多零碎的事务,要求延期到闭会后再说。
“好的,我放宽你的期限,看你下次再有什么推托!”
恰巧有一家摄影新闻社来给秦枫谷拍照。秦枫谷便拖了张晞天等立在《永久的女性》下面拍了一张照。罗雪茵当然在内,而且紧贴了秦枫谷站着。这又使她很高兴,她觉得今天虽然不曾看电影,但拍了这一张照,和他一起,而且恰巧站在那张画下,总算不虚此行了。
凄凉的是秦枫谷的心里,事情真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他早就有这奢望,等朱娴来了他要请她同自己立在《永久的女性》下面,两人合拍一张照,以纪念这一张画。不简直是纪念他们两人的巧遇、两人的姻缘!
但想不到事情的变化竟这样不能捉摸,说是第一天就来的,如今已经到了第三天,人也不来,也没有信来,究竟为什么呢?
对着展览会的入口,秦枫谷已经用一种绝望的眼光守候着。他知道一定有绝大的变故阻止她来了。他的守候,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我不能再遵守我的诺言,我只得冒险了!
吃了晚饭,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难耐的苦闷,一定要揭开这个哑谜。他偷偷独自走了出来,按着朱娴所抄给他的住址,开始了探险的行动。
深秋的晚上,亚尔培路的下段,越过了回力球场,显得异常的冷落,只有偶然一辆汽车,闪着红色的尾灯从他眼前滑了过去。被夜风摇荡着的路灯,冷冷的在街心撒下了一圈大的影子。
远远的望见了清源坊,他的心不由的跳了起来。像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一样,他回头向后面望了一眼,然后就屏息从街对面很快的走了过去。他不敢多看,只用眼角扫了一下,好像有人在注意他的举动一样,匆匆的低了头走过去了。
走过了十几家人家,他又鼓起勇气,装做寻错了门牌一样,穿过街心,沿着清源坊的一面走了回来,但是走到清源的弄口,他心跳着向里面仔细望了一眼,里面冷静的没有一个人,他又脚也不停的走过去了。
“该死的,这样的没有勇气!这次一定进去!”
第三次又走回来的时候,他这样坚决的对自己说。
七八、心的巡礼
不用说,秦枫谷虽然下了最大的决心,但是第三次经过清源坊的门口,仍鼓不起走进去的勇气。他不敢再走回来,只得沿了亚尔培路一直走了下去。
他从亚尔培路折人辣斐德路,从辣斐德路转入迈尔西爱路,又走上霞飞路来。在清冷的路上,他只是嘲笑自己的无能。并没有人留意他,而且也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会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会几次不敢走进去呢?
其实,走进去又怎样?敲门吗?从门缝里偷望一下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个愿望:至少也要望一望她所住的房屋,望一望窗里的灯光,用以安慰自己,知道她是住在这里面。至于敲门进去。他自己不敢想,他自己不能断定他自己有没有这勇气。
但是,不亲眼望一望她所住的房屋,他是不甘心的,而且也不肯放过自己的。从霞飞路又折人亚尔培路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得走进去一下了。
过了回力球场,亚尔培路更显得特别的清冷。停在弄口的一个黄包车夫,好像并不曾认出他是往返从这里经过了几次的人,每次总向他兜揽生意。他因了这一点暗示,知道是自己心虚,别人决不会留意他的行动,而且根本也没有人在注意他,于是经过清源坊弄口的时候,他牙齿一咬,下了最后的决心,用着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自己走进去了。
清源坊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幢小洋房,他低头走几步,才敢抬起头来望望两旁的房屋。右面人家门牌号数已经是二十六号,他知道朱娴的家是在前一条弄里,便索性将错就错,一直走到弄底,才像找错了门牌一样,又匆匆的走了回来。
短短的围墙里,每家人家都从窗帘的缝隙里漏出灯光,显出一种和平安静的空气。他从弄口的市道转入第一弄。第一弄的头一家是一号,他知道再走过十八家就是朱娴的家了,心里不由地跳了起来。他低头走了过去,走到二十一号才敢回过身来,向十九号望了一眼。
十九号的楼上是黑的,只有楼下客厅里有灯光。明亮的灯光,从垂下的窗帘缝隙里,水一样的漏了出来。
——也许正在吃晚饭吧?她的家庭情形怎样?父母在吗?还是住在亲戚家里?她住在哪里?楼上没有灯光,难道不在这里吗?
这许多凌乱的问题,立时涌到他的心上。他脚也不敢停步,好像每家人家有人在窥探他的行动,又匆匆的走了出来。
虽然只是望了一眼,但他心里轻松了许多。像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巡礼者一样,已经辛苦的达到了圣地,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旁的奢望已不敢再想了。
——是的,她就住在这里,就在这有着灯光的客厅里。与我是如何的接近又如何的远隔哟!怀着这样感伤的情绪,走出清源坊弄口的时候,他听见后面有急促的皮鞋脚步声,便头也不敢回的更快的走了出来。
走到马路的对面,他回头一望,走出来的人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接着拍的一声,这个人打开停在弄口的一辆跑车的车门坐上去了。
七九、解约罢
刘敬斋今晚所办的交涉,虽然不曾全部解决,但是离开他的丈人家里的时候,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段落。
未婚妻今晚向他所表示的态度,是他从来不曾见过的。他完全猜测不透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变化,但他是深于世故的人,第一,他看出来朱娴并没有真正的不名誉行动;第二,他知道朱娴目前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她是不会真正的反抗父亲的,因此他索性认清了目标,要他的丈人负全责,单独去说服他的女儿。自己不愿多开口,以免引起双方感情上的冲突。
他向来对于朱娴是满意的,虽然知道和她父亲的一点经济关系,未免使女儿心里总有点不舒服,但他却以为人为未尝不可以回天,而且这一点缚束未必不是一种保障。
他知道现在是最适宜发挥这种保障的权威时候了,所以经过了一时感情冲动上的怒气之后,便平心静气的辨别了事情的真相:将责任完全放在他丈人的身上。
朱彦儒的心里当然是明白的,而且更知道女儿的婚事如果决裂了,会影响到怎样的局面上去,所以对于他女婿含有威胁意味的暗示的话,完全无条件的承受了。
“我不想再向她质问了,以免引起大家感情上的冲突。我想只要老伯和伯母细细的向她劝导一番,她当然会明白自己的错误的,我只


![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离了[娱乐圈]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12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