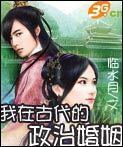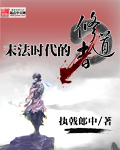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地位,这些为她提供了一个另类性经济(sexual economy)的迷人景象,后来她还把这种景象传递到伦敦宫廷。蒙塔古夫人信中的描述一直是后来的土耳其浴及后宫描写的基础,直到19 世纪末期摄影家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从而提供了关于非西方女子更加另类、更富异国情调的描绘。伊沛霞的著作也是这样对待中国妇女的吗——它是否通过向我们提供为自由、参与、变化而斗争的女英杰而使我们加倍着迷?是否因为她们穿戴着东方服饰而使这本书显得更有趣?
我的意见是,伊沛霞的著作(多半像其他妇女史著述)通过建立一个不能轻易——不是不可能,但也不直接——进入宋代妇女世界的入口,消解了历史写作中一些最危险的幻想因素。比方说,一个学者不会在希特勒的铁靴政策和征服的残酷世界中欢呼,却必定会苦苦思索关于婚姻的复杂的父系制(patrilineal)、父家长制(patriarchal)、从父居住(patrilocal)的系统和这个系统对联姻的严格规定。这两种态度的差别不是一个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的问题。作者个人的途径是掌握中文,读了跨度长达3个世纪的难读的文件(一小部分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笔),越过了无数关于想像的障碍。到了最后,没有不现实的、夸大的女英杰,却有更加针对个人的描写,包括分内责任(如纺麻线或指挥仆人),既有不可想像的又有常见的艰难,既有小小的享乐又有极度的奢侈。我们可以满意地谈论她们的全部重要性,尽管可能不像那些男性征服者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那么起劲。越过社会性别和文化差异——不仅是时间上的差异——的曲线、艰难地达到的历史的理解使历史英雄主义幻想的色彩暗淡了,一如伊沛霞表达她不让“我的想像跑得太远”的关注时所暗示的。结果,这出戏的历史舞台背景不同,演员更多,没有主角,观众听到的声音并不那么独特,台词断断续续,需要更多的注意才能捕捉住它的信息。
但在这里我们再次接近了幻想的境地。在这里,支配许多妇女史学家(包括研究者和作者)的信念是她们的业绩“改变”了历史自身的性质,那就是,妇女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英雄主义类型,因为它重建了一个不同的过去,并且通过使历史专业的分析实践少一些性别主义和偏见,发挥了一种更加另类的作用。我愿再次指出这种低调,作为历史学家的伊沛霞以这种低调说出了她的大多数断言。她坚持不懈地把自己获得的洞察力转换为质疑中国主流史学的问题。能够想像我们的知识将会重塑世界,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方法论上的幻想是作为问题提出的,从而给其他的解释和叙事留出行动的空间。《内闱》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和其他学者的洞见敞开自己,不妄做最终结论。
这本书不提供令人满意(或震惊)的那种读者会轻易认同的叙事,也不展示宋代妇女生活的异国情调的差异。相反,它提供给我们有时难以把握、有时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来说更为常见的材料。通过提出关于妇女生活、社会性别、我们为什么阅读历史和怎样撰写历史等问题,伊沛霞使《内闱》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进入的领域。
第一部分:目录自序
博妮·史密斯
(Bonnie Smith)自序
我研究宋代(960—1279)的家庭、家族和婚姻已有十几年。撰写一本以妇女为中心的书的计划久已有之,但屡屡发觉有必要事先研究相关题材,如财产法、家庭礼仪和儒家思想。我也在拖延,希望克服一种感觉——关于这个课题永远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我不想掩饰不愉快的事实如买卖妇女、缠足或扼杀女婴;我也不想用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描绘中国的社会性别差异,同时在判断中隐藏着当代西方标准。作为历史学家我发现一般性地描写“妇女在传统中国的位置”失之于简单化,那样做实质上已经暗示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以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把妇女首先表现为受害者,这种做法经常困扰着我,因为它似乎贬低了她们。难道不是大多数中国妇女都有自己控制的空间吗?而且不是有些女人——至少有传说中的暴虐的婆婆——对别人进行相当可观的控制?我知道许多当时男性作者书写的史料建筑在我们今天不一定认同的道德前提之上。我能不能找到一些途径同情地看待各种女性——不止是尽职的儿媳和自我牺牲的母亲,还有被嫉恨征服的妻子,不再信任任何人、整日争宠的妾,以及遗弃孩子而再嫁的寡妇?
尽管怀有疑问,我还是逐渐开始收集本书使用的零散、片断的史料。我最初的目标是写一本关于婚姻的学术专论,而且我写了几篇有深度的考察婚姻特殊侧面的文章。1990年,我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写作本书,我决定放弃专论,准备广泛考察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既有挑战性又令人兴奋。正常情况下,当我写给史学同行看时,我可以把精力限定在史料完备的儒家思想和财产法这类问题上,但是现在为了全方位的理解,我必须介入难以捉摸的性倾向、嫉妒和社会性别象征主义等领域。
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使我对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课题产生了新的洞察力;然而,有一个代价就是要使每个专题的论述都不长。用50页而不是5页或10页来处理如离婚、寡妇再嫁或亲戚之间联姻这类专题,当然就有余地做更细致的分析。但是本书很快就写到难以控制篇幅的部头,因而未能为初衷服务。因此我不得不寄希望于我对重大问题的简约将激励精力充沛的学者们展开更全面的考察。
由于致力于将更大的整体历史纳入研究焦点,我发现纠缠不休的不知从何入手的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由于强调语境和妇女的参与,我感觉我能给予妇女应有的描述,同时又不背叛我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既包括权力的结构,也包括帮她们给自己定位于这些权力结构之内的观念和符号。它嵌在历史之内,其特征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塑造并反过来影响那些进程。家族和社会性别体系毕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强调妇女的能动性意味着把女人看作行动者。正如男人一样,女人占有权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对现存史料的解读可以把以下内容摆在显著位置: 妇女回应那些向她们开放的机会,并且或顺应、或抵制那些围绕着她们的机会。
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不可避免地受惠于那些使他们有时间和资金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人们。本书包含的研究始于1983—1984年,是年我在普林斯顿度过,得到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支持。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部多次提供资助聘请研究助理。谢宝华(Bauhwa Sheieh)小姐在写作初期、来秋月(Chiuyueh Lai)小姐在后期给予帮助。伊利诺伊——淡江大学交换项目奖金使1990年夏天在台湾的研究成为可能,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提供了制作图片的费用。伊利诺伊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奖金使我有时间在1990—1991年专心写作。那一年我在京都大学人文学部逗留6个月,那儿是搜集资料、反思更大课题的好地方。
内闱自序我的谢意不仅给予这些研究所,还献给慷慨地付出时间和参考意见的同事们。孟久丽(Julia Murray)在图片、弗兰西丝卡·布雷(Francesca Bray)和盛余韵(Angela Sheng)在妇女的纺织活动方面给我建议。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周起荣(Kaiwing Chou)、托玛斯· 黑文(Thomas Havens)、桑亚·迈可(Sonya Michel)和罗纳德· 托比(Ronald Toby)——在短时间内阅读了校对稿。我特别感谢所有阅读过全部初稿的朋友: 贾志扬(John Chaffee)、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皮特·格雷戈里(Peter Gregory)、金滋炫(JaHyun Haboush)、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马伯良(Brian McKnight)、恩·瓦特纳(Ann Waltner)和罗宾·瓦特森(Rubie Watson)。他们指出哪儿该多交代些背景,哪儿自相矛盾,哪儿应更有力地展开自己的观点,这些使我的陈述更清晰。我也感谢用发言和论文回应本书覆盖的问题的人们,他们是斯坦福、戴维斯、拉特格斯、哈佛和华盛顿大学研讨班的参加者,京都大学古代中国研究组、东京中国妇女史研究组、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史小组的成员。论文来自“家族人口统计讨论会”(阿西洛玛Asilomar;1987)、“中国社会的婚姻和不平等讨论会”(阿西洛玛 Asilomar;1987)、“早期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史讨论会”(台北,1990)、“中华帝国晚期家庭和政治进程讨论会”(台北,1992)。最后,我愿感谢我的中国妇女史研讨班的学生,他们对这个课题付出了热情,并且愿意从几乎任何角度讨论各种问题。
第一部分:目录习用语的说明
1 如果可能,本书用姓名而不用某男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表示一位女人。如司马光的妻子为“Miss。Chang(1023—1082)”。“张”是她出生的家庭的姓,她终生可以使用。如史料载有全名,如“沈德柔”,则照录。多数事例里没有女人的全名只有姓。一般说来,当时用娘家的姓再加一个礼貌的字——氏——称呼已婚妇女。本书把某“氏”译为“Miss。 ”,表示出嫁前娘家而不是夫家的姓。称某女子为某氏不表明婚姻状况。尽管“氏”也加在男人的姓以后,但是男人还是常用家庭的姓和本人的名组成的全名。本书只有很少的例子,用丈夫的姓称呼妻子如“Mrs。 〃。男人姓名以前不加“Mr。”,如只写“司马光”。女人姓名前写“Miss。”或“Mrs。”, 这样做违背当代美国避免使用性别字眼的规矩,但用在这里可以减少弊端,可以突出中文原有的精确性,对男人直呼其名比较简单,读者一看就知此人性别。
2 导言里讨论的6位男女作者(洪迈、司马光、袁采、程颐、朱熹和李清照)以外的其他男女均注生卒年,即便与所叙之事无关,也注明。这样做为了强调他们比较特别,不是一般的类型,可以与很多女人如张小姐或吴小姐区别开。提供生卒年还促使读者考虑变化问题,比如逐渐增长中的理学的影响。
3 年龄用“岁”表示,一般地说比西方人大1岁,因为出生后即1岁,过了第一个新年后即2岁。因此,18岁结婚的姑娘实际年龄在16—17岁最后一天。比如,1000年12月31日出生、1017年1月1日结婚和1000年1月1日出生、1017年12月31日结婚的,都是18岁。
4 为了方便,用当代的“省”名而不用宋代的。附有地图表明宋代和今天的不同的北部边界。
5 引用的中文由我本人译为英语,英译文后面注明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到整个段落。
6 本书正文只用了一个缩略语 c。s。 ,表示的日期是没有生卒年的男人中举的那一年。
内闱习用语的说明宋朝疆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