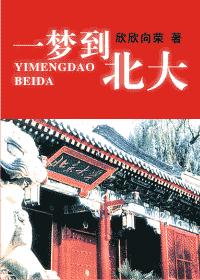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万两银子的存折呀,还有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生的伙食费,众名流的电话和住址,历任校长的风流逸事。诸如此类琐碎的传闻,全成了他们与北大人交往的资本和生意手段。也为许多爱写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和野史作家提供了风流潇洒的故事佐料。每当夜幕降临,许多名流都爱来这儿喝几盅,趁兴海阔天空地闲扯一通。学士居就是其中最受师生青睐的一家小饭铺,范文澜知道他要找的人准在那里。
士居的掌柜姓张,河北人,在沙滩一带也算老字号这家饭铺不大,却有几手绝活儿。一是掌柜的陪喝,都说北大怪人多,张掌柜的眼神也腻怪得很。一眼瞅准了谁,就把康熙酒壶往你面前一放,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桌的酒钱就上了他的账。当年的张亨嘉、严复,以后的林琴南、辜鸿铭,都是他向人炫耀的话题。据说林琴南就是从这儿听说了管学大臣许景澄慷慨就义的故事,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剑腥录》。
二是堂倌的鸣堂绝。你别小看这跑堂儿的,俗话说“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你瞧,一个好堂倌顶得上饭馆的半个买卖啦。这个行当要的是心快、眼快、手脚快,嘴得会说话,能言善哄,不让吃主空着肚子走,非得把兜儿里的钱掏出来不算完。这里的堂倌会来事,懂得礼节也多,尤其是那鸣堂叫菜和口念唱账的功夫,在沙滩一带独领风骚。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大呢,一见食客上门,先要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接引,叫引客呜堂。客人入坐,送上茶水、手巾把儿,如有小孩还得送上玩具。一只手在本来很干净的桌面上殷勤地擦拭,一面以鸣代步地把客人订下的菜单一一唱付给后灶的红案厨师,这叫介绍鸣堂。厨师将菜烧好,又用吆喝鸣堂唤堂倌前来端菜。在鸣唱中要说清上菜的顺序,摆放的要求。如鱼头冲主客,鸡头不呈女宾等等。还得说明是“单上”,还是“双上”和“分上”。如是香酥鸡,将蘸料放在主菜旁为单上。要是拔丝山药,同时上一碗涮筷清水为分上。碰上了浇汁锅巴,将炸好的锅巴与浇汁分上到桌面再合在一起为双上。最为精彩的还是结算鸣堂。算账时,只见那店小二当着客人的面,不用算盘不用笔,先悠悠地唱菜名、菜碟尺寸,再唱酒水、主食和汤,都逐一报出价钱。还要把顾客的钱和找头也一并唱出,这叫心明眼亮,让顾客、厨师和钱柜都觉得无暗送人情之嫌。学士居凭借这些天下一等的堂倌,还愁没生意?
此刻,一位年轻的堂倌见来的是两位常客,也不用范文澜开口,就顾自鸣唱起来。
“二位爷里边请,来拌凉皮一道七寸,拉薄剁窄双份芥菜,神面两碗,多搭两扣走细条”
这是穷学生的吃法,多是来碗面添一道下酒菜。范文澜一进门,就见戴着黑边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端坐在酒桌上,一旁陪着的正是张掌柜。
他心中一阵窃喜。这位钱玄同,虽是浙江吴兴人,也可算半个绍兴老乡。尤其与蔡元培,有非同一般的世谊之交。那还是前清的旧事,绍兴乃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刘宗周和弟子黄宗羲、祁彪佳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钱玄同的父亲钱骞仙,就在此执掌过著名的龙山书院。这是一位博学方正的学者,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朴学大师俞曲园,还有绍兴名流徐树兰都是至交。蔡元培是十二岁拜王子庄为师的。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也是钱山长的朋友。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源流,专攻制艺闻名遐迩。蔡元培以后就是凭借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据传他二十一岁中举时,房官为缙云县人宦汝梅,阅卷后一口断定必是老儒久困考场者所为。最可笑的还是坊间刻印的怪人股特刊,名《通雅集》的,还将他的文章作为压卷之作供应试者仿效。蔡元培在求学期间,就多次拿文章请教过钱骞仙。钱对其怪僻生涩的文风竟大为欣赏。
这还是远的,再说近的。熟悉蔡元培的人都知道,真正帮他学养大进的还是徐树兰。绍兴徐氏乃山阴望族,徐树兰又是光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


![[希腊神话]大地之父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8/885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