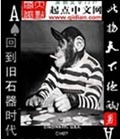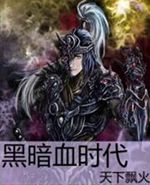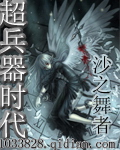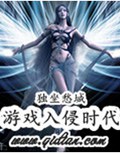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了,周人把他们带来之后,一同带来了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则被遗留在原王畿地区,也就是中原朝歌一带,被称为“殷人”,受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也作为一个封国。但是周武王派了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夹辅着武庚,号称“三监”,就是坐地盯梢的意思。
然后,周武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而把中原留给三监管理。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要反周复商!!!!”
出师一捷身就死,武王大哥在灭商后第二年就于镐京驾崩了,没享福,先升天找父亲文王言好事去了。接任的周成王是个小孩,请叔叔周公辅政。
辅政的周公并不姓周,他姓周王族的姬姓,周公整个的名字应该是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
(注:据书上说,鸡在古代还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因为避刘邦的媳妇也就是毒婆子吕太后吕雉的讳,雉才改叫了鸡,但鸡为什么现代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其实,“姬”是家族的姓,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也就不用担心念成“鸡蛋”了。当时一般把官职和人名连称,他应该叫“周公旦”,“旦”是他的人名,“周公”是他的官位。)
周公旦辅政,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处置政策,签署禁酒条例,讨伐周边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还得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进去接着洗,反复三次,洗一次澡中间得料理三拨客人。
(注:周朝人蓄长发,把长发拧成一股之后,再像弹簧似的盘成大髻,髻中间插笈做扎束。甲骨文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髻上插笈——簪子,而“妻”字表示女孩儿结婚以后也开始结髻,并且上面插了好多簪子——横杠,以示爱美之心。商朝贵族妇女有一位出土的,脑袋上插着26枚玉制的簪子,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
至于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 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从浴室跑进跑出,也感冒着凉,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说他是圣人,一点不错,“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名字还排在孔老二之前呢。孔子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称“梦见周公”,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大约梦中还真得了他不少真传。(柯云路大师硬胡说孔子这是开天目。)
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他文笔也很行,他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行说的规矩,其中无处不体现了对等级的维护——核心意思就是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天子是老大谁都得在礼仪中维护,同时还规定了男尊女卑的礼。《周礼》反映的就是秩序和尊君,一并连带着是尊父和尊夫,后者是沾了尊君的光。《世说新语》上晋朝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婆制定的就好了,礼节就能反过来变成对女人有利了。
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周武王的弟弟管叔就心怀嫉恨,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周天子的权位,并且策反另外两个地方大员,发兵诛杀周公。我们知道,管叔、蔡叔、武庚,是留在中原的“三监”。管叔策反了其他“两监”加盟,其中武庚作为商朝遗民首脑,整天正想着反周复商呢,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叫上自己所统领的商朝遗民,又去和一些东夷族特派员洽谈,获得许多东夷族武装支持,与管叔、蔡叔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中原及其以东地区形势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向中原讨乱。在战斗中,造反的几伙势力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被姜子牙隔挡开了东夷人——姜子牙顶着,东夷人往中原冲,姜子牙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给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三监的暴乱分子:把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四年后周成王长大成人20岁时,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
后来的臣子奏章或者科举专家写的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人物,他给后来的人臣特别是辅政大臣们立下了规矩。辅政大臣的定位到底可以怎样,大家援引周公事迹作标准,越古越有理啊,如同外国法律上援引老辈子案例作准绳。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们好意的变改说法,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于宝位,面向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 为其如此,管叔(三监的老大)自认为是行三(周武王行二,而周公行四),在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他发动暴乱,又联合了时刻想着“反周复商”的武庚。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先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就配合三监武庚一起反周。在三监武庚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几十个国家卷入其中,但战斗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时称奄国)全部骟掉,作为严厉的报复和惩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管太监又叫“阉人”、“奄人”。
奄国,是曲阜地区的一个东夷强国,抵抗周公格外剧烈,长达三年,最终在失败后得到了这样的严厉报复。这就是很多史书上提到的“周公践奄”的事。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就是残灭踏平了奄国。
包含奄国在内,被灭的东夷诸国达到五十个之多。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亡国之后的男人,有的人额上被烙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以此作为奴隶的标志),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战争是个疯狂的事情,它一旦启动之后往往偏离人的道德规范。
而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人员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都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飞廉而且是F4中伯益的后代,后来他与伯益一并成为秦人的祖先。
《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公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当时从征的,不光有周人,也有周人挟持下的诸侯联军。去时风花雪月,回来雨雪凋零。这场东征战斗,不论对于敌人和征伐者来讲,都是一种哀情。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经济上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再多不是他不想养,而是养不起了。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对付分散盘踞在周控地区以外的上千个诸侯,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费尽心思,创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绝技,那就是“周礼”!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等级尊卑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让诸侯们服气他。
周公把自己制定的“周礼”,下发给全体臣民去练习。
按照《周礼》要求,不同等级的人,见到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有十数种不同的磕头方式。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的话先迈右脚,从西阶上的话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在堂上或是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套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宫院大门时,孔子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经过的时候,不敢经过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