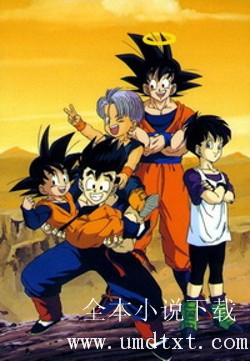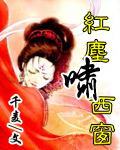西窗烛话-第1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多识广,一会儿工夫,就会把酒菜全端到桌上来。
我们一直在怀化的街上晃荡,直到街上的路灯都亮了,我们才回旅馆,走到三楼服务台请女服务员帮我们开门,迎面走来的两个女子叫人目瞪口呆。当时虽然是夏天,她们就只穿一件女式背心,一条鲜红的女式平脚内裤,趿拉着拖鞋与服务员打招呼。两个女子都很年轻,最多不超过二十岁,胸部丰满,屁股老大,涂脂抹粉,走过一路香水味,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也知道旅馆是默认她们的存在的。
怀化火车站前面的夜晚还是很热闹的。几个赶晚班火车的山民用竹竿挑着笨重的行李不知从哪里而来,一堆西瓜像是被遗忘了似的,没人买,卖瓜的人都跑去打牌了,沿路边摆了一溜儿的小折叠桌,那是为宵夜的人们准备的,我最喜欢那些满脸横肉,赤膊上阵的食客,一瓶啤酒,两碟卤菜,好不潇洒。
那天晚上,我们的房门被敲过两次,我决定不开。
六六大顺 38.蹊跷之行
如今我把当年如何去的邵阳的过程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极其罕见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我对着湖南地图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好久,直到我开始动笔写这篇邵阳之行的时候,依然一无所获,只得把这篇命名为《蹊跷之行》。
我可能是乘火车去的,在怀化乘上开往株洲方向的火车,途中心血来潮,在娄底转向邵阳的;或者就是干脆从怀化直接到的邵阳,但我对邵阳火车站却没有一丁点印象;下意识地感到我还是乘汽车去的,那我是从哪里出发的呢,从线路上看,有可能从常德经涟源去的邵阳,也有可能是从益阳出发。但都不能确定。
我只记得,我们到达邵阳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了。那是个不冷不热的好季节,太阳已经有些倾斜,城市的大街上到处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我知道这是湖南中部最大的一座城市,建筑物和街道也就自由发挥了,沿街的门面都开着,卖什么的都有,不远处就望得见一条河流,岸畔也是林木葱郁。
我们就在汽车站附近胡乱找了家旅馆,一楼的两人间,窗外是一个家属院,白天有孩子的嬉闹,晚上则是音乐爱好者的乐园,不过还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那些蹩脚的胡琴声早就偃旗息鼓了。我们还是到附近的人民广场转了转,广场不大,暮色中有不少人在散步,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孩子在骑着童车。
正是晚餐时分,每一家餐馆里都人满为患,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却是与一对情侣相对而坐,挺尴尬的。我们点了一荤两素,还要了点酒,湖南菜太辣,只得再要一碗汤。情侣先是很警惕的望着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很拘束,后来从语言上听出我们是外乡人,而且听不懂湖南话以后,就又恢复了窃窃私语,情话绵绵,反正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只知道男青年似乎在请求什么,女孩子笑而不答,最后两人迅速离去,不知是谈崩了,两人分道扬镳,还是女孩子答应了,共赴爱河?
第二天早上的一切又奇怪的异常清晰,起床,洗脸,收拾行李,退房,在街边的小店一人一碗米粉,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要离开,对邵阳的熟悉就局限在人民广场。邵阳汽车站是在一个大院里,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从对面街上横穿马路走向车站入口,正好有一辆班车驶出,一个男售票员站在敞开的车门前探出身来喊道:“长沙,长沙。”不少人都涌向车门,售票员又在喊:“直达长沙,长沙的才能上。”于是大多数人退出了,我们跟着缓缓滑行的班车跑了几步,就上了车。
客车经过了邵阳化纤厂和邵阳粮油机械厂就进入了邵东县,公路与铁路线相互缠绕着,忽左忽右,大概这里属于丘陵地带,山不大,坡不高,班车不费多大的气力就可以翻过去,两边的田地大多是水田,一些刷在农户墙壁上的石灰标语在号召大家加快黄花之乡的建设,字迹潦草,有些看不清。
过了界碑就是双峰县。直到过了双峰县城关永丰镇后,售票员才开始卖票,见人就问:“哪里?”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的回话,掏钱买票。钱是交了,票却不给,有人抗议就给上一张。车上人不多,断断续续也就上了二十来人,售票员走到我面前停下:“你。”我在回答:“长沙,多少钱?”我的陪伴已经掏出了钱包,售票员却径直走了过去,丢下一句话:“到长沙再说。”
班车从铃山进入了湘乡县,然后走湘潭到长沙。那是另一篇所涉及的了。只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太过于匪夷所思了,令人不敢相信,所以接着写一点。从湘潭开始就有人下车,慢慢的,当班车开到离长沙火车站一步之遥的白沙饭店时,车上就只剩我们两个乘客了,司机停下车,售票员在叫着我们:“喂,你们还不下车?”我们连声答应着,背起行李急忙跳下车,那车就轰轰隆隆的开走了。我们没买票,居然从180公里之外的邵阳来到长沙,为什么?我们没敢问,他们也没说。
去邵阳忘得一干二净,到长沙却有如昨天。
六六大顺 39.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39.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湖南人因为“两个主席的故乡”而自豪,而主席也曾自称自己是湘潭人,而曾经主持修建伟大的韶山灌区的华国锋也由此引起了主席的注意,称其为自己的父母官,并由此青云直上,从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副主席,最后在死前索性将自己所有的头衔(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并交给了他。自己乘鹤而去。只可惜人高马大的华国锋却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还沉浸在打倒“四人帮”的喜悦中,号称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敬爱的华主席”就被叶剑英,汪东兴打翻在地,赶下了历史的舞台,这也许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经典再现。
不过到了湖南,岂有不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的道理,那对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就是一次朝圣。长沙火车站有一班到韶山的专列,走株洲,过湘潭,从湘黔铁路修了一段21公里的支线到韶山。满满一车人,大多是旅游者,还有穿绿军装,带毛主席像章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红袖章。
那是很狂热的气氛,我所在的车厢有人领唱《忠字歌》,我真惊讶自己也还记得歌词,还能唱出声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贴心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跳下火车,走上韶山的土地,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这片养育了一代伟人的土地上可能是中国还能看到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的地方了,站在毛主席塑像前,不得不承认主席那崇高的人格威力和平易近人的慈祥面孔给人的感召力之大。看着那些色彩黯淡的画像和字迹模糊不清的语录牌,就会体会出农民的崇拜和保护。
我喜欢毛主席的诗篇,那是一种豪迈的艺术享受,但我不太喜欢在韶山遍地都是的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那未免太过于直白,也有些大跃进的味道,我还是喜欢同是《七律到韶山》里的另一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多美的画卷,多好的意境。
事实上,韶山与湖南其它地方的景致差不多,只是公路更平整,水田里的禾苗更茁壮,田间地头显得更热闹,房屋建筑更讲究,山上的树木更郁郁葱葱罢了。从南岸绕过那口著名的水塘,就走进了毛主席故居,这个家庭无疑是这一带最富裕的农户,规模颇大,房间颇多,要不然也无法容纳那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观光客。我看了看主席当年回家很感兴趣的那张照片,他们两兄弟俩站在到长沙看病的母亲身后,那时的主席年轻,充满朝气,玉树临风,傲慢而雄心勃勃。
爬到韶峰看过了主席父母的坟墓,就和大家一道道主席故居的对面的毛家饭店吃午饭,老板娘口口声声说她当年见过主席,而且指着照片上的一个未擦掉鼻涕的女孩子自豪的说:“这就是我。”主席真的在她家门前坐过,和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坐在一条没刷油漆的木条椅上,抽着香烟,说着家常话。
我们看过了毛主席纪念馆,毛氏祠堂里的农民夜校的旧址,从一道小桥上走过去,那里是韶山宾馆,很宁静的,只要掏钱,就可以入住,只是不知主席1957年第一次回韶山时是否在此住过,绿草铺地,砖砌的甬道显得很精致,树木很大,屋檐下的水沟里长满了青苔,连成串的蚂蚁不知在忙碌着什么。
和一帮不相识的游客挤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去滴水洞。私人的车,擅自跑客运,马动机似乎有问题,时快时慢,司机也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吹着口哨,满不在乎,顺着公路行不多时,就拐到一条岔路上。开始爬山,山道弯弯,越走越偏僻,越走越显得安静。拐弯处很急,司机拐弯的速度令人提心吊胆,乘客们也随着前仰后合。终于有人骂了起来,司机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急转弯,一个急刹车,一座别致的水泥砌成的古朴的门楼就在眼前。滴水洞到了。
这里离韶山仅4公里,却少了大多数的游人,显得清静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沿着大路走去,路旁的一座水库据说曾经是主席的游泳池,虽然水面和水质不知比韶山好了多少,虽然可以自由畅游,但缺少了乡亲们的喝彩声,也没有了乡亲们注视的目光,主席当年是否感到有几分寂寞?
岩壁上有不少赫赫有名的游客的留言,很庄重地铭刻,涂着红漆,看了一圈,还是痴呆了的毛岸青用歪歪斜斜的俄语写得来几句话更引人注目。走进那栋不大的别墅,也就是很普通而已,旁边还有一排平房,那是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所住的。只有主席住过的那间房,那张床,那个宽大的写字台,还记得1966年那个难忘的六月。
那时主席下决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夜,是真正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全国一片热情高涨,他却悄悄地来到这里,就在那栋小别墅里,就在那片不大的坪坝上,天知道这位伟人想了些什么,算计了些什么,决定了些什么,但无疑的是那段时间,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主席一生,肯定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
滴水洞的右侧有一片竹林,不大,但青翠极了,据说主席父母曾经帮他讨得一房媳妇,未过门的,死后就埋在那里,主席是知道的,不知他当年是否会去她的墓前祭奠一番?倒是从别墅旁边的防空洞步步上行,就可以爬到滴水洞后面的山坡上去,那里更加荒凉,加上以前是军事禁区,连种田的都没有。
顺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就可以一直走到“石三伢子”的石岩前。据说主席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儿子能长命百岁,就到那里祈求过山神,“石三伢子”也就成了主席的乳名,不知是否,但据说主席1966年的确去过。我们只走了一段就放弃了。主席在给江青的信里把这里称作“西方的一个洞,”但他肯定不喜欢这里,如同不喜欢韶山一样,仅仅只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主席两次回乡都在六月,我们也是六月去的韶山。满目翠绿,很是养眼。到滴水洞来的经历令我们后怕不已,便索性从滴水洞步行走回韶山,区区四公里路,还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是乘汽车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