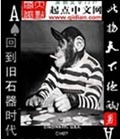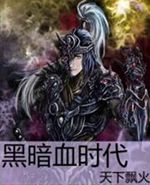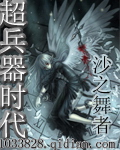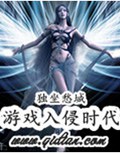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齐湣王所受的酷刑,恐怕是古来君王中最惨的死法了:淖齿把齐湣王的筋给活生生抽出来,拿筋当绳子,把齐湣王悬吊在宗庙的房梁上。筋的尾部大约还在肉体里。齐湣王疼痛无以言表,“宿夕而死”(就是从傍晚一直吊到次日黎明,才活活疼死)。
齐湣王是个胖大的人,史料上说他“颜色充满”,即便在流亡的过程中还“带益三副”(腰带大了三围),这样大的身躯,靠一根筋是吊不住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淖齿是抽了他多少根筋出来,才吊他在梁上。
齐湣王被痛吊着,欲死欲活,淖齿还对他进行了拷问和数落:“齐国高青、博兴这两个地方,数十里的地面,下起了血雨,血水沾湿了人的衣裳,王你知道吗!”
齐湣王哼哼说:“不知。”
“齐国另一个地方,大地开裂,直至黄泉,你知道吗?”
“不知。哎唷~~疼死我啦!少说点罢!”
“有人在王宫殿前哭泣,求之不得,而闻其声,王你知道吗?”
“不知。那~~又~~怎么了!”齐湣王有气无力地喘出微弱的几个字。
“呵呵!”淖齿说,“天雨血,沾人衣湿,是天在警告;地裂至泉,是地在警告;有人当殿而哭,是人在警告。天地人都在警告你,而你不知,还在胡作乱为,怎能不受诛杀?”这固然是淖齿为自己弑君找虚无迷离的借口,但也折射出齐湣王不恤民力,外战频频,对苍生的残耗,引发了民间的怨气。
齐湣王已经没辩解的力气了,为所有罪孽承担责任,他耷拉着头,等着“宿夕而死”,血一点一点地滴答着。
莒城庙堂里,公元前284年的这一夜,断断续续传来的,是齐湣王临死煎熬中的哀呼。
后人论齐湣王:“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然而在对外战争中耗尽国力,“矜功不休,百姓不堪”,终于诸侯合谋而伐之,不但没有“兵动而地广”,反倒国破而身亡,为天下笑。
齐湣王早年曾经罢斥他爸爸留下的“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显然欲振奋有所作为,于是击楚五年、伐秦三年、败燕十万、吞宋一国。
但是齐湣王的一切败亡,都是以吞宋为转折点。
该怎么看待齐国吞宋这件事呢?难道不应该吞宋吗?德国人“克劳塞维茨”在其著名的《战争论》一书中指出:“进攻要适可而止!——因为,占领区的扩大、交通线的延长、战斗伤亡和疾病减员的增多等,都会削弱进攻的力量,所以进攻者必须掌握时机,量力而行,适可而止。进攻者应该在自己尚能组织有力防御而敌对势力的反攻力量尚未形成之时,立即转入防御,这就是进攻的顶点。如果超越了进攻的顶点,就会招致敌人比自己力量更强大的反击;如果过早地停止进攻,则会减少应该取得的胜利。正确判断进攻顶点是非常重要的。”
齐湣王就在于没有把握好进攻的顶点。他一味勉强吞宋,超出自己的防御能力,当列国干涉部队纷纭来攻的时候,齐国已经力弊兵疲,无力防御,不但宋国守不住(立刻被诸侯瓜分),连齐国本土都被突破得七零八落。
齐国的先哲管仲早就阐述过“得地而国败”的规律。老是战胜,漠视“进攻的顶点”,是危险的。所以要提防“唯战胜论”。
在朝鲜战争中的后两次战役,就是因为志愿军推进的距离超过了进攻的顶点,打到三八以南几百公里,补给和对占领区的防御都不够,结果在敌人的反击中吃了大亏。
从前,夏桀灭有缗而亡其国,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吴王夫差屡战屡胜而亡国,日本在二战中屡屡战胜却最终残废,都是因为进攻超出了防御的顶点。频频“战胜”虽好,却把国君的胃口诱得更大、更贪,更想出去打仗,于是又出去频频打仗,对国家的消耗也越来越厉害。终于把自己消耗得不行,最终失去防御强敌的能力,由胜转败。这就是“屡战屡胜而亡其国”。日本在二战中的发起和败亡,正体现了这么个规律。“战胜”是一种双刃剑,可以杀人,也可杀己,这是战争的辩证法啊,也就是道家所说的“太强则折,月满则亏”吧。
我们看古式建筑房檐上,常有一个仙人和九个动物排列着。那个排在最前面的骑凤小仙人,据说就是齐湣王。“小仙人”齐湣王的位置已经非常领先了,但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会掉下房檐来摔得粉身碎骨。这真是寓意深刻,正是齐湣王一生的写照,是一个形象生动的“持盈保泰”理论宣传画。
唉,说是这样说,可谁又真能当着春天的迷醉时,想得起及时挪走梯子,从而把春风留在人生的房顶呢?
春天属于飞翔,飞翔高于一切。
附:公玉丹先生二三事
公玉丹,就是齐湣王曾经派至赵国的使臣,许诺给李兑蒙邑封地的。据《吕氏春秋》说,当齐湣王流亡时,一边散步,一边问公玉丹:“我已流亡国外了,却不知道流亡的原因。我之所以流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公玉丹回答说:“您之所以流亡国外,是因为您太贤明的缘固。天下的君主都不肖,因而憎恶大王您的贤明,于是他们互相勾结,合兵进攻大王。这就是大王您流亡的原因啊!”湣王很感慨,叹息说:“君主贤明原来要受这样的苦啊!”公玉丹就是这么蒙骗他。看来齐湣王身边,除了间谍,就是佞臣,能不灭亡吗。
齐国的地理位置不太好,如果换了秦国,遇上强敌的时候可以向陇西撤退,战略回旋余地大,伺机反攻。但齐国背负大海,没有战略回旋余地,总不能到海上去吧。齐国人大概还不知道去日本发展。只好死守。
首先,齐人死守莒城,乐毅猛攻,莒城齐军拼死抵抗,敌人数年未能打入城内。于是绕过燃烧的城市,在周边浪战一通,东西长蹈,把各地的齐军一顿暴打,五年之间陆续下齐国七十余城,掠夺财货,尽输于燕国。也有说法是,乐毅“屠”七十余城。燕军一直打到了东海附近的即墨,遇到坚守,这才像吃撑了的野猪,打着饱嗝坐下不动了。乐毅屯扎攻打即墨。即墨大夫战死,但即墨仍久攻不下。
于是,有“红眼病患者”进谗给燕昭王说:“乐毅呼吸之间克齐七十余城,区区莒、即墨两城却迟迟不下,非力不能拔也,他是在玩寇自资,是想在齐国南面称王啊!希望大王早行处置。”燕昭王却置酒大会,当着军政干部们狠狠地批评了红眼病患者,然后牵出去斩之。
燕昭王明鉴万里,不愧于一个“昭”字。
不过,上述这个斩“红眼病”故事,大约是假的。燕昭王未必明鉴万里,他就曾经听信谗言而猜忌苏秦。而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说的这个故事,不见于先秦及汉朝的各种古书,很可能是司马光瞎编的,以便教育皇帝老儿向燕昭王学习。大约宋神宗一会儿用改革派的王安石,一会儿用保守派的司马光。司马光嫌他耳根子软,不能善始善终。
但是,我们也奇怪,乐毅能下齐国七十余城,为什么对莒、即墨却多年久攻不下?这是因为齐国共设“五都”,五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训练的常备兵,即所谓“技击”,也称为“持戟之士”,因而有所谓“五都之兵”,也称为“五家之兵”。在对外作战时,“五都之兵”常常被用作齐军的主力。临淄、平陆、高唐,都是齐国五都之一。即墨、莒,大约也是五都之一,乐毅遇上了硬石头,不能逞志。
这时候,即墨城里冒出了一位满肚子鬼主意的人,名叫田单。
田单,是战国时代的韦小宝,满肚子坏水。最初他在临淄农贸市场里当办事人员,负责记录商品交易和盖章之类的,是个不知名的人。公元前284年,临淄失陷,他随着本族的人逃到安平。当燕军进攻安平时,他让族人把车两边的车轴凸出部分锯短,以免互相碰撞,影响行动。因此在城破撤退的时候,逃难的人驾车争路,车轴互相牵挂,挤做一团,多当了俘虏。只有田单一家因为搞了这个小改革,车行灵活,得以安全撤到即墨。燕军攻打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大家就公推田单为将,让他负责守卫即墨,因为他小聪明多。
这时候,燕昭王死了(公元前279年)。
新君燕惠王登位,这家伙从前与乐毅“有隙”,就是feel sick at him,互相见面吐唾沫,感情上有裂痕,想拿掉乐毅。与此同时,“韦小宝”田单派人来使反间计,在燕国大街上到处嚷嚷:“齐王已死,齐国五年无首。乐毅以伐齐为名,迁延战机,在即墨城踯躅不进,实欲拥兵自立为齐王啊!!!”
韦小宝这么一喊,燕国满大街的都知道了。燕惠王呸呸地连吐唾沫,朝着想象中乐毅的脸。于是,燕惠王派笨蛋骑劫为将,直赴前敌,临阵替代乐毅。
针对无能之辈骑劫的到来,田单搞了一系列诡诈计谋来忽悠自己的人和自己的敌人:
一、以心理战恐吓敌人。田单下令城中百姓吃饭前必须在庭院中用食物祭祀祖先,从而引来铺天盖地的飞鸟,上下飞舞于即墨城上。城外燕国人看了,以为上帝垂下了自己的“铁布衫”罩着即墨,惊诧万状。
二、当时齐国无王,田单就找了一个“海公公”,让他扮演神主,对之极其恭敬,每对即墨人下令,都矫用神主旨意,加强自己的权威。
三、巧妙地利用间谍把假信息传给燕军,说齐人最怕被挖祖坟和割鼻子,促使燕军在城外大施暴行:把齐人的坟墓掘开,焚烧其中的死人,又把齐军俘虏的鼻子都割去,高兴得城外的蚂蚁们纷纷举着鼻子游行。城中军民见此情形,无不切齿扼腕,涕泣求战,怒自十倍,皆抢着欲与燕军决一死战。
曾经称霸的齐国人是有志气的,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就是齐国人的写照。火烧临淄是齐国人的世纪噩梦,每个即墨人夜里说出梦话,都喊出打倒燕国侵略者的口号。终于,在一个漆黑不见手指的夜晚,即墨城墙底部事先凿开的一列数十个洞穴,突然同时爆炸,从中冲出一千余头“火牛”:牛角绑着利刃,牛尾巴绑着浸蘸了灯油的柴苇,牛身披着五彩龙纹的红绢(齐国盛产丝绢)。千余头火牛狂奔而出,仿佛火龙一样(这牛屁股着火了,自己能不牛急嘛!),猛顶猛撞燕国士卒。
五千壮士跟随火牛其后,杀声震地。城中老弱也敲击铜器,鼓噪呐喊,声动天地。燕军睡眼朦胧,拎着兵器光膀子作战,眼见无数蛟龙冲来,寒光闪闪,直掘人腹。燕军惊骇莫名,猝不及防,胸洞腹穿,张皇大乱,自相践踏,一败涂地,主将骑劫竟死于乱军之中。
田单“火牛阵”一战痛殴燕军,燕军大奔,主力尽伤。由于主将已死,无人调度,燕军攻下的七十余城也全没了保证,燕军能不能组织逃离齐国本土,都是问题了。田单追亡逐北,势如破竹,尽复齐国攻下的七十余城。燕军蹀血他乡,纷纷退出济水以外。
田单,挽狂澜于既倒,复齐国之社稷,逞豪杰之英能,被齐湣王的儿子齐襄王,封为安平君,授相国印,执齐国之政,亦可谓乘时而起者也。孙子所谓:“善出奇者,(奇招)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田单之谓也。
看来,战国时代的贵族们,也不全是败类。就像布衣之中也有白薯一样,贵族之中也有英豪。田单,就是齐国田氏王族的远亲,勉强算是个贵族,然其矢志刚坚,成于败势,亦如此。
可惜的是,贵族之中就算偶有英豪,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