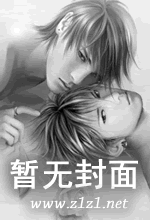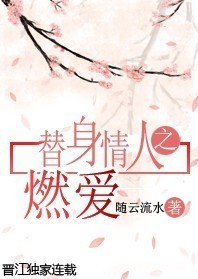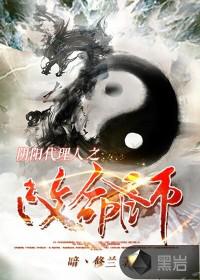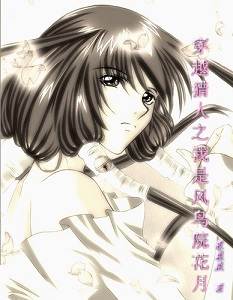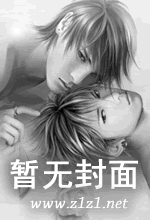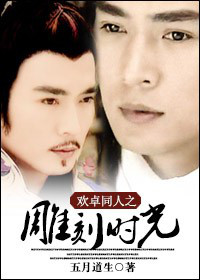人之窝-第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和张南奎、许达伟、柳梅、阿妹、朱品都川流不息地拥到了王先生的房间里,
围着王先生问长问短,忙这忙那,最主要的是问他都受了哪些折磨,伤在哪里。
王先生不讲他受刑的情况,只是苦笑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王师母却忍不住要说了:“真是遍体鳞伤啊,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些
人和畜生差不多,不是娘养的。”从来不说脏话的王师母也忍不住要骂人了。
张南奎也气愤:“现在我也要反对孔孟之道了,‘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
人之初性本恶!他们对同类相互残杀,竟然把打人作为一种乐趣。”
许达伟又有见解了:“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的变化是由教育来决
定的。”
王先生竟然也点头:“是的,那些打人的人接受了一种教育:对敌人要冷酷无
情。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敌人,都是些反革命分子,是恶棍、是魔鬼、是带着
瘟疫的过街老鼠,打几下有什么了不起,最好是要彻底地消灭!像希特勒消灭犹太
人似的。何况打人和吸毒一样,多打了也会上瘾。那些晚上值班看守的人,到半夜
里要打磕睡了,就把我们这些人拉出来毒打一顿,提提精神。”
我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说起来苏州人还是软绵绵的,尚且把打人作为一种乐趣,
如果我不从那个山城里逃出来的话,说不定要被那些“天不怕”的人挖出心肝来炒
韭菜呢!
朱益老头懂得三教九流,他家里有伤药,是装在一个朱红色的葫芦里。据他说
此药比云南的白药还要灵验,是专治内伤的。他打开药葫芦,取出十几粒,调在半
杯黄酒里,给王先生服了下去。说是眼下以后出一身臭汗,身上青的地方更青,紫
的地方更紫,紫得发黑就证明药已生效,内伤都发出来了。
费亭美虽然不问世事已久,听说王先生受了酷刑,身体虚弱,便不糊火柴盒了,
把柳梅叫到自己的身边说:“你到大橱顶上去把一只小藤箱取下,让我找一样东西。
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我也记不清到底是放在哪里……”费亭美到底是七十多岁的人
了,人老了话就长,要是在年轻时她只会说一句话:“替我把大橱顶上的小藤箱取
下来。”
柳梅踏在方凳子上,取下了那个积满了灰尘的小藤箱。这藤箱可有年代了,还
是当年许春葳外出求学时用的,那时的书箱都是藤器或竹器,读书人不背书包叫负
笈。
费亭美打开那个小藤箱,呆呆地看着,她好像不是急于去寻找什么东西,而是
在那里寻找失去的记忆。这种记忆到底是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看见费亭美先
是愣着,过了半晌才伸出那双枯瘦的手,一只手揿住箱子,一只手在箱子里翻弄着,
在箱子的角落里寻出一根用丝绵纸包着的人参,这根人参的参须没有了,却有拇指
那么粗细。费亭美拿在手里对柳梅说:“这是一枝老山参,它比金子还要贵,当年
是老太爷留下来的,说是能使虚弱的人强壮起来,能使快断气的人多活几天。去年
抄家的时候,红卫兵不识,以为是晒干了的胡萝卜,把它摔在墙角里,这也可能是
王先生的福气吧。拿去,给王先生用了吧,他是你公公唯一的至友,希望他能长寿。
他不像我们,他还要写书。我们这些人嘛,活着和不活都是一样的。”
朱益老头见到了这枝老山参,眼珠子都突出来了:“不得了,这参是可以起死
回生的!快把它蒸了,分几次眼下去。”
王先生吃了朱益的伤药,又服用了一枝老山参,身体确实复原得很快,可以上
上下下地爬楼梯了。
夏海连夫妇也回来了,没有几天却又被他的一个老部下接过去。他那位老部下
接管了一座疗养院,请他们夫妻俩去治病、疗养、休息。打过仗的人一旦还个清白,
关系网仍然是四通八达的。
那汪永富不敢再嚣张了,他不仅是被我们抓住了辫子:在外面好像也没有了市
面,冲冲杀杀的人已经不大需要了,鸟尽弓藏也是理所当然。汪永富好像也有自知
之明,不大出去活动了,整天粘着个陶伶娣。陶伶娣却有些推推搡搡的了,她发现
这个赤脚司令已经没有多大的花头。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吧,城内外早就没有枪声了,城门也不再紧闭。乡下
人进城卖菜,城里人下乡钓鱼,进出都很方便,没有那种手执大刀长矛的人在城门
口守卫。工厂也都开工了,商店正常营业。北京开过了“九大”,林彪被规定为接
班人,而且写进了党章里,造反时卧铁轨的王洪文,当了国家的主席。一般的人对
这些事也都认了,谁想当主席就去当吧,只要不把一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
生,就算是上上大吉。那时候的人要求都不高,只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天。
想不到却是平地一声雷,苏州城里又闹翻了天,城市里的人要下放到农村里去!
先是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毛主席说很有必要,那就没人敢说是没有必要了,那些在校的学生,
那些首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都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要到农村里去插队落
户。这件事虽然不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样到处有枪声炮声,实际上却是此时
无声胜有声。哪家没有孩子,哪个孩子没有许多亲戚,下放一个知青最少要牵动五
六个人,有人是三房合一子,那就有几十个人不能平静。千家万户都骚动起来了,
仅仅许家大院里就有十一个知青要下农村,包括王先生家的小革命王玉树,许达伟
家的亮亮和明明。亮亮和明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了初中,也算是知识青
年,其实只是小学毕业。
第一个雷声还在天上滚动着,第二个霹雳又从晴空落地:干部、教师、医生以
及那些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人统统都要下放,一人下放要带走全家,要注销城市
的户口,到农村里去安家落户永远当农民,而且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江苏的
北部去,到那黄海之滨去接受考验。
外面的谣言纷纷,说这是林彪下的一号命令,那位救过夏海连的司令员又来个
快刀斩乱麻,一人走全家走,从城里挖根,到农村生根,省得牵丝攀藤。
下放的主要目的是准备打仗,要把城市里那些屁股上不干净,心里面有怨气的
人统统赶到农村里去,等到美帝或苏修打来时就没有人里应外合,就没有人去做奸
细。所谓的下放实际上是在城市里“扫垃圾”。这些传说虽然无法证实,从行动上
来看倒也不完全是假的。被批准下放的人都是些牛鬼蛇神,走资派,以及那些所谓
站错了队的造反派头头。当然也有一些自愿革命的人还排命地挤进去,他们认为到
了乡下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许家大院是动员下放的重点,上面特地派来一个叫顾炳的人来领导林阿五完成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听说这顾炳是一位复员军人,却又没有穿军装,那时候,
没有当过兵的人还要千方百计地弄一套军装来穿穿,有着时髦和防身的双重意义。
顾炳当过兵,为啥不穿呢?顾炳自己说是穿的时间太长了,换个新鲜,这话也不知
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是真是假,这顾炳有点儿来头,据说是革命委员会派来搞
试点的。顾炳对许家大院一无所知,只是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了解到一些情况,知道
许家大院是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好像是个黑窝,也是个染缸,千万要提高警惕,站
稳立场。他同时还从上面了解到,这林阿五虽然是个好人,可他和许家大院里的牛
鬼蛇神关系太深,思想右倾。
按照上面的标准和下达的任务,许家大院里的老住户除掉朱益老头之外,其余
的人家都要下去。一人下放,全家都走,小至吃奶的儿童,老到……还没有死。林
阿五对谁走谁不走做不了主,好在这些该走的人也不需要他去动员,许多人都是他
所在的单位批准,然后带走大院里的家属,连许达伟也是被柳梅带走的。最奇怪的
是汪永富也被下放了,他的工作单位是前远五金零件厂,倒是要林阿五去说服动员
的。
林阿五动员汪永富下放时,思想一点也不右倾,动作迅速,立场很稳。他一得
到消息就到一号门里去找汪永富,看见汪永富在那里哄着陶伶娣,陶伶娣气呼呼的。
林网工也不用什么虚词了,当着陶伶娣的面说:“汪永富,你被下放了,七天之内
离开苏州,你准备准备。”那口气就像是下最后通牒。
“啊,居然下放到我头上来啦!”
“你是司令嘛,当然要带头。”
“不行,我要去找……找我的小兄弟。”
“随你的便。不过,你现在要去找军代表,找小兄弟是没有用的,你的那个叫
尤金的小兄弟也下放了,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也难保。”
汪永富的脸涨得通红,眼睁睁地看着陶伶娣,僵在那里。
林阿五也看了看陶伶娣:“伶娣,你和汪永富的关系现在要确定了,确定是夫
妻就跟他一起走,不是夫妻就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算个啥呢?”
陶伶娣听到这句话,立起身来把手一甩:“谁和他是夫妻,桥归桥路归路!”
走了。
陶伶娣当然要走喽,她刚才就和汪永富斗过气,她说汪永富是个骗子,是说大
话把她骗到手,却原来是个狗屁司令,一啥呒啥,一钿勿值。
原来,陶伶娣的一家也要被下放了,因为陶金根早就不做’大饼油条,陶伶娣
也没有个固定的职业,他们一家算是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在下放之列。陶伶娣听说
下农村就像是下地狱似的,风吹雨打太阳晒,那日子可怎么过呢!连忙去找汪永富
想办法,死活也要留在苏州。汪永富想不出办法来,说他们那一派的人没有一个是
当权的,他们算是站错了队。
陶伶娣一听说汪永富也要下放,马上就下了决心,决心和汪永富一刀两断,了
却此情。这可不是什么爱不爱的问题,真家伙,要到农村里去受一辈子的苦,遭一
辈子的罪,爱有什么用?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也不能两个人整天都睡在被窝
里。
陶伶娣决定不求人了,自己来救自己。报纸上说下放要自觉自愿,我不自觉,
不自愿,死赖着不走,看你怎的,反正现在已经没有红卫兵打人了,怕你!顶着,
拖着,等到下放的高潮过去以后再作打算。什么打算现在也不清楚,有一点她是很
清楚的,像她这样标致的女人是不愁找不到靠山的。
陶伶娣一走,汪永富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不回来也好,有什么能耐骑什么
马,像陶伶娣这样的牝马决不是现在的汪永富能骑的,骑上去也要被摔下来。汪永
富想是这样想,想想又不服气,多少年来他都想出人头地,好不容易碰上“文化大
革命”,他不顾一切地冲在前面,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含着眼泪,喊着口号
向敌人冲过去!结果却是站错了队。老婆走了,房子没了,光棍一人要到农村里去……
汪永富又热泪盈眶了,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