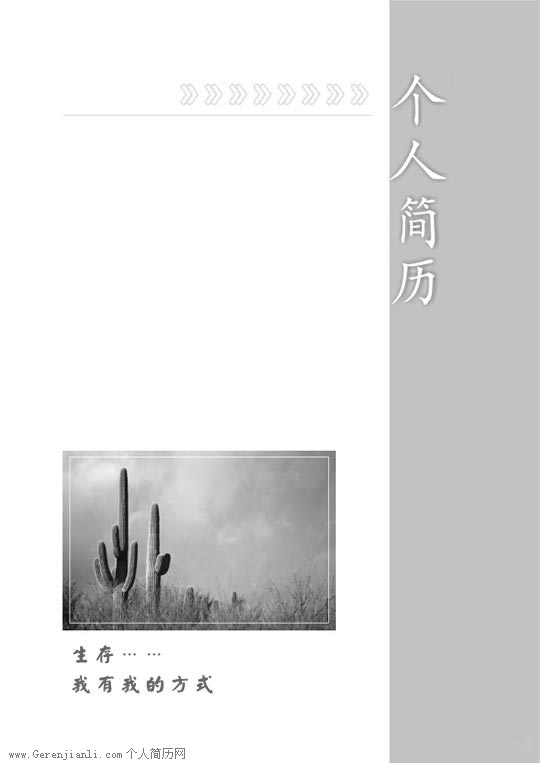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件事,是既同我们中宣部科学处也同中宣部文艺处有关的,那就是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那件事的起因是,《红旗》杂志社从吉林调来了一位文教书记郑季翘担任这个刊物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陈伯达)。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中认为形象思维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对使用这个概念的人进行批评,而且批评时用字相当重。郑抗战前是我清华同学,在学校学中文。他是“一二·九”的参加者,也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的同事。可是我以前没有看过他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这回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文章。这篇东西,是有他独立见解的。但他并不把这篇文章拿出去发表,而是送到中宣部来要求“审查”。中宣部收到郑写的文稿和来信后,周扬就把我找去商量。我们两个人认为这类学术问题属于争鸣范围,中宣部不应该去“审查”,但又都认为不能不给以答复。我主张中宣部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请郑参加,这样我们中宣部既表示了对他写的东西的重视,同时也处理了他的来信。周扬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办法。他还认为中宣部以后可以经常开开这种会议。我当然赞成这个主张。周扬让我同陈伯达商量,陈伯达也赞成中宣部可以多开这样的会议。于是我提出一批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其中有哲学所研究黑格尔的杨一之(他单独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贺麟(他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并参加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王玖兴(他也参加翻译了《精神现象学》,北京大学的朱光潜(他是“美学”专家、黑格尔《美学》的译者)和王大庆。我们还提了邓拓、廖沫沙等人。文艺处也提了若干人。座谈会就在中宣部教育楼会议室举行。周扬主持会议,陈伯达、郑季翘参加。那天朱光潜未到。会上各抒己见,发言集中在所谓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之间的关系:所谓形象思维究竟属不属于思维的范围;形象思维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关系;在美术、雕刻中的形象思维与音乐创作和欣赏中的形象问题等等。周扬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会上也讲了不少话。
虽然周扬认为这样的会中宣部可以经常地开,但事实上只开过一次,没有再举行过第二次。
关于周扬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所作的贡献,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建议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一些同志专门写一篇周扬与自然科学的文章。他们对一些具体工作的情况似乎记忆得比我清楚。
60年代刚开始不久,周扬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同时聂荣臻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在建国前的四五十年代,周扬曾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中央局担任过工作,同聂总本来就很熟,在医院里二人有比较从容的时间交谈。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虽不在场,但是从周扬出院后和我的谈话中,也从周扬的表现中,看出这次谈话对周扬思想上的启发很大。在这之后周扬对科学工作明显地比以前更加热心了。他对政治运动中科学工作者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表示很不满意。他特别强调科学工作要多出成果、出人才,党应该保护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1956年党的八大是一个开得非常好的代表大会,不久前我写了一篇纪念八大的文章。但是八大路线只维持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因反右派斗争实际停止执行了。不过在党领导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工作方面,周恩来、聂荣臻等仍通过坚持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办法,和制定科学十四条等办法,一直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八大路线。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十多年中,同时在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两个系统中工作,我知道这两个系统中的指导思想是有相当差异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是“抓政治抓思想”,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跟得很紧。国务院抓建设工作,对搞阶级斗争不那么积极,甚至有些抵触。周扬在与聂总谈话后,依我观察,思想上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比较多地倾向聂总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领域中采取的做法。
科技系统也就开始找周扬参加他们的活动。1961年4月中国科协在北京饭店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请周扬去做报告。他答应了。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对聂总在医院里跟他讲过的一句话表示欣赏。聂对周扬说:“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周扬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是周扬最早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人写到中国科学的院史里。在中国科协这次讲话中他也讲到,要求自然科学家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品、农民生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文学家创作文艺作品、社会科学家写出理论著作一样。周扬讲,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来适合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在这次讲话中他非常强调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1956年5月由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演讲中提出之后,科学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许多人怀疑这个方针的真实性,也有人翻了过来,认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在人们头脑中变得很模糊。因此周扬在这个讲话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周扬不只是在这个讲话中重申了陆定一讲过的那些语言,还作了自己的发挥。在反右之后,有一次他去湖南了解到那儿有些高等学校又重新对遗传学中的门德尔摩根学派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他就严肃地进行制止。他看到科学处办的一期简报中反映各地发生反对百家争鸣的现象后,立刻指示中宣部把这期简报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要求他们注意克服这些现象。
三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的事、特别在人事方面,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去作“副业”。现在我写这篇文章,读者们当然会希望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我也觉得应该讲一些当时听到的情况,讲一些当时自己的想法。可就是说不出什么来了,真很抱歉。
但是我毕竟在中宣部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会上会下总听到见到不少事情,还是可以写一点的。
比如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我不敢说他在文艺界的表现究竟如何,我只能说说他在中宣部内给我留下的印象。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关于这个口号之争,30年代在上海的刊物上的文章,作为一般的读者,我倒注意了一下,但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原则的分歧。觉得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东西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来争去理解不了,也就不再关心,我也一直没有注意胡风与胡的朋友们的言论和行动。反胡风斗争后毛泽东批注的那几个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我当然看了。看了仍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胡风等人消息很灵通。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中写到1952年由于“学习杂志错误”几个“理论红人”受批判的事。我就是信中所说“理论红人”中的一个。而且信中所说的陈伯达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是我所不知道的。我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件事,但是除了胡风几位提到此事,至今我还没有得到其他信息。从公布的那些信件中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来。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的时候),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是全都知道的。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一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常常说他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
现在胡风案件早已正式平反,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的,有的文章作者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上面写的是我在中宣部期间周扬给我留下的印象。
关于丁陈事件。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干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我有些奇怪,因为丁的历史似乎大家早就知道,组织上想必也早就审查过,否则不会到中宣部当文艺处长,陈企霞也是在延安经过整风审干的人,怎么一下子又都有了“严重问题”。
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可是这个问题又不好提出来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因而许多年一直不清楚。加上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