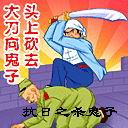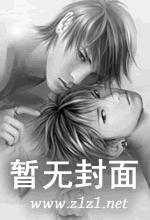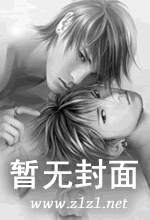鬼子进村-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人的面就强奸,那女孩的母亲中了毒,也躺在院里,听着女儿直叫“妈呀”,眼泪直流。还有一个鬼子,闯进院后,转了几圈,一把拖出一个年仅10岁的幼女,就按在地上奸污,那女孩叫得那个凄惨,在场的人都捂着耳朵不敢听。那女孩的奶奶也在院里,在一边给那个日本兵磕头求饶,可那个鬼子仍不停止。有个外村的青年妇女,让鬼子抓住后,拖到李化民家院子里,脱光衣服,又抓来北疃村的一位男青年,也脱光衣服,然后强迫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鬼子还摘来不少石榴花,插在那位青年妇女头上,一大群鬼子围着看,开心得不得了。随后又将那个妇女拉进屋,轮奸了。
有极少数人,逃出了北疃村。像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在洞里熏昏后,被日本人抓来的民夫从地道里拖了上来。当时是拿一根竹竿,前头绑上绳子,就像套马杆差不多。由民夫套在人身上,上头一拉,给拖出来。赵树光回忆说,日本人把这些身上带着枪(大都拿着枪就昏过去了)的战士、民兵,都押到村西一户人家关押起来。大伙口渴难忍,就十几个人一齐喊:“要喝水。”日本人可能是想留下活口,怕都死了,就让民夫送来一桶水,水一下肚,都一阵难受,一个个忍不住吐起来,吐完了,反觉得轻松了。不知怎么,日本人防守得不严,虽说房顶上有哨兵,但房门没锁,人也没绑。于是赵树光他们乘着黑夜,敌人的哨兵也正打盹,一个个蹑手蹑脚出了房屋,又贴着墙往村外撤,后头不知谁不小心踢了水桶,“当啷”一声惊醒了敌人,“叭叭”地乱打枪,但赵树光等人已逃到村外大麦地里了。一些百姓,也设法逃了出去。27日中午,听着北疃村的枪声稀疏下来,又见村里房顶上站满了鬼子,周围村里的人就知道不妙。接着听见村里传出阵阵妇女的哭叫声,零星枪声,鬼子的嚎叫声,就知道北疃村这回遭了难了。都说咱的干部呢,咱的队伍呢,怎么不来搭救一把?其实,在北疃村外头的干部,何尝不想支援北疃。县委书记赵铁夫回忆说,在5月27日上午,北疃村的枪声、炮声正响成一片时,他就派人去东西赵庄送信,请据说是驻在那儿的分区独立营赶快来支援。结果没有回音。北疃那边枪声一停,凭经验他就知道情况不好,急得坐立不安,正说摸过去看看,在西城村外遇见从北疃村跑出来的县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宗波和四五个战士。马一见赵铁夫,就说赵书记,大队和老乡们全给捂在地道里了,我们是顺着地道走,用刺刀把地道掏透,出来一看是块麦地,才算逃出来了。赵铁夫一听又痛又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写了封信,让他们坚持一下,先去找驻赵庄的分区部队,请他们火速支援北疃,但仍无消息。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分区部队也没有来。周围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急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300多,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90多,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29人。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耷拉着死去
一些当年去北疃村掩埋过尸体的老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一听问及当年的那些事情,脸上立刻显出痛苦的神情。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有些事情,问了也不说。似乎很不愿回忆当年那悲惨的情景。
问:当年鬼子走后,您去了北疃吗?答:去了。
问:您都看到些什么呢?答:
问:除了街上、房里、院里、井里有尸体,地道里还有尸体吗?答:有。
问:您当年下地道去拖尸体了吗?答:去了。
问:地道里,又是个什么情形?答:(沉默片刻)吓人。拿着油灯下去,一照,半明半暗地,一溜死人。一个人我是不敢下去。
问:尸首不是一二天就都埋了吗?怎么材料上说都臭了?答:那两天天热,还没进村,就嗅见臭味了。
老人说的完全是事实。在5月28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途经北疃村时,也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回忆说:“5月28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
骑兵团没有在北疃村久留,李健他们只是告诉村干部,请他们尽快把群众和战士的尸体掩埋好,部队也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在北疃收尸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看着骑兵团几百匹战马在夜幕中渐渐远去。老人们说,那天晚上,大家在躺满尸体、村内外弥漫着死尸的气味的北疃村忙碌着,一个个都装出十分平静,似乎这种场面见多了的神情,相互见面,什么也不说,只是轻声讨论着具体事:你看谁谁家的尸首咋办?你看谁谁家还有活人吗?其实,人人心中都堵着一大团东西。月光下,神态各异的死人宛如活人,而面色难看无声无息地忙碌的活人,却犹如行尸走肉。骑兵团要是早一天来,是决不会坐视日本人遭害百姓的。所以,多少年以后,还有人埋怨说,当年分区部队咋就没来呢?老人们讲,那干部们一直说,分区部队会来支援,大伙听了,觉得心里有底,才守着村子没跑。要是说就是县大队这些个人,那就又不一样了。对此,当年任定南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7)
…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有按原定作战计划来支援,并作认真处理。但均无结果。
赵说,“我于此事,于194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当年在北疃指挥战斗的赵树光,倒没提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来这档子事。但他提到,那天午后,敌人暂停进攻——也即大江芳若开会时,他曾想在敌人完成新的部署前突围,但当时在村里的两位抗三团的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还是应打到天黑再撤,他们一个是长征干部,一个是参加过19路军上海抗战的。游击战经验也有,阵地战经验也有。赵树光觉得也有道理,就没突围。
如果当时坚持突围,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不知道,历史,是不承认“如果”的。
还有材料说,日本人早上一围村,就根据汉奸送出的地道图,挖断了北疃通往解庄子的地道,插上了木桩。一进村,又挖断了通南疃的地道。如果通外村的地道还通,损失是不是也小一点呢?
我们到北疃村那天,正赶上电视里在播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那里头也有日本鬼子“屠村”(借用“屠城”一词)的场面。
我们和老乡们挤在炕上,一边看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一边说着话:问:您瞧着这场面拍得怎么样?还像不?答:(笑)还行吧。
问:可我们总觉得,还不太像。
答:比起当年的实情来,是还差点事。你瞧那衣服,还穿得挺整齐。我们当年瞧见的死人,好些是赤身露体,还有好些让火烧了,让狗咬了,那衣服只剩下几个片片,半拉子了。
还有那表情,那死人的表情咋能都一样呢?有的是眯着眼,张着嘴,一瞧就是刚从地道里爬出来,就让鬼子给整死了;有的是龇牙咧嘴,那是出了地道有一会了,再让鬼子活活折磨死的。不一样的。(停顿片刻)那死人,也是有表情的。
问:现在村里还有残存的地道吗?答:早没了,64年发大水,全泡塌了。
■6月8日,肃宁县雪村,雪村——“血村”
如果在那年6月走进河间县城,你会看见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男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
开始是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从他们的七零八碎的话语中,我们对常德善司令员的外貌和人品,都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一员好将,可惜了。”
“劳动人民体格,山东大汉,有近1米80的个头吧。”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可以想见,常司令员是一个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很成熟、很勇敢的一员战将。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常德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他们捕捉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打开历史的记忆阀门,看一看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那悲剧的时刻: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也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并把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以免被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