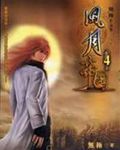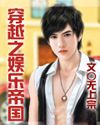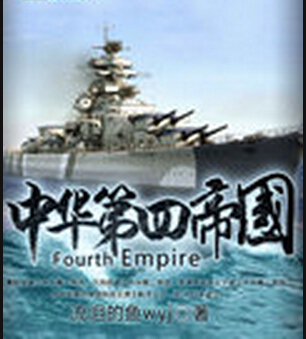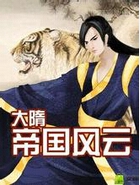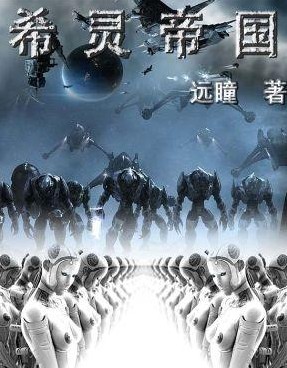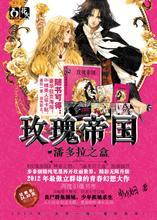帝国雄兵-第1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于英雄小说
…
英雄是实践的产物,也是艺术家的创造。战争题材的英雄创作,是英雄主义的乐园。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和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战场都是英雄创造的最好土壤,围绕这些事件,苏联文学家、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的英雄典型、作品。在我国,长征,首先是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动荡,海内沸腾;日寇入侵,国共内战,正“国家有难,四海悲歌”,山河罹难,百姓涂炭,多少英雄奋起救中华,碧血琼花,血沃华夏八年抗战,义勇军号声铮铮,热血砌筑万里长城三年解放战争,摧枯拉朽,百万雄师过大江,蒋家王朝顷刻瓦解;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多少英雄,多少题材生与死考验英雄,这里的英雄,是征杀的英雄,是英雄小说的主体。
…
关于英雄小说,约莫回顾了一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好像没有专门这样分类的,但是不妨说,从文学实践来看,英雄小说是存在的。它是专门写英雄的小说。如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奥德赛》、欧洲中世纪《尼伯龙根的指环》等,我国也有《西游记》等。
“百科全书式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项羽是司马迁着力塑造的英雄。 “超秉赋英雄少年”,“身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论英雄,非他莫属”。“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先声夺人、排山倒海威势;“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分散聚合指挥艺术和疾如飙风战斗风格;“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
司马迁涉猎浩繁,“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动。”
然而东西方英雄小说是不一样的。英雄的概念不一样,英雄的表现也有差别。
从中西文学发展来看,在西方,英雄作为一种悲剧性的体验首先是在悲剧中被书写,而悲剧这种体裁,在中国几乎是没有的。英雄崇拜是根植于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传统,英雄是文学分析与心理学常用的概念。童话中的主人翁就是容格分析心理学里的英雄。在这种分析里——人生就是战争,人活着就是要扮演英雄的角色。
纵观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英雄史诗的发展,其英雄形象经历了从力量英雄向道德英雄、从人性英雄向神性英雄的内涵转变。譬如中世纪法、俄两国的英雄史诗。深究英雄形象的成因,就宗教观而言,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英雄史诗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中世纪法、俄两国英雄史诗则分别受到天主教教会和双重宗教观、神权政治观和宗族政治观、宗教战争观、宗教善恶战争观和民族保卫战争观的影响。在英雄形象的艺术塑造上,中世纪法、俄两国的艺术手法有同又有异,其异分别表现为悲剧性的渲染与夸张和迅速移动的时空观;而其艺术风格分别表现为庄严崇高的叙事风格和优美抒情的牧歌风格。
黑格尔曾称荷马史诗创造的英雄“许多性格特征充满生气的总和”。阿喀琉斯既是铮铮硬骨的铁汉,也不乏善良温厚和仁慈。“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
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英雄;也不是抗日作品,就一定是英雄小说。战争与和平观称量英雄,一部真正的英雄小说,一定是像小说那样从发掘人的本质中塑造人的形象,也一定有道德冲突,在正义的胜利中体现世界的悲剧性。
后记 … 英雄与悲剧
英雄与悲剧
…
为什么有时候读一本小说,英雄主角牺牲了,我们会垂泪冥索,不断追思为什么往往这样的主人公,有时候会深深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久久难忘,甚至会伴随终生?很简单,英雄主角牺牲了。主角没有牺牲的作品会不会感动我们,根据我们的体会,可能有感动,但是不会这么深刻,也不可能持久。这么说,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英雄主角牺牲了的作品,不是英雄小说,喊喊杀杀的作品不是英雄小说,开庆功大会的作品不是英雄小说,叙每日家常、工作流水账的不是英雄小说。那么,为什么一定是要主角牺牲了,才能被作为英雄来接受呢?为什么一部作品,英雄主角牺牲了,才能成为英雄小说呢?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死了人,我们的审美心理才能满足,我们的审美境界才能更上一层呢?因为我们都有悲悯之心,因为我们都有对生的依恋,对死的恐惧。如果一个英雄,像我们一样活着,我们不会把他看成英雄,我们看到的是他凡身的一面,甚至淡忘英雄的定义(在悲剧意义上,在经典意义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英雄);如果有一个人为了我们大家而献出了生命,我们会感到深深的追悔、痛惜、不舍难忘,我们习惯地把这个人称为英雄。
经典英雄的含义,决定了作品、大作品的悲剧性。英雄一定是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英雄死在我们面前,如同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悲怆嚎哭,如丧考妣,这就是英雄作品感动人的机制——我们都是人,有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我们又是结成社会的,所以这个人即使不是我的亲人,但是我能产生自己痛失亲人那般的感情——于是,一篇英雄小说,以其悲剧性的结尾,感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天下人,天下所有有同情心、怜悯心的读者,天下所有有人类心肠的人们。
…
“大作依然撼人!”
“建军节读此书更觉悲壮伟大!”
“看后除了震撼,剩下的只有感动!”
“看完了最后两章,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那是悲壮的滋味!总觉得帝国雄兵在对我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也当过兵 高喊一声 中国军人万岁!”
“正读到第六章铁列克提,那股阳刚之气感动了〇世纪的人!”
“看得我慷慨激昂”
…
《帝国雄兵》尾声中曾大军作为我西线军人英雄的代表,一位即将面临“处决”的“监外执行”,他是连队饲马员,每天有20多头骏马相伴,他没有骑马逃走;八连指导员,他的亲弟弟,曾经怆动于私,想连夜把他放走他婉言拒绝他不是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他在山上弹奏三角琴的时候,甚至在战争前夜漆黑密林中那几声微弱的“鸟叫”未必不是在做像《圣经》中耶稣在加利利旷野40天祈祷里那样的,对生命和死亡最后的思考但是,最后他选择了战场上的受难
…
英雄的血没有白流,在读者的感动中,得到了上帝般的垂悯!
后记… 英雄与杀戮
英雄与杀戮
…
拒绝堆砌在脚下的白骨、血尸、腐颅。已经拒绝看银幕上的古装战争片和现代战争片20年、30年了,因为影片的缺乏美学境界及相应的艺术水准,甚至拒绝看李云龙之类的垃圾片——不是反对歌颂我国军人,也不是不支持抗日战争——
而是指我们应该有新型的战争片了。
…
“八一”前夕,《南方周末》刊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文章披露,戎马一生的刘伯承晚年拒看一切战争电影,因为国共内战战死无数同胞,殃及无数家庭,令他不安。
《南方周末》7月28日刊登许小峰文章《建军节,应记住周成荣》介绍,周成荣是在国共内战第一场大战——绥远战役牺牲的,其过程与董存瑞炸碉堡相似,时间上还要早一年半。绥远战役指挥官贺龙在发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周成荣的名字,但他没有得到任何荣誉,事迹也未见过任何报道。原因是绥远战役中我军并没有成功。
刘伯承晚年拒看一切战争电影,他解释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啊!这会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就是从大堆大堆我们的兄弟、父老、亲人的尸体上爬过来的,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煳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这是经历过残酷战争后的肺腑之言,也算为后人留下的警示。
许小峰呼吁,政治家应具有现代文明智慧,尽力避免将政治纷争演化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对即错、你死我活的极端阶段,防止战争成为无可替代的惟一选择。
古语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老帅的仁人之心此也。
文章说:今天,国共战片层出不穷,是不是可以少一点。一遍遍用一些虚构的人物与情节,一次次上演旧日的同胞相残,而我们看到今天,已没有同胞相残的快感,也没有胜利解放的欢悦了。应该要少一点了。
…
而我不看中央电视台战争电影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是真正的英雄小说。它们有戏剧形式的一切特点:有情节,有形象,有人物,有悬念,甚至有思想——但是,没有英雄。
后记 … 英雄的环境
英雄的环境
…
英雄产生在其所由产生的环境里,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你不给他这样一个环境,你生出来的是“假英雄”,或者是次品,或者,没有英雄。
英雄产生的环境和普通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不是说,英雄小说里就没有或者容不下普通人物,或者说,有一种自然状态的专门为英雄准备的环境;而是说,小说是虚拟的,是创造性的,想象的,因此,你应该为英雄的问世准备一点条件。
英雄产生的环境,一定是急迫的、催迫的,要产生点什么东西出来、有一个大矛盾在其中运作的。
这种矛盾和冲突,酝酿着、激化着,准备着,等待着一个解决,等待英雄的出场。
她很类似——暴风雨的前夜,她很美丽,诱惑着我们。
英雄产生的环境,实际上是我们笔下的创造物,而这样的创造物,往往要假借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已知事件、年代、或历史背景,这么说,我们实际上是借重大历史事件、时代、年代,写英雄小说,创造英雄。
这样说,是不是有强调写重大题材的意思呢?或者,是不是重弹“题材决定论”呢?好像难避嫌疑;但是,作者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就是典型环境,却是确凿无疑的,肯定的。
英雄一定是产生于典型环境的。广而推之,一切小说的主角、人物,他们的性格、命运、结局,都是典型环境的产物。
李沪生、部队长、曾大军、中亚泥布拖地、高虎声、闵斌斌…只能产生于他们所处于其中、所由产生的那种环境,典型环境。
典型环境产生典型人物。这一定义、命题,曾经为恩格斯专门、重点强调过的文艺学原理,被多少人、多少年弃之如敝屣,唾弃鄙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文学状况这么烂!?为什么是一地垃圾?为什么有些人写出的东西不像样子!?为什么这些作品是那么地令人不忍卒读?!为什么那些东西尽管铺天盖地,除了短期内,被所谓的低龄粉丝,而实则是和作者同样对文学基本原理不懂、没有审美境界的人追捧外,很快就被扫进故纸堆,成为昨日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