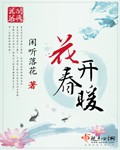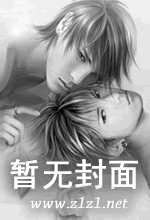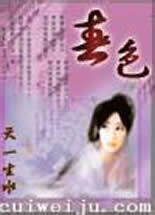太平春-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为第一场。
第二场有论、判五道、诏、诰、表。五科选一作为第二场考试。简单来说,论就是说理文、论文。《六国论》此类文章便是“论”。
判则是宣判的判决书,字数在百余字上下,一共要考五道,采用骈文形式,要在百余字内说明情况,违法的地方,提出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主要考考生对国朝法制的了解。
诏与诰就是以皇帝的口吻写天家文体的诏书,这是翰林必备技能。表则是一种公文形式,戏文里的上表,就是如此,也可以称之为上疏。
第三场则是古老且一直延续至现代公务员考试都使用的“策问”了,当然公务员考试叫“申论”,不在赘言。
时至如今,虽说理论上三场考试都是等价的,但因为八股文的权重一直在上升,嘉靖后期后两场的比重大大缩水,看重头一场的时文制义尤为凸出。
目前具体落实到县试这一级别,已经宽松许多,需要在一天内考完,则只考《四书》两道八股文。
徐秀小心的拆开卷子,里面有十多页纸张,这纸质量很好,每页分了十四行,每行可以写十八个字,都用红线隔开,还有空白的草稿纸数张。
打开题纸头道大题就是论语“学而时习之”一章节。第二题是《孟子》“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施施从外来。”
徐秀微微松了一口气,还好,都是大题,他最怕的就是出一些小题,截题,这在后期小考中,司空见惯。
只因四书五经字就那么多,考了几百年,到清朝,无论哪一个大题都有标准范文,往死里背就能过的现象很严重,所以在秀才这一级别截搭题数不胜数。
明朝这样的情况不严重,但也不是没有,所以在秀才这一级别的考试,也有很多是采用小题,截搭题之类。
如这两道题,截出学而两字作为考题都是有的,如果碰上了,恭喜你,难度上升一个台阶,就算知道是学而时习之的意思,但你作文便不可以有后几个字存在,还要表明后几个字的意思,很是考验考生的能力。
这两道题问题都不大,特别是学而时习之,作为八股文体第一个的破题,最是好破了。
稍微酝酿了一下,徐秀拍拍自己的脸颊,便开始在草稿纸上作文。
破题:圣人论学,惟不息以几于成。
承题:盖时习者,不息也……
起讲:意谓:学者,所以复性也……
起二股:《诗》、《书》吾既学之矣,而非仅涉其文也……
出题:时习如此;吾知其于学;乐而玩;居而安……
中二股:人之不知如彼,不愠如此,吾知其于学也;足于中,无待于外。
中二小股:人虽不知;而己独知自得之深;而道德之归也有日。……
束二股:至于此,殆所谓以成德为行,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者,而学其自此至矣……学者诚以吾言思之,其不亦然呼?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这短短数百字的八股文,真是耗费你的心血,徐秀不由苦笑:圣贤啊圣贤,你简短的一句话,我却要为之作上一篇
多少人考的头白花白,牙齿掉的精光,连苗和草都分不清,全是为了这个功名利禄。
不去在做多想,徐秀反复审视了一下破题,八股文破题至关重要,听钱福讲到,小考很多考官往往只看一下破题,如果破题破的不好,后面也不会再去看,直接给个罢黜的结果。
也不难以想象,朝廷规定县试只允许知县大人一个人评阅,不准找本地儒学教授之类的帮助阅卷,这七百多份考卷如果一一都要从头看到尾,工作量实在不小。破题是以要好。
确认无误,没有偏题,没有写错别字,用的虽是行书,较为潦草,但这只是草稿纸,也无碍,徐秀微微有些得意,看来县试这一关,不是什么难事了。
拿起孟子题的问题纸仔细瞧了瞧,稍作酝酿,才思敏捷的徐秀按着先前的草稿格式认真的书写。
破题:齐妇丑其夫,而齐人不自丑焉。
……
到了中午,徐秀微微抖动了一下手腕,约莫有些酸疼,总算这第二题也完成了。在誊抄前,他拿出了饼子,有些发硬,也聊胜于无,有的吃就好,不见有些考生看到别人吃东西还嘴馋没的吃吗,边吃边注意周围的情况。
此类的题目很多人都可以尝试着写,并不难以理解,但写的好与坏就是个问题,也有些人因为紧张而晕倒,被衙役送了出去,徐秀继续感叹科举的无情。
□□的打了一个饱嗝之后,他小心的清理了一下桌面,接下来可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了。
这一步就叫“誊真”,徐秀很佩服有人能有那个直接在正规试卷上写的本事,那已经可以称之为天才,非一般人能够做的到。
只因这卷面的要求很是严格,只能以楷书,或台阁体写,不能涂改,不能错字、别字、通假。还要自己给自己的文章点标点,当然古代的标点就是句尾画个圈,也不另起一行。
徐秀小心翼翼的进行誊真,写完第一篇,已经有人开始交卷,此时的太阳微微有些西斜,照旧耀眼,这时候交卷,知县就会随到随阅,当场给出一些评语。
徐秀并不着急,只因钱福恶狠狠的跟他说,你不许前十名交卷,在他询问过后,得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答案,只因为前十名出去的,门口会有敲锣打鼓的送行,会一直跟到你的家里,讨要赏钱,而他不愿意或者说没这个钱去出,还美其名曰真是世风日下。
两篇文章通通誊抄完毕,小心的用先前发放的密纸将自己的名字糊住,虽然县试这点往往都不严谨,但也是个形式,需要做,不然直接罢黜,不留情。
“嗯,我看看,我看看。”李嵩拿着折扇抵住嘴角,试卷平铺在案台,一手拿着沾着朱色墨水的细笔圈阅,觉得这一句说的好的,便画个圈。
“有志于学者,习之不可不时也。好,这题明破,甚好。”李嵩说完继续看,最后点了点头,在左上角写了个中字。当场取中,尤为不宜。
笑了笑道:“多谢老师。”考官点中的,在古代就是老师一样的存在。遂如此回答。
“你还是别笑吧,怪难看的,哈哈。”李嵩拿扇子敲了敲自己脑袋打趣道。
此人便是徐辉。
见已经十好几人交卷,连徐辉也交了上去,徐秀呼了口气,拿起草稿纸和正卷走向知县。
“向父母官问好。”恭谨的递交了上去。
“噢,又是一个娃娃,我来瞧瞧。”李嵩笑起来很阳光,见到连续两个十几岁的小娃娃也不由心情大好的道。
“圣人论学,惟不息以几于成。嗯,不错不错,这是暗破呢。”李嵩画了一个圈圈,表示认可。
“觉得有点怪呢,小娃娃。”李嵩把两篇文章都看完了,画了很多圈,却没有写中,笑道。
徐秀心中一阵懊悔,肯定又是不知不觉用了一点偏的论述了,带着点后悔的意思同李嵩道:“望父母官见谅。”
见他脸上一阵吃味的表情,李嵩被逗乐了,无外乎自身也不过二十几岁心性也不是很老成,笑道:“你今年多大了?”
徐秀以为自己会倒在县试这关不由悲声道:“一十三岁。”
李嵩满眼笑意的道:“你这文章现在取中还早了;回去用心读书,县试三年两考,本县也是初来,到下一次,我取你。”
去你的,虽然徐秀也知道科举不是那么好走,但自身起步点又不是这边十几岁的娃娃,图书馆十几年的侵浸这样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强化,都无法过了县试这一关,不由耍了一下滑头故作伤心道:“望父母官怜悯,全我尽孝之心。”
明代每一位帝王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孝字,由此便知大明朝是以孝立国,什么事情在明朝扣上了孝的帽子,这问题就大了。
翻看了一下他的花名册,见是永感下,李嵩不由一阵腹疼,自己也没有罢黜他的意思,他却耍这种滑头,有意思的娃娃,道:“你对个对联,便让你过,听好了,我这上联是大器贵在晚成。”
徐秀一听便放松了下来,这很多古典小说中都有类似的对子,认真道:“长才屈于短驭。”
“你对的倒是工整,我便取了你吧。”李嵩摸了摸肚子,摇头笑道。
顺手就在他的试卷上,写了一个中字。
“你且去吧。”
“多谢老师。”
☆、第十一章 道试
过了十天,弘治十三年松江府华亭县的县试榜文发放了出来,周围密密麻麻的围着一圈人,他离着稍远,只看到了两个大轮子。
不同于之后的考试竖排从左到右的排榜方式,县试的榜单是一个圆形,第一名在正中12点方向的位置叫县试案首,然后依次写,五十名围一圈。
剩下的人数则在外围再围一个圈,这样的榜单有一个名字,叫“轮榜”意思指的就是还没经过府试的确认。
这一场总数取了一百四五十人,较常规十比一大幅上升。
徐秀瞧见榜单后,微微有点不爽自己排在了第一轮的最后一名,既五十名,也只能无奈接受,之前没有出榜还有点期盼自己能够得个案首什么的,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小说,主角是六首状元,那才叫一个威风。
他也有这样一个梦,可惜现实是残酷的,现代人发散的思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约束的住。
那日回来后默写给钱福看,钱福摇头晃脑的说,这样的文不是案首哪个有资格是案首,不由一阵窃喜,恰好顾清和徐辉也在,就给了顾清看,要知道,顾清可是弘治三年大比第四名,当的起一句时文大家。
而他的说法是,既然父母官点中了你,名次可能也不会太高。以理性的角度给他做了分析。
虽然失望,但也不至于不爽,可是轮榜的第一个,□□裸的写着徐辉两个字,这就是差距。
徐秀发狠,既然县试比不过,那就府试再来过,现在才三月,府试是在四月,还不用去什么省城,松江府的治所就在华亭,路上也不会浪费时间,仅仅是将地方从知县衙门改到专门的考棚,这样的考棚每一个地方都有,地方大了不少。
这一发狠就就是彻夜攻读,头悬梁锥刺股,眼睛都泛起了一点淡淡的黑眼圈,让陶骥哇哇乱叫很是心疼,他四书往死里背,不把自己洗脑不罢休,情况到的确好了不少,最起码提笔写文的时候会考虑考虑了。
……
府试时上海县的考生也赶赴了过来,有亲友的则投靠,无有则住客栈,甚至城外租一间农舍,两三千考生还有几千家属的涌入,可以说华亭县的治安瞬间就下降了一个层次,有的儒生依仗着人多寻衅滋事,搅合的市面不得安宁。
知府大人刘琬狠狠的责罚了一批人,才稍有好转。
同县试不同,徐秀大半夜就无奈的出了被窝,深夜即入场,只因人数太多。
人还是那些,除了陶骥作保,还有一位县学的前辈挨保,两个人保一个,考棚门口,有许许多多的奇形怪状的等身灯笼照着,人挨人,人挤人,一不留神就会散掉,全靠这样的大灯笼在前边指引。
其他检查的地方同县试区别不大,拿了座号走进,很巧又是和徐辉连号,两人对视一眼也不多说,闭目养精蓄锐。
等到人都进场开考,徐秀打开试卷,又是《论语》和《孟子》的题,论语出:“文不在兹乎。”之前有一句文王既没没写上,这是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