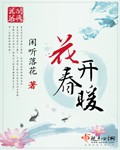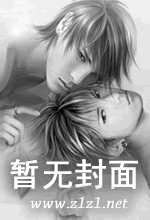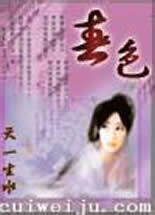М«ЖҪҙә-өЪ13ХВ
°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ы »т Ўъ ҝЙҝмЛЩЙППВ·ӯТіЈ¬°ҙјьЕМЙПөД Enter јьҝЙ»ШөҪұҫКйДҝВјТіЈ¬°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ь ҝЙ»ШөҪұҫТі¶ҘІҝЈЎ
ЎӘЎӘЎӘЎӘОҙФД¶БНкЈҝјУИлКйЗ©ТСұгПВҙОјМРшФД¶БЈЎ
ЎЎЎЎЎ°І»·БКВөДЎЈЎұРмРгНЖНСөАЎЈ
ЎЎЎЎВҪЙоНЖҝӘҙ°»§Ј¬ЦёБЛЦёНвГжЈ¬ИПХжөАЈәЎ°С§өЬЈ¬ұұөШНтАпТшЧ°Ј¬ҙшнВЙҪәУЈ¬ДгҫНГ»ҫЖРФ·ўҝсЈ¬К«РФ·ўЧчВрЈҝЎұ
ЎЎЎЎРмРгПлБЛПлІЕөАЈәЎ°ИзҙЛУРАНВҪРЦБЛЎЈЎұ
ЎЎЎЎБҪДкІ»јыЈ¬ВҪЙоРоЖрБЛөӯөӯөДәъРлЈ¬ИЛіЙКмБЛәЬ¶аЈ¬РмРгІ»өГІ»іРИПЈ¬ХвСщөДЛыёьПФ·зІЙЈ¬ҫЬҫшөДРДЛјТІҫНөӯБЛЎЈ
ЎЎЎЎВҪЙоХЈБЛХЈСЫҫҰөАЈәЎ°ИзҙЛЙхәГЈ¬ОТөИ¶аДкОҙҫЫЈ¬ҪсИХұШТӘІ»ЧнІ»РЭЎЈЎұ
ЎЎЎЎЎ°ЎӯЎӯЎұ
ЎЎЎЎФхГҙВҪЙоТІҝҙЖрАҙТІУРөгІ»М«¶ФҫўөДСщЧУЈ¬РмРгУРөгДЙГЖөДПлөҪЎЈ
ЎЎЎЎЎӯЎӯЎӯЎӯ
ЎЎЎЎДП№ъ·»Ј¬ЦчТӘКЗХРҙэҪшҫ©ёПҝјөДС§ЧУЛщҝӘЙиөДҫЖјТЈ¬Ч°КОөДЗеРВСЕЦВЈ¬ЧЯҪшАҙәуТ»Ху№ЕЗЩУаТфЈ¬әЬКЗұрЦВЈ¬ТІІ»УЙ·ЕПВРДАҙЈ¬»·ҫіІ»аРФУЈ¬ҫЫҫЫТІҫНКЗБЛЎЈ
ЎЎЎЎФЪөЗҝЖМГДЪБҪХЕіӨЧАІўРРЈ¬ВҪЙоЎўМХжчЎўРм»ФЎўРмРгЎў°ьАЁФЛәУЙПҪбК¶өДіэСоЙчНв¶ӯ«^ЎўОәРЈЎў·ҪПЧҝЖЎўЙЫНўиЁЎў№ЛУҰПйТІ¶јЗ°АҙПаҫЫЎЈ
ЎЎЎЎЎ°ҫГСцҫГСцЎЈЎұ
ЎЎЎЎФЪТ»Хуә®кС№эәуЈ¬ЦЪИЛЛгКЗјы№эБЛАсЎЈ
ЎЎЎЎ¶ӯ«^ЧшПВәуҫНІ»°І¶ЁЈ¬ОЕБЛОЕЧАЙПөДҫЖҪРөАЈәЎ°ХвҝЙКЗЙҪОчМКіцАҙөД·ЪЛ®Ј¬ГыҪРЦсТ¶ЗаЈ¬УРГыөДГыҫЖДШЎЈЎұ
ЎЎЎЎМХжчіеЛыРҰөАЈәЎ°ОДУсөЬөЬХжКЗ¶®РРөДДШЎЈТӘІ»ОТБ©ПИәИТ»ұӯЈҝЎұУГЛыДЗРЎКЦ№ҙБЛ№ҙЎЈ
ЎЎЎЎЎ°ЯАЈ¬ЙФәуРЎөЬЧФөұҫҙҫЖЎЈЎұЛөНкәуТІІ»јыБЛ¶ҜҫІ°ІЧшФЪТОЧУЙПЈ¬ОўОўҙтБЛёцІьЎЈ
ЎЎЎЎТэөГЦЪИЛТ»ХуЗіРҰЎЈ
ЎЎЎЎ№ЛУҰПйГюБЛГюЧАЙПөДЖеЧУөАЈәЎ°ФЖДПұвЈ¬әГЖеЎЈЎұ
ЎЎЎЎВҪЙоөАЈәЎ°ҫГОЕО©ПНРЦЛгС§УлЖеөАЙхУРСРҫҝЈ¬ИзҙЛТ»ҝҙЈ¬өұХжГыІ»Рйҙ«ЎЈЎұ
ЎЎЎЎ№ЛУҰПйҝНЖшөДТЎБЛТЎКЦөАЈәЎ°КўГыЦ®ПВЖдКөДСёұЈ¬ЧУФЁРЦМъ»ӯТш№іЈ¬РЎөЬІЕКЗЙсНщТСҫГЎЈЎұ
ЎЎЎЎЎ°ДДУРДДУРЈ¬Н¬ОвЦРҙујТПаұИЈ¬ІоЦ®ЙхФ¶ТУЎЈЎұ
ЎЎЎЎРмРгЧмҪЗОўОўТ»ійЈ¬әПЧЕДгГЗҫНКЗАҙҝНМЧөДЈҝ
ЎЎЎЎөАЈәЎ°О©ПНРЦөДЛгС§ЧФөұКЗАчәҰөДЈ¬ФЪПВЕе·юІ»ТСЈ¬ЧУФЁРЦөДКй·ЁРмРгТІКЗЙсНщТСҫГЈ¬¶юО»УЦәОұШҝНМЧЎЈЎұ
ЎЎЎЎ·ҪПЧҝЖДҘІдБЛПВЛ«КЦөАЈәЎ°ОЭДЪәЬЕҜәНЈ¬ҝЙФЪПВ»№КЗҫхөГАдЈ¬іхАҙұұөШХжКЗІ»П°№ЯДЕЎЈЎұ
ЎЎЎЎРмРгГ»МэЗеіюЈ¬ЛіҝЪҫНөАЈәЎ°КеПНРЦТІЛөОрРиҝНМЧЎЈЎұ
ЎЎЎЎЎ°ҝИҝИҝИЈ¬ҝЦЕВКеПНРЦІўІ»КЗХвёцТвЛјЎЈЎұАлЧŹ㶫І»Ф¶өДёЈЦЭИЛЙЫНўиЁұпРҰөАЎЈ
ЎЎЎЎЎ°ҫюҚтЎӯЎӯЎұ·ҪПЧҝЖЧчКЖҫНТӘЖюЛыЎЈ
ЎЎЎЎРмРгБ¬ГҰЕвАсөАЈәЎ°№юЈ¬РЎөЬөДІ»КЗЈ¬КеПНРЦПўЕӯЎЈЎұ
ЎЎЎЎЎ°әЗәЗЎЈЎұ
ЎЎЎЎҝҙөҪРм»ФҙөІиХөТІІ»Ньі°РҰЧФјәЈ¬РмРгТ»БіҫАҪбЈ¬ХжөДКЗМэІ»Гч°ЧЎЈ
ЎЎЎЎХвКұТ»ГыЙнІДёЯҙуөДДкЗбҫЩЧУЧЯБЛҪшАҙЈ¬Т»БіЮПЮОөД№°КЦөАЈәЎ°ұ§Зёұ§ЗёЈ¬ФЪПВАҙНнБЛЈ¬ЦоО»ПўЕӯЎЈЎұ
ЎЎЎЎЙщТфәйББЗеіәЎЈ
ЎЎЎЎРмРгҝҙПтВҪЙоОКөАЈәЎ°ХвО»КЗЈҝЎұ
ЎЎЎЎДкЗбҫЩЧУБ¬ГҰ№°КЦөАЈәЎ°ФЪПВСПбФСПО¬ЦРЈ¬ҪӯОч·ЦТЛИЛЎЈЎұ
ЎЎЎЎЎ°аЫЎӯЎӯЎұРмРгОҙФшСКПВөДТ»ҝЪІиҫНХвГҙЕзБЛіцИҘЈ¬Б¬ГҰЮПЮОөАЈәЎ°ЗәЧЕБЛЗәЧЕБЛЈ¬¶ФІ»ЧЎЎЈҫГСцСПРЦҙуГыЎЈЎұ
ЎЎЎЎУЦКЗТ»ХуҪйЙЬә®кСЎЈ
ЎЎЎЎВҪЙоөАЈәЎ°ИЛөҪЖлБЛЈ¬ҝЙТФҝӘПҜБЛЎЈЎұ
ЎЎЎЎұӯХөҪ»ҙнЈ¬Ж·ҫЖПВЖеЈ¬МёәьЛө№ЦЈ¬ВЫКұКЖЈ¬МёПИПНЦ®јдЈ¬РмРгЦ»ТӘҙюЧЕ»ъ»бҫН»бНөНөҙтБҝХвО»СПбФЈ¬ұПҫ№ГчҙъЧоЕЈөДјйіјҫНЧшФЪЧФјәөДРұ¶ФГжЈ¬ФхДЬІ»ЖрәГЖжРДЎЈ
ЎЎЎЎІ»УЙТ»ХуДЙГЖЈәХвГҙТ»ёцГјЗеДҝРгЈ¬ЙнЧЕТІКЗәЬЖУЛШөДИЛЈ¬әЬДСБӘПлөҪДЗО»ҙуИЁјйДШЎЈ
ЎЎЎЎСПбФЛЖәхІмҫхөҪЛыТ»ЦұТФАҙөДНөҝъЈ¬ГюБЛГюұЗЧУРҰөАЈәЎ°ҫюҚтРЦЈ¬ФЪПВөДБіЙПКЗУРКІГҙ¶«ОчВрЈҝЎұ
ЎЎЎЎЎ°Г»УРГ»УРЎӯЎӯОТЦ»КЗҫхөГСПРЦәГПаГІ¶шТСЎЈЎұұ»ЧҘБЛёцПЦРРөДРмРгХТІ»өҪКІГҙНРҙЗЈ¬Ц»әГИзҙЛҪІөАЎЈ
ЎЎЎЎСПбФГюБЛГюЧФјәөДБіСрЧ°іоГјҝаБіөДөАЈәЎ°ФЪПВТСҫӯіЙ»йБЛЎЈТІІўІ»әГДЗёцДШЎЈЎұ
ЎЎЎЎЎ°№ю№ю№ю№юЎұЛщУРИЛ¶јІ»ҝНЖшөДРҰБЛЈ¬КэМХжчЧојъЈ¬Рм»ФЧоөӯЎЈ
ЎЎЎЎЎ°ЕйЎұ
ЎЎЎЎРмРгДФГЕәЭәЭөДҝДФЪБЛЧАЧУЙПЈ¬Т»өг¶щ¶јІ»ПлМ§Н·Ј¬Т»өг¶јІ»ПлЎЈ
ЎЎЎЎЎӯЎӯ
ЎЎЎЎФЪұ»МХжчБ¬Рш№аБЛОеұӯҫЖЦ®әуЈ¬ұИРмРг»№РЎДЗГҙјёёцФВөД¶ӯ«^ЛІјдҫНёЯБЛЈ¬ТІ»ЦёҙБЛДЗёцЛө»°І»ҙӯЖшЈ¬Т»ҙуҙ®»°УпБ¬ГаІ»¶ПөД¶ӯОДУсБЛЎЈ
ЎЎЎЎТ»Ц»НИҫНХвГҙЗМЙПБЛЧАЧУЈ¬әмЧЕСЫҫҰөАЈәЎ°ОТГЗҙУПаёфКэ°ЩАпЈ¬ЙхЦБКэЗ§АпөДөШ·ҪПаҫЫФЪХвұЯЈ¬ХвГҙөДТвЖшПаН¶Ј¬іэБЛГчТ«РЦУЦ¶јКЗҪсҝЖУҰКФөДҫЩЧУЈ¬І»ИзҪбТ»ёцОДЙзЈ¬Па»ҘГгАшЈ¬Па»ҘјӨАшЈ¬Ҫ«АҙТІәГУРёцХХУҰЎЈЦоО»ФхГҙҝҙЎЈЎұ
ЎЎЎЎГчҙъОДИЛҪбЙзЦ®·зКўРРЈ¬УЙҙЛТ»МбІў·ЗІ»әПККЎЈ
ЎЎЎЎМХжч°СЛыДЗМхНИ°ЗАӯөҪБЛөШЙПөАЈәЎ°ХжКЗёцәГЦчТвДШЎЈЎұ
ЎЎЎЎРмРгРДЦРТ»ҫӘЈ¬ЧФјәұИСПбФРЎБЛҫЕЛкЈ¬Ц»ТӘЧўТвөгЈ¬»оөҪЛыө№МЁ¶јІ»КЗКІГҙОКМв°ЙЈ¬ХвТӘВдТ»ёцН¬өіөДГыН·НнДкЖсІ»КЗЖаБ№ЛАЈҝ
ЎЎЎЎёХПлХЕҝЪЛөөАЛөөАЈ¬ҫНМэТСҫӯУРҪшКҝ№ҰГыФЪЙнөДРм»ФөӯөӯөАЈәЎ°ЙхәГЈ¬ОТФЮН¬ЎЈЎұ
ЎЎЎЎРм»ФТІУРЛыөДҙтЛгЈ¬ЛыДЗТ»ҝЖөДИэ¶ҰјЧҝөәЈЎўЛпЗеЎўАоНўПаЈ¬¶јКЗ¶юК®јёЛкөДДкЗбИЛЈ¬ЛдЛөН¬ДкКЗ№ЩіЎТ»ёцАОҝҝөД№ШПөЈ¬ө«ЖҪКұЛыёъЛыГЗИэИЛІўІ»КЗәЬМёөДАҙЈ¬ОӘКьјӘКҝөДКұәтТІОЮУРФЬПВ¶аҙуөДИЛВцЎЈ
ЎЎЎЎДЗТ»ҝЖ»бКФЦчҝј№ЩОвҝнПИЙъПДјҫұгИҘКАБЛЈ¬¶чКҰ№ЛЗеТІГ»УРКІГҙКЖБҰЈ¬ЛөКЗ№ВјТ№СИЛ¶јКЗЗбөДЎЈ
ЎЎЎЎ¶шТӘПлФЪ№ЩіЎЦРХҫөДОИөДБҪҙуТӘЛШЈ¬Н¬ДкәНАПКҰЈ¬Рм»ФТ»ёц¶јІ»ҫЯұёЈ¬УРХвГҙТ»ёцК®ИЛөДНЕ¶УЈ¬ЛыГЗТІҪ«»бУРЧФјәөДЧщКҰәНН¬Дк№ШПөЈ¬ХвСщТ»АҙЈ¬ЖҫҪиЧЕХвІг№ШПөЈ¬¶ФЛы¶шСФұШИ»ҫНКЗУРАыЎЈ
ЎЎЎЎЛщТФІЕ»бФЮН¬ЎЈ
ЎЎЎЎ¶ӯ«^ЕДЕДЧАЧУөГТвөДөАЈәЎ°ЗЖЈ¬ОТГЗөДёшКВЦРҙуИЛ¶јН¬ТвБЛДШЈ¬ДгГЗ»№І»ҝмұнМ¬ЎЈЎұ
ЎЎЎЎРмРгјұБЛЈ¬ХвСщПВИҘХжҪбЙзБЛЈ¬СПбФТ»ө№МЁЈ¬ҝП¶ЁЙЩІ»БЛН¬өіөДГыН·Ј¬Б¬ГҰөАЈәЎ°»бІ»»бИГИЛҫхөГКЗҪбөіДШЈҝЎұ
ЎЎЎЎМХжчРұСЫөАЈәЎ°ҪбЙзЦ®·зКўРРЈ¬ФхГҙҝЙДЬКЗҪбөіЈ¬К«ЙзОДЙзөҪҙҰ¶јУРЈ¬УРКІГҙәГөЈРДөДЎЈОТТІФЮіЙЎЈЎұ
ЎЎЎЎОәРЈРҰөАЈәЎ°ХвГҙёцөГТвНьРОөДОДУсөЬөЬЈ¬өҪМбБЛёцәЬҝҝЖЧөДЦчТеЈ¬ОТФЮіЙЎЈЎұ
ЎЎЎЎ·ҪПЧҝЖөАЈәЎ°ФЮіЙЎЈЎұ
ЎЎЎЎРмРгМ§Н·өАЈәЎ°О©ПНРЦІ»ФЮіЙЈЎЎұ
ЎЎЎЎЎ°ҝИЈ¬О©ПНРЦКЗФЮіЙөДЎЈЎұ
ЎЎЎЎЙЫНўиЁЧЦҝЙ°®РЦУЦТ»ҙОідөұЖрБЛРмРгөД·ӯТлЎЈ
ЎЎЎЎСПбФітБЛітТ»Цұ¶ўЧЕЧФјәөДРмРгІ»УЙУРР©әГРҰЈ¬ФЪЛыөДЧўКУПВТ»ЧЦТ»ЙщөДөАЈәЎ°ОТТІФЮіЙЎЈЎұ
ЎЎЎЎјыЛыГЗТ»Т»ұнМ¬Ј¬¶јКЗФЮіЙЈ¬РмРгҫшНыөДУЦУГДФҙьЗГБЛЗГЧАЧУОЮДОөАЈәЎ°ФЮіЙЎЈЎұ
ЎЎЎЎҫНҙЛЈ¬У°ПмәуКАЙхЙоөДОДәІЙзЈ¬ФЪРмРг»ГПлЧЕНнДкЖаБ№өДЗйҝцПВЈ¬ұ»ұЖОЮДОөДЗйҝцПВЈ¬РыёжіЙБўЎЈ
ЎЎЎЎИҙГ»ПлөҪЧФЙнТІКЗУРҝЙДЬЧЯЙПёЯО»Ј¬өГТФЧФұЈЈ¬»тХЯАъК·ҙУҙЛҫН№ХНдБЛДШЈҝ
ЎоЎўөЪК®ЖЯХВЎЎ»бКФ
ЎЎЎЎ»бКФЈ¬ТаіЖҙәгЗЈ¬ГҝИэДкТ»ҙОЈ¬ҝӘҙә¶юФВіхҫЕҝјөЪТ»іЎЈ¬ЖдҙОК®¶юИХЈ¬К®ОеИХҝјәуБҪіЎЎЈИэіЎЧч°ХЈ¬ҫІәт°сОДЈ¬КЗБъКЗіжЈ¬ҫНҝҙХвТ»ФвЎЈ
ЎЎЎЎХвКЗЛщУР¶БКйИЛЧоЦШТӘөДҝјКФЈ¬Ц»ТӘНЁ№э»бКФіЙОӘЦРКҪҫЩИЛЈ¬ҫНТвО¶ЧЕЈ¬ХвТ»ұІЧУҫНУРБЛТ»ёцәГөДЗ°іМЎЈ
ЎЎЎЎИфКЗФЪНҘКФөДКұәті¬іЈ·ў»УІ©БЛТ»ёцёьәГөДГыҙОЈ¬ТАНРЧФЙнөДЕ¬БҰЈ¬О»ј«ИЛіјТІІўОЮІ»ҝЙЎЈ
ЎЎЎЎҝЖҫЩЈ¬ЧЭУРЗ§°гІ»КЗЈ¬ИҙОЮ·Ё·сИПЛыИ·КөКЗТ»ёцЖХНЁИЛёДұдГьФЛөДУРР§КЦ¶ОЈ¬ТІКЗФЪХвёц·зЖш»№ОҙНкИ«ЛъПЭөДКұҙъЈ¬іцҪ«ИлПаЈ¬Гыҙ№З§№ЕөДЦШТӘҪЧМЭЎЈ
ЎЎЎЎЎ°ЦХУЪЧЯөҪХвТ»ІҪБЛЎЈЎұАҙөҪ№ұФәГЕҝЪЈ¬РмРгУРР©ёРҝ®өДөАЎЈ
ЎЎЎЎЎ°С§өГОДОдТХЈ¬»хУлөЫНхјТЎЈЎұВҪЙоЕДБЛЕДЛыөДјз°тРҰөАЎЈ
ЎЎЎЎЎ°ө«Фё°ЙЎЈЎұ
ЎЎЎЎЎӯЎӯ
ЎЎЎЎ»бКФөД°ІјмЛдИ»Н¬СщСПёсЈ¬ИҙТСҫӯІ»»бФЩУРДЗР©Ў°ЦВЛрКҝЖшЎұөД·Ҫ·ЁЈ¬ЦрО»өгГыЈ¬ЙуКУЖдИЛЈ¬И»әуЙППВГюГюЛчЛчЛСЛСјсјсГұЧУ·ӯТ»·ӯҫННкЎЈ
ЎЎЎЎҪсҝЖҝјКФ№ЩКЗМ«іЈЛВЗдјжәІБЦС§КҝХЕФӘХкЈ¬Чуҙә·»ҙуС§КҝјжәІБЦКМ¶БС§КҝСоНўәН¶юО»ЦчҝјЈ¬ЛДөо¶юёуҙуС§КҝЧцЦчҝј№ЩХэөВДкјдІЕіЙОӘ¶ЁЦЖЈ¬Ц®З°ҪцҪцКЗЙЩКэЈ¬ИзҪсЦчҝј№ЩИЛСЎЈ¬ЦчТӘФтКЗјжУРәІБЦФәС§КҝөДМ«іЈЗдәНЧуУТҙә·»№ЩөЈИОЎЈ
ЎЎЎЎЗ°ХЯөДЦ°ДЬН¬АсІҝУРР©ЦШөюЈ¬Цч№ЬјАмлЈ¬әуХЯКЗХІКВё®өД№ЩЈ¬ХІКВё®јҙКЗ»КјТЧУөЬҪМөјөДЦ°ДЬ»ъ№№Ј¬ёЕСФЦ®ҫНКЗҪММ«ЧУ¶БКйөДЈ¬Н¬јМО»»КөЫөД№ШПөЧФИ»І»ЗіЎЈ
ЎЎЎЎәуАҙОҪЦ®ЗұЫЎ№ЩЈ¬ҙуГы¶Ұ¶ҰөДРмҪЧҫНКЗұ»ХІКВё®іцЙнөДёЯ№°ёш¶·БЛПВИҘЈ¬¶ш¶·ПВёЯ№°өДХЕҫУХэТІКЗіцЙнХІКВё®ЎЈ
ЎЎЎЎЛөөҪХвАпЈ¬І»УЙІеТ»¶ОМвНв»°Ј¬әуАҙҙуС§КҝөЈИОЦчҝј№ЩЈ¬ЧоДЬАнҪвөДВЯјӯҫНКЗёшДЪёуҙуС§КҝөДКЖБҰКХРЎөЬЈ¬ДЗКЗФЪДЪёуөШО»ҙу·щЙПЙэЦ®әуІЕУРөДЈ¬ҙУХвТ»өгЈ¬ТІҝЙТФө№НЖЈ¬өГіцТ»ёцХэөВТФЗ°өДДЪёуөШО»ІўІ»ёЯөДҪбВЫЎЈАъК·өДКВКөЈ¬ТІИ·КөИзҙЛЎЈ
ЎЎЎЎәлЦОК®°ЛДкТТіуҝЖУҰКФөДС§ЧУЈ¬і¬№эБЛИэЗ§°Л°ЩИЛЎЈҫНЛгКЗХвГҙ¶аөДИЛЈ¬№ұФәДЪТІКЗІ»ПФУөј·Ј¬ГЬГЬВйВйөДТ»јдјдРЎёфјдУМИз°С№«№ІІЮЛщёЗҪшБЛДсіІМеУэіЎЎЈ
ЎЎЎЎФЪёъЛжёәФрЧФјәТ»ЗР°ІЕЕөДҫьКҝҪшЧФјәҝј·ҝөДКұәтЈ¬РмРгПлөҪөДФтКЗЗ®ёЈөұіхөД»°УпЎЈ
ЎЎЎЎЎ°ЛщОҪКұОДЈ¬ұШИ»ТӘҙ§ДҰөұПВөД·зЖшЈ¬ИфКЗІ»ЦӘөАҙ§ДҰЈ¬ҫНКЗКҘИЛАҙҝј¶јКЗІ»ЦРөДЎЈЎұ
ЎЎЎЎЎ°ПИЙъөұКұөД·зЖшҪІҫҝІГ¶ФХыЖлЈ¬»щөчФІКмЈ¬ИзҪсҝЙДЬІ»ҙуПа·ыЈ¬ЛщТФЈ¬ИфөҪҫ©КҰЈ¬ұШТӘУлКҝЧУ¶аНщАҙЈ¬¶аҪ»БчЎЈЎұ
ЎЎЎЎХвТ»өгРмРгЧцөДәЬід·ЦЈ¬ЧФҙУОДәІЙзіЙБўЦ®әуЈ¬јёәхГҝМм¶јКЗҫЫФЪТ»ЖрЗРҙиЦЖТХЈ¬І»өГІ»ЛөЈ¬ХвТ»ИәДкЗбИЛФЪ°Л№ЙХвТ»өА¶јКЗәЬАчәҰөДЈ¬ТІ¶јІЕЛјГфҪЭЈ¬¶ФөұПВөДБчРРОД·зЙхКЗБЛҪвЎЈ
ЎЎЎЎИфЛөҙ§ДҰОД·зөД·ҙГжАэЧУЈ¬ұгКЗЧЈФКГчПИЙъБЛЈ¬ХвО»ТҜҫНКЗө№ФЪБЛІ»¶®өГҙ§ДҰКұОДөДХвТ»өАҝІЙПЎЈЖЯКФЖЯҙмЛдЛөКЗЛөәуКА°¬ДПУўПИЙъөДЈ¬УГөҪН¬СщҝјБЛЖЯҙОөДЧЈЦҰЙҪЙнЙПЈ¬ТІІўОЮІ»ҝЙЎЈ
ЎЎЎЎФЪХвР©ИЛАпГжЈ¬ЧоН»іцөДҝЙДЬҫНКЗ¶ӯ«^Ј¬ЛыХжҝЙОҪКЗМмІЕЈ¬ОДЙзДЪЛыКЗЧоРЎөДТ»ёцЈ¬ЛщЧчөДКұОДФЪРмРгҝҙАҙёД¶јКЗёДІ»БЛТ»ёцЧЦЈ¬ОД·з»ъұдЈ¬ҙЗФе»ӘАцЈ¬»тРнЈ¬ЛыөДХвТ»ёцОД·зөҪәЬәНөұПВөД·зЖшЎЈ
ЎЎЎЎРмРгПлөАЈәХЕФӘХ깫өДОДХВ¶аОӘ№ЕТвЈ¬№ЕЧҫЦ®ПВҙуЖш°хнзЈ¬ҝЙОҪҙуЗЙІ»№ӨөДҫіҪзЈ¬¶ӯ«^ИфЕцөҪЛыөДКЦАпЦ»ЕВТІОЈПХЈ¬¶шСоНўәН№«ЙЩУРЙсНҜГыЈ¬ҙЛИЛөДОД·зІЕҙКОДФеҫгКЗҙујТЈ¬Из№ыХвСщАҙҝҙЈ¬БҪО»Цчҝј№ЩөД·зёсХэәГКЗТ»ёц¶ФБўГжЈ¬КЦПВЕдәПөДК®°Л·ҝ·ҝ№ЩҝП¶ЁТІКЗёщҫЭБҪО»Цчҝј№ЩРҙөДіМОДЧчОӘЖАЕРұкЧјЎЈФхГҙСЎЗРИлөгЈ¬ө№КЗёцОКМвЎЈ
ЎЎЎЎ»бКФөДҝјМвКЗіхЖЯҫНұ»ЛшҪш№ұФәІ»өГНвіцТ»ІҪөДБҪО»ҝј№ЩФЪҝјКФөДЗ°Т»Мм·ӯКйЛщДв¶ЁЎЈИ»әуЧч·¶ОДЈ¬УГҪсИХөД»°АҙҪІЈ¬ҫНКЗФДҫнөД·ҝ№Щ°ҙХХЦчҝј№ЩөД·¶ОДЧчОӘІОҝјҙр°ёЈ¬ҪшРРЖАФДЎЈ
ЎЎЎЎХв·¶ОДЧФИ»ТІҫН»біКПЦіцҝј№ЩГЗөД°®әГЈ¬РРОДөД·зёсЈ¬ұнҙпіцЛыГЗИЎКҝөДұкЧјЎЈ
ЎЎЎЎө«ПЦФЪТ»ЗР¶јКЗОҙЦӘЈ¬РмРгУЦИзәОДЬ№»ЦӘөАЈ¬НтТ»ЧФјәСЎФсБЛТ»ёц·зёсЈ¬¶шЗЎәГВдИлБнТ»О»ОД·з¶ФБўөДҝј№ЩКЦАпФміЙөДәу№ыДШЎЈІ»УЙҝаЛјБјҫГЎЈ
ЎЎЎЎ¶ЛЧшФЪПБРЎөДҝј·ҝАпЈ¬РмРгОўОўөДЙмБЛТ»ПВНИЈ¬І»УЙМЯөҪБЛНвГжөДҫьКҝЎЈ
ЎЎЎЎҫьКҝСПЛаөАЈәЎ°ҫЩИЛАПТҜУРәО·ФёАЎЈЎұ
ЎЎЎЎРмРгБ¬ГҰөАЈәЎ°І»ФшІ»ФшЎЈЎұ
ЎЎЎЎЦ»ТтҙуГчЦШКУЦРБЛҫЩөДОДИЛЈ¬»бКФөДКұәтТ»ЗР»Ё·С¶јКЗіҜНўҝӘЦ§Ј¬өұКұДПҫ©іЗ·ўөҪРмРгКЦАпөДЈ¬іэБЛЧјҝјЦӨНв»№УРТ»ҙьЧУЕМІшЈ¬РмРгІўГ»УР»ЁХвұКЗ®УГФЪЎ°№«іөЎұЙПЈ¬¶шКЗСЎФсБЛГв·СөДЙМјТФЛҙ¬ЎЈ
ЎЎЎЎЧЎЛЮөД·СУГЈ¬ТІКЗТ»ёЕГвИҘЎЈөұИ»Ј¬ДкЗбКЗУРУЕКЖЈ¬ИфКЗДЗДкАПөДҫЩЧУЈ¬ХвР©өкјТ»щұҫЦ»»бГв·СМṩҝјКФЗ°әуТ»¶ОКұјдөДЧЎЛЮЈ¬Ц®әуҫНТӘ»ЁЗ®БЛЎЈ
ЎЎЎЎЛщОҪ№«іөЈ¬јҙКЗіҜНўөДждХҫ»т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