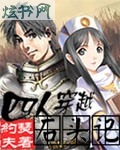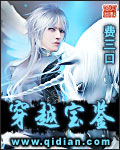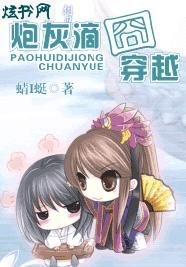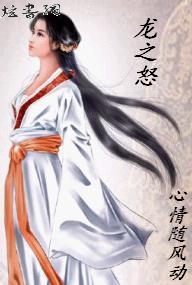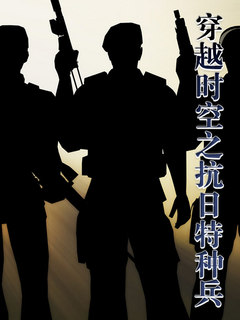穿越之绝色赌妃-晚歌清雅_完-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在烽火战乱中往往迅速增殖,诸将军间也常常形成上下统属关系。汉代还把“将军”用为优崇之衔,加给并不领兵的方士、文官甚至宦官,这时的“将军”显已脱离军职而成衔号了。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繁衍,并在位阶化的道路上骤然加速。军队编制中另有牙门将、骑督、五百人督或队主、幢主、军主等等军职,各级将校所拥有的军号,便成了他们的品位标志。由于地方行政制度日趋军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军号作为位阶,“随其资望轻重而加以征、镇、安、平之号”,并与东、西、南、北等方位字样相配,例如征西将军、镇南将军之类。上承汉代的将军辅政传统,中央官僚加军号的范围也在扩大蔓延。
由此,昔日寥寥可数而班位高贵的“将军”之官,就逐渐演变成了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了,军号的变换意味着位阶的升降。晋宋间的军号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类军号为一阶的原则,构成了有异于官阶和禄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又使军阶列于官品之外,以125号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军号的授予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如学者所称:“梁陈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52'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53'。岳珂“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的看法,实际是上承唐人旧说'54'。魏晋南北朝时,军号最先形成整齐清晰的散阶序列,并成了唐代武散阶的先声。而文散官的“品位”意义尽管也很浓厚,但其散阶化却仍不充分,零乱而不系统,落在了军号后边。直到北魏、北周之际,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魏末战乱时的军号滥授中,军号往往是和文散官成双成对地“双授”的,授军号的同时也授一个文散官,例如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55',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56'。随后这“双授”现象便引发了一个重要变动。西魏模仿周制,改九品官品为“九命”等级;“九命”所列,除大将军到武牙将军的军阶之外,还有一个由开府仪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构成的序列,与军阶赫然两立而双峰并峙。军号和文散官不仅在品阶上一一对应,而且仍像魏末那样成双加授,例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双授,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双授,征南将军与右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中军将军与左金紫光禄大夫双授,如此等等。
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序列,至少包含着两个重要进步。第一个是军阶与官阶的一致化。此前各朝的军阶与官品是不对应的,某些品级上军号阙如,另一些品级上又分布着十数个军号。而西魏的军号则均匀分布在官品各阶之上,每“命”两个军号,它们还构成了上下阶关系。军阶与官阶不再参差龃龉了。
第二个进步,便是文散官也迈入了文散阶的境界,并形成为序列。前述岳珂认为汉代诸大夫只是散官而非阶官,其后又云:
梁制,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溯而考之魏、晋、宋、齐、元魏,下而考之陈、北齐、后周、隋,亦莫不有之,参见于九品十八班之间。元魏初又尝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应作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于其中以补之。盖皆以储才待须,而亦与诸职事官均分其劳佚也。
依岳珂所论,南北朝“莫不有之”的诸大夫只用于“以养老疾”、“储才待须”,散官的性质依然故我。不过有一个进化岳珂却没看到:曾在阶官化道路上滞后不少的诸大夫和东西省散官,在西魏北周曾发生过一次质变的飞跃,由此演化为首尾完整的位阶序列了;其时军号与散官的两列分立,显已构成唐代文武散阶体制的先声。
文散官的阶官化在魏末骤然加速,与魏末以来的名号滥授、尤其是“双授”,实有密切关系。“双授”令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先已成为散阶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于军号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通过“双授”时的一一对应关系,军号便把零落散乱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质言之,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的“双授”,对文散官的散阶化和序列化,曾构成了强劲的“拉动”因素。
然而魏末的名号滥授毕竟是一种弊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又混淆了文武职类。为此,东魏北齐政权选择了与西魏不同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抑制名号滥授及文武“双授”,史称“始革其弊”。不过对“正规化”、对“文治”的这种寻求,却使诸多散官回复了原有性质,阻碍了其阶官化进程。岳珂说南北朝散官“盖皆以储才待须”,这个论断不足以论西魏,倒还合于北齐(及南朝)的实情,在那里诸大夫仍是优崇元老、安置冗散的散官而已,而非阶官。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砰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
隋廷面对北周、北齐和梁陈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个百川归海、承上启下的当口,散阶制进程一度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岳珂所述过于琐细,兹不赘引了。相关事件大略包括:隋文帝用上柱国到都督的11等“散实官”,与翊军等43号军号共同构成本阶,开皇六年(586年)又创设“八郎八尉”;隋炀帝以九大夫和“八尉”构成本阶,后来又创设谒者台九郎;唐高祖起事之初把这些名号全都利用起来,以酬奖将吏。这等于是一轮官阶大实验,各种位阶优劣各现,便推动了随后的进步。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便着手清理,初步规划出文散官、散号将军和勋官三个序列。文散官由开府仪同三司、诸大夫、诸散骑及16种郎官构成,军号包括辅国到游击共12号;勋官方面则形成柱国、大将军、都尉、骑尉的组合。
最终,散阶制的进化来到了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当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令,以光禄大夫等11个大夫加16个郎官构成文散阶,以骠骑大将军等13号将军加16个校尉、副尉构成武散阶,以柱国、护军、都尉、骑尉等构成勋官。岳珂谓:
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于一,至唐则析而为二。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禄、中散之养疾,儒林、文林之待问,一归之于文散;散号将军参取杂置,益以校尉,一归之于武散;柱国等号,本以酬劳;武骑诸称,并同郎位,一归之于勋官。则散阶也,勋官也,唐虽因隋,而所用未尝因隋,有职者改为虚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谓前世合于一者,而唐则析为二。
隋文帝的散实官加军号,隋炀帝的九大夫加八尉,都是既以进阶、又以酬劳的单一序列。而到唐代,首先散阶与勋官“析而为二”了,其次散阶中的文阶、武阶也“析而为二”了。到这时候,唐代散阶制就算基本定型了。
作品相关 资料…官阶制度研究2
四、动因与意义的进一步分析
汉唐间禄秩等级到文武散阶的发展,以上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概貌。读者能感到这个叙述有其特别的取舍,某些事实被置而不论,某些事实只是约略言及,某些事实则得到分外的关注。其原因则在于我们采取了“品位…职位”视角,这就是叙述时的取舍原则。而且,上一节采取了尽量简洁一些的笔调,而把进一步的分析留给了本节,这样层次可以清楚一些。
本书的目的,是探讨不同的分等类型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论证了周代官员等级制是一种“品位分等”的制度,卿…大夫…士的爵级及“命数”等等构成的等差,乃是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身份等级,这是其时贵族政治的内在部分。这样,在论述“汉代禄秩等级之从属于职位”一点时,对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肇始于“职位分等”意味的禄秩,“品位分等”性质的散阶制反在其后,就不致心存疑窦了。因为重“品位”的爵禄之制已先期演生,这与学者如下论述并无二致:较早出现的官员等级制多属“品位分类”。周代的封建制、宗法制和贵族制,决定了当时的官员等级制必然是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品位分等”。这时的贵族官员阶层拥有重大的自主性,君主对其权势利益的予取予夺能力,较之后世是相当有限的。
秦汉的禄秩等级一度显现出“等级从属于职位”的鲜明特点,这确实非常发人深思。我们紧紧抓住“从稍食到月俸”这一线索,揭示了秦汉禄秩作为“吏禄”的来源与性质。也就是说,禄秩等级制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稍食”这样的东西;而昔日的“稍食”是对胥吏阶层的酬报,因而“吏禄”的扩张也就是文吏群体的扩张。战国的专制官僚制化,一度造成了“天地一大变局”。商鞅、韩非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也就是“以吏治国”,“吏者平法者也”。学者谓秦帝国“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从而大异于“后世繁文缛礼之政”。秦以“刀笔吏”治天下,这种“文吏政治”与后世“士大夫政治”确实大异其趣。“士大夫”阶级已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就其与“绅士”阶层的关联而言)的官僚群体,已拥有相对于专制皇权的相当自主性。
汉承秦制,依然视官为“吏”。其时自佐史至三公皆可称“吏”,我们觉得这大有深意。汉儒曾痛心疾首于“王侯三公之贵”而被朝廷“如遇犬马”、“如遇官徒”,正反映贵族的坐享天禄、安富尊荣已成明日黄花,专制君主以“吏”的形象为臣僚定性、定位,他们只能在专制权力之下俯首帖耳,听凭其役使、迁黜和宰割。对官吏的权益、地位和荣耀,统治者经常漫不经心。职此之由,此期官吏的酬报和等级,便透露出了更多从属于职位的色调;此期的官僚,便显示出了更浓厚的“服务取向”。如艾森斯塔得所论,这种取向往往对应着拥有“铁腕”的专制皇权'57',对应着他对官吏的无情支配,官僚由此变成卓有效能的行政工具,而且未能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建立起特殊的联系。秦汉的文法吏确实很近于这种情况,他们并未显示出特定的社会来源,与后世士大夫儒生和绅士阶层的情况,明显不同。
不过帝国的官僚们总有一种“自利取向”及寻求“贵族化”的本能倾向。随时光推移,汉代官僚逐渐成为支配阶级,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基,进而形成了官僚、地主与儒士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这时官僚们必然提出更多的权益要求,希望在规划等级制时给官僚个人以更多保障。为换取官僚的效忠,汉廷也不断依禄秩等级向官僚授予特权。同时,“品位分等”确实有其灵活的地方,它在处理能力、功绩和年资的矛盾时不乏独到之处。“增秩”、“贬秩”等做法日益普遍,事实上便蕴含了一种寻求“品位”的苗头。无论从哪方面看,汉代的等级体制中确已蕴含着趋于“品位分等”的内在动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