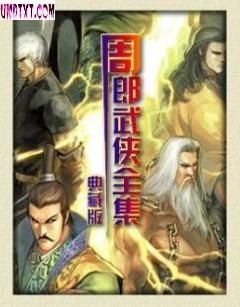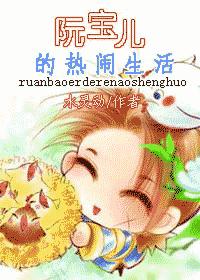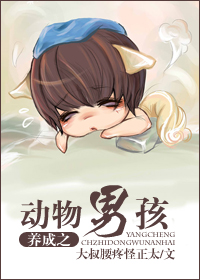饥饿的女儿-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住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架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当时,幸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的结合。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母亲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这四年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撤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象一只只温柔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烁。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么好听。
大姐嘲讽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几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个倔犟劲,倒真是象我。我生父,那个混帐男人,”大姐说了下去,“那混帐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就带了摩登女人回家。母亲独自垂泪,他看见母亲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子的女人,还有脸!我早晚得娶个校”母亲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县。家乡呆不住,按照家乡祠堂规距,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沉潭。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那男人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找,没有下落。
5
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她洗衣服动作麻利,专心致意。洗衣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笑骂不断,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己。她站起身,虽然背上有个婴儿,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
她的脸转过来,头抬了起来。他入神地看着,不转眼。他以为她在朝他看,但他错了,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马上就背过身,蹲在地上洗衣。早春二月,江水异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袖口挽得极高,头发梳了个髻,不知是怎么梳的,竟没有一绺头发垂挂下来,耳朵,脖胫和手腕没一件饰物,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如果不是背上那个不哭不闹的婴儿,带来了一点真实感,他真以为这个女人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世界而来。
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夫,小贩,妓女,逃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不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是船员追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
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哪个码头没个相好。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个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点拔他: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跟每个见到她的男人一样。这是城里一个袍哥头子的老婆,从家里跑出来的。离远点,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
1947年初春,对父亲一生来讲,是个特殊的分界线。他本对机械和器材有着天生的兴趣,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加上好学多问,没多久就学会了驾驶。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总晃荡在眼前,忘也忘不了。当她又象第一次朝他这个方向站起来,为了舒动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时,他看见了她的全部:善良,孤零,浑身上下的倔强劲,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辞,头也不回一个。
“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用不着洗嘛。”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不好意思了,脸红红地楞在门边。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一个木凳,让他在门口坐。
6
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我母亲,就断定她已远走它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艳丽的舞女在作鬼,她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浓妆的女人,母亲没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取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袍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子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不象其他唾涎母亲的男人,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二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漫。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的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给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
7
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么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字的瓜葛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么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脸上,想象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模样?他不象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担,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罗、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妈抱你出走,否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我想煞煞大姐的傲气。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火蔓延着,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贫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大人寻找孩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
火熄之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的人,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体,架着柴泼着油烧,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城市。
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认自己的亲人。小孩烧死最多,身体缩成一小块炭。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脸上黑糊糊的一条条,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
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毙掉了。是否真如街上传言,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渗了汽油,使火越燃越旺?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以增添老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
谁去弄清楚?这是个兵荒马乱,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
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月2日,它熄灭之后二个月,即1949年11月下旬,这座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长江上船员大都弃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打仗时,船最惹祸。
父亲舍不得船,哪怕是老板的船。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船。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长江,从第一声枪炮响起,父亲就用他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大拐“之”字行进,躲避船外两岸飞来的炮弹。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血溅到玻璃上。士兵惨叫着,有的是跳入江,有的跌趴在到船舷后。父亲的棉被上,血在一滩一滩漫开,船上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但是父亲却奇迹般冲到了目的地。
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算是租船的钱。然后,用手枪指着父亲说:“我们要沉船!”他跳到岸上,给士兵下任务。
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他当没听见一样,便将船掉头往回开。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炮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