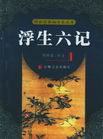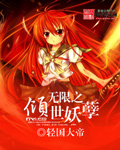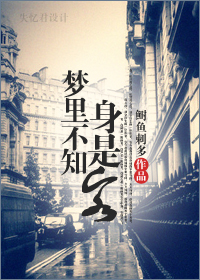梦里浮生之倾国作者:梦里浮生-第1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臣、当代名将了,决不至于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既非乱逞意气,那么在危城之中,战乱之际,想要揭起“清君侧”大旗,其意实不可测!就算他无异心,又怎么保证掌握着京营兵权的其他刘氏子弟没有非分想法?
室外冰天雪地,阁内众文官却不禁都在悄悄擦着冷汗。林凤致左右权衡,摇头道:“因此召叛党入京……只怕更加不妥。”叶德明道:“逆臣俞汝成已死,孙万年反心不重,先赦其罪,或可招抚;殷庶人……咳,袁杰实是将才可用,又与刘太师有前嫌,未必不能用以抗衡,事急从权,那也说不得了。”林凤致道:“驱狼进虎,并非善策,列位大人三思。”
他的意思分明不怎么同意内阁意见,杜燮于是毫不客气的挡了回去:“太傅公说得自是药石之言,然此等情势,还计较什么善策不善策?当年我等坚持京营不可全落刘氏之手,结果仍是无力制衡,诸公却又如何不提善策?这几年西南镇抚,北防加紧,朝鲜用兵,消耗京营兵力无数,兵部又有什么善策?”
兵部尚书章守成也在座,听了指摘不免愠怒,于是也反唇相讥:“兵权兵力之事,我兵部自是难辞其咎,然而这回南京擅自矫令迁都,意图裂我国朝,也未必不是户部的责任罢!若非这几年加捐加派,留都以下诸省怨声载道,怎会有背离京师之心?原本最是良驯的东南财赋之地,近年闻北京而色变嘲议,演成如今局面,又怪得谁!”
杜燮正兼任户部尚书,一听大怒:“东南加派捐税,说起来还不是朝廷连年用兵之过?从早年发太仓库银去重修昆明城,便是由于那一仗毁了昆明,所谓大胜却是摧残之极!……”
眼看阁内又是一场争吵,林凤致只好起身来做拦停,道:“永建朝的旧事,何苦再拿到眼下来分证?下官之见,南京矫令迁都之事,如今只是风声,尚未见着真正圣旨,真伪尚自可疑,就算是实,也必非圣意自专,朝廷决无抛弃北京之理——然而为此就召殷庶人入京,恐有后祸,莫怪下官直言冒犯列位。”
林凤致直言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暗暗苦笑着的,因为听杜燮提起昆明的事,就想到昆明之毁,全是殷螭干的好事——当然也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辛酸悲愤绝望,却又夹杂着一丝爱恋一丝愉悦的往事,悄然回来的时候,却已全无着落之处。林凤致甚至要咬牙坚决反对给殷螭以任何实益,将他的一切机会扼杀在萌芽状态,自己大约是这里最希望殷螭平安的人,却变成力排众论最敌视殷螭的人,所以人生真是荒谬。
林凤致无法直言出来的是,眼下这等情势,决非巧合,而是算计!殷螭那么有恃无恐的慢慢和谈,乐于纠缠细枝末节,并不是他愚蠢到看不出朝廷拖延的用心,而是他业已料到,朝廷无法拖延下去,必然会出现急骤转机,不得不答应他的条件而联手合作——也就是说,如今南京朝廷矫令迁都意图分裂国朝的事态,乃是他预先知道的。
因为俞汝成虽死,生前埋伏下的重棋却还留在南京,自行转运着局面,甚至会因为俞汝成之死,变得愈发不可控制,无法阻碍。
在北京受到重围的情况下宣布国朝迁都南京,北京这面的反应定是愤怒已极,同时又危险之极——倘若迁都的诏书正式颁出,北京朝廷却又无法弃城渡江而下,那么国朝实质上就成为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从而会使各路勤王军裹足不前,观望难决,也会使意欲争夺权位的野心家们,获得乱世中角逐的大舞台。
俞汝成出亡之后,一直投奔化外,让人只觉得他专为外族效力,图谋打将回来,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布局,仍在境内,这一场大计划悄然无声,却委实可以称得上宏伟之极——不幸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一次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俞汝成临终的时候喃喃的说道:“这一次又是功败垂成。”这句话里,只怕自恨之意远远大于自嘲——不仅仅是功败垂成,而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苦心布局,留下白白与情敌仇人受用。俞汝成一生精于图谋,擅长慢慢培植力量,可谓是个耕耘派,不幸遇上殷螭这个天生的混水摸鱼党,于是俞汝成辛勤培植出的结果,却让殷螭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摘桃派。
所以殷螭的命相,实在太好!
林凤致走出文渊阁的时候,外面白雪反射阳光耀眼,一时竟有头晕目眩之感,官靴踏在路面上,雪虽扫净,却仍有极薄的凝冰在靴底轻微破裂,林凤致竟想起许久之前的往事——那是自己决意倾覆反正,主动委身殷螭以便下药绝他后嗣的时候,头一回自愿和他上床,便是在文渊阁中,事后走出阁来,外面也是雪后一片清冷的寒。那一刻自己心中其实充满厌恨羞辱,却有仇恨如火意志如钢,支持着不堪的身躯坚定前进;而此刻呢?俞汝成业已死去,同殷螭也决裂到覆水难收的地步,面临着的,只是一个危险又混乱的大局,心力交瘁寻找平衡的支点,却又无权一力掌控。
甚至找不到力量支撑自己走下去,无论是爱是恨,都如烟云过眼,居然连痕迹也不剩,于是连身体里的气力,也似乎都被抽空了。
然而他还是与同僚们扯着客套话一路出了宫门,坐入官轿之后,轿夫便殷勤问道:“大人,可是回府?”林凤致想了想,笑道:“我孤身回京,家里连个人都没有,回去做甚!先送我去官驿胡乱住两日罢,这等时候也讲不得舒适。”
一品官员来住官驿,的确是件罕见事,所以驿舍上下也大忙了一阵,林凤致别说没带行李与仆人,就连银钱也不曾携带,幸好太后关心臣子,特意派了内监来服侍太傅大人,又赐了些金银物事。林凤致谢恩领了赏赐,却退还了内监,吩咐驿舍先拨人临时替自己跑腿服役。住下一两日,京中官员们便流水价来拜会致贺请宴,林凤致也只得一一还礼。
忙着应酬的时候,便听说城外礼部尚书接手与叛党谈判,几日来颇为顺利,孙万年首先答应了被收编,爵封武显将军,却不肯进入京城,自领手下将领去驻西南面兴州中屯卫,因此也没来与林凤致相见。林凤致寻思,孙万年本是弃武从文,如今却又得了武爵,宁不知是喜是悲?而他的胡妾与二子尚自留在建州,又不知能否接回中原来?
殷螭的封爵,却又多费了一点口舌,终于双方各让一步,殷螭不再强朝廷之难非得做太上皇——这原是漫天要价,自居奇货,他也知道绝对不成的——朝廷也不辱降他为郡王,将“北靖王”之封号去掉了“北”字,改封为“靖王”,同时赐其改名殷诚,以见其诚心为国效忠之意。袁百胜获封武功将军,与孙万年一样是二品武爵,仍然驻守营州卫,不随靖王入城,这一面是刘氏不愿意接纳其并入京营,一面也是含有对朝廷的戒备之意,万一朝廷言而无信,想要暗害其主,便不得不考虑在外的这支强兵。
于是朝廷择吉日大开城门,请靖王殷诚入宫领取封爵。殷螭带了五千精兵,威风凛凛驱马入城的时候,朝中三公三孤以下各重臣,以太师刘秉忠、太傅林凤致二人为首,领头迎接出来的时候,冤家相会,不免各自眼红,却又均笑得一派春风蔼蔼,貌似全无芥蒂。
面上是笑,心里藏刀,又如何能真无芥蒂?至少殷螭的芥蒂,进京头一日便对林凤致狠狠抱怨了出来:“好端端的,给我赐什么名字叫殷诚?以为改了名,大家就不知道我是谁了不成?你们也真掩耳盗铃!”
他是领毕封爵出了宫,便径直打听了林凤致下榻的官舍前来拜会,林凤致还在宫里与内阁大臣们又商议了一回事体,回来比他晚,居然让他屈尊等了小半晌,只好一入门便告罪不已。殷螭抱怨过后,林凤致当然无话可说,又道了诸如:“朝廷自有主张,下官懵懂未闻,王爷见罪。”之类的场面话,说得冷淡又敷衍。殷螭不觉有些伤感,过了一阵又笑了:“林大人真是会装佯——却不道到了今日,你又称我王爷,我又称你大人,我们之间,居然回到原来了!”
原来命运兜兜转转,却是有一日又回到原点,你仿佛仍是旧日顽劣王爷,我依稀还如昔年清贵侍臣,隔了这些年的风波恩怨,竟似全然抹平,从这头一望而到那头。
殷螭牢骚完毕就被林凤致客气的端茶送客出去,他的王府已毁弃,又戒备着京中势力暗算,只好先跟手下精兵在南城宿营。林凤致则在命人收拾自己的宅第,准备过几日便搬将回去,免得驿舍之中难以清净,更难以回绝这厚颜家伙的骚扰。何况京中一日比一日更是寒冷,驿舍虽供火炭,到底气息粗恶熏人难受,林凤致不讲究舒适豪奢,却喜欢洁净清爽,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宅第住着自在。
从冬月直奔腊月的时候,关外战事愈紧,战报一份份送将进来,铁儿努分兵四路,已直抵长城之外。这一回蛮族兵势比往年都强大,不数日便闻宣府告急,大同告急,阳和口血战,密云关示警,战报求告雪片般送入朝廷的时候,记录战况的塘报也一份份在京城中流传出来,市民中开始笼罩着惊慌不安的气氛,京郊四野的百姓也纷纷投亲靠友,南下的南下,入京的入京,只怕又象上两回一样,被蛮族在四郊烧杀抢掠。京城中驻军云集,难民也云集,于是九城提督不得不加紧巡查,维护平安。
就在这惊恐氛围愈酿愈重的时候,南京方又送来了一个严重打击——那份北京朝廷接到的密报,说天子已有下诏宣布迁都之举,大家都只希望乃是南京的迁都派放出的不实风声,小皇帝万万不能真被他们鼓惑甚或挟制,然而正式的诏书,却由不得大家不希望就不传抄送来!
南京朝廷送来迁都诏书的同时,一字不漏抄下诏书的邸报也迅速在京中散布开来。市民本来还被朝廷瞒在鼓里,这一来瞒将不住,登时哗然一片,满城大乱,连日奔涌向金水桥声讨呼吁,甚至激烈的举人秀才太学生们,冲入搬出景阳钟敲得震天价响,请朝廷给出说法,岂有这般不明不白,不加知会京城百万军民,就擅自迁了国都的道理?祖制何在,国法何在,圣驾何在,大臣何在!
这场请愿无法消弭,连执金吾也拿群情汹涌的市民没有办法,直到刘秉忠亲颁手令,命京中骁骑营出动长枪队去驱赶,才算没让市民们在愤怒之下冲破宫门杀进大内。但长枪队驱逐的时候,免不得流血伤人,京中一向娇惯的市民哪里吃得了这等亏,愈发鼓噪不停,向长枪队投掷石头瓦片,骁骑营又急调铁盾队去遮护,市民们便换作砸石灰包,结果一场混乱之下,骁骑营多人眼睛受伤,市民却死伤数十人,金水桥前满地流血。这一年是乙亥年,国史实录上便称作“清和乙亥迁都之变”。
国朝前代并非没有出过杀戮百姓的暴君,但自从重福帝穆宗的祖父安裕帝孝宗以来,就一直以爱护子民、护持言论的祖制为要,国民们几代以来享惯自由风气,尤其以南北两京被纵放最甚,一下子遭此铁血手段,不免怨愤之气冲天。武斗不得,于是文谏,从缙绅到商贾走卒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