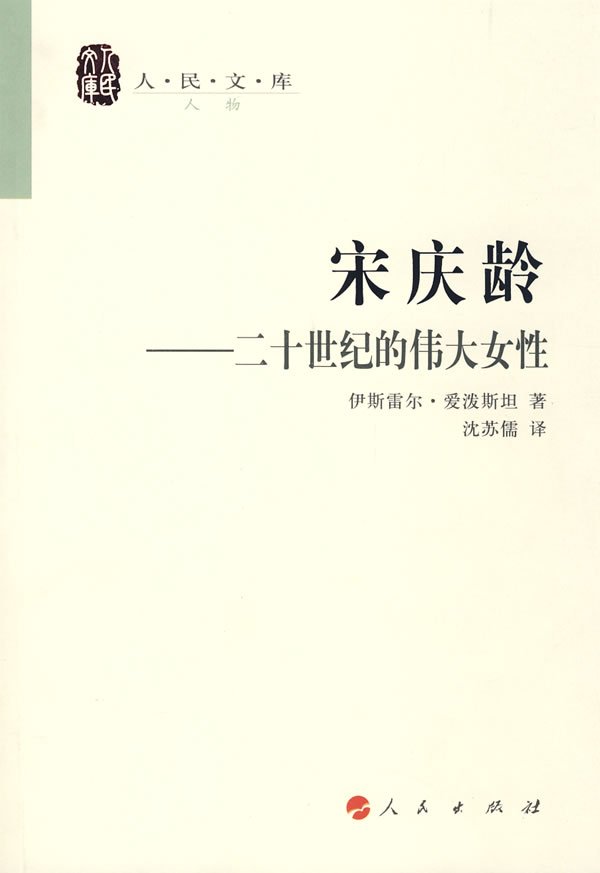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连忙到了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映芝,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映芝和他分辩,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他见映芝不说,便天天和映芝闹。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晚上到这里来捱骂,如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结算。映芝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映芝还磕了多少头,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才把他劝肯了,和他雇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
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栈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杏农方才别去。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
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净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饼摊旁边,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
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道:“怎么去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我道:“正是。”店家道:“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客人初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这劣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
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寓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道:“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道:“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我道:“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老者道:“卫里吗(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以天津本卫也),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卫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厘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捐一趟,自然把酒捐坏了。”我道:“捐贵了还可以说得,怎么会捐坏了呢?”老者道:“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那厘捐越是抽得利害,那水越是搀得利害,你说酒怎么不坏!”我问道:“那抽捐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老者道:“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我道:“这又有甚么分别?”老者道:“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顽法。”正是:一任你刻舟求剑,怎当我掩耳盗铃。
未知那老者还说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我听那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里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代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
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五十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道:“我这回进京,满意要见焦侍郎,代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馆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只住了两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
我道:“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理儒?”宗生道:“正是他。”我道:“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甚么不自在的事呢?”宗生道:“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甚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得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材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拱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二十五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甚么要紧,还把他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的一发没有人敢问名的了。去年六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三十岁。二十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宦囊里面多了三千金,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坊。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捱到六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便打算央媒说合。既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得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等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是两榜同年;却是个旗人,名叫惠覃,号叫雪舫;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雪舫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道:‘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得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便说道:‘那么这件事,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
“雪舫得了这个差使,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六岁大的男孩子,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雪舫到了,总是逗他顽笑,考他认字。偶然谈起说道:‘怪可怜的一个小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辅成听了笑道:‘伤心还没有得过,那里便谈到这一层;况且我是立志鳏居以终的了。’雪舫道:‘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久后这中馈乏人,总不是事。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赶伤心追悼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久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雪舫又道:‘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辅成道:‘可不是吗。我这立定鳏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着。’雪舫道:‘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辅成兄,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赁宅子,要省得多呢。’辅成道:‘我何尝不想。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内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样了。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课子消遣,因此未果。’雪舫道:‘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到底省点浇裹。’辅成道‘我何尝不想。只因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辫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舫道:‘就是这个难,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用着好的。’辅成道‘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舫道:‘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浇裹,还是一文不能省的。’辅成道:‘这个自然。’雪舫道:‘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辅成发急道:‘这话怎讲?’雪舫笑了一笑,却不答话,辅成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甚么道理。雪舫道:‘我要待不说,又对你不起;要待说了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辅成道:‘说的不近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舫又笑了一笑,依然没有话说。辅成道:‘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甚么话不好说,要这等藏头露尾作甚么呢?’雪舫正色道:‘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朋友不起,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辅成道:‘你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甚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