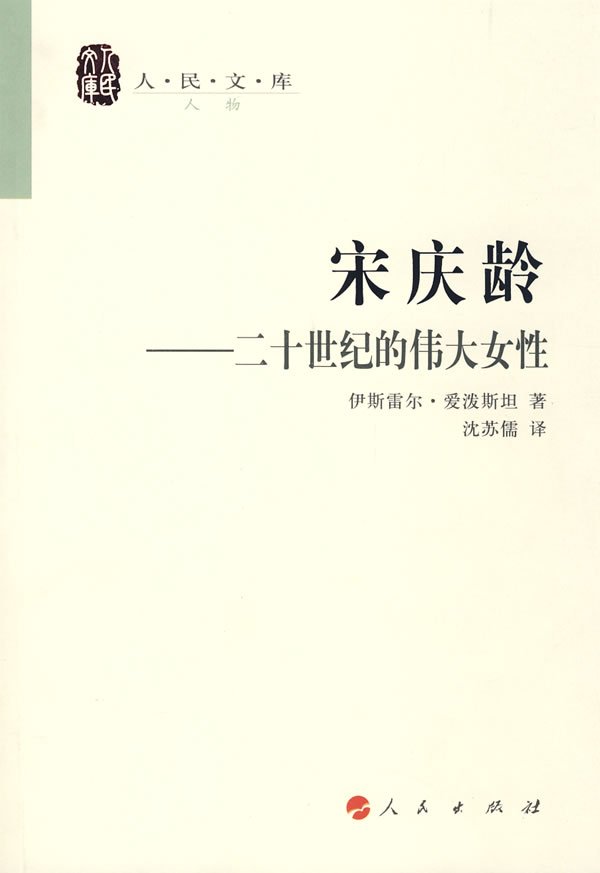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名也)。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
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姊姊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苟姨太太怎样了。姊姊道:“那种人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奁具给他重新理妆,他洗过了脸,梳掠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我道:“回去还不知怎样吵呢。”姊姊道:“这个我们管他做甚!”说罢,各自回房歇息。
次日,继之先到藩署谢委,又到督辕禀知、禀谢,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继之已经奉了劄子,饬知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帐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继之,还带家眷去不带。继之道:“这署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动甚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晋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罢。”我听了,自然无甚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
忽然家人来报说:“藩台的门上大爷来了。”继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甚么事。继之道:“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继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姊姊也在这边,大家说起藩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姊姊,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继之回来了,说道:“我本来日间便要禀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我道:“新任藩台是谁?只怕等新任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继之道;“新藩台是浙江臬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抚台是被参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迅赴新任,毋容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以便中丞好交卸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道:“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罢。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察,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我答应了。
过了两天,附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事毕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甚么事。九江事完之后,便附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得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译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泉,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乘红轿围的蓝呢中轿,在局门口憩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湖色绉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晶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下得轿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对我拱手道:“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镜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认不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厮见。镜江便让我到电局里客堂上坐。我道:“我要发个电信呢。”他道:“这个交给我就是。”我只得随他到客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甚么地方,可还同继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道:“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道:“继之这种人,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舍亲此刻当这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舍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了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值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应道:“这叫做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调桌子打牌。镜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费,便辞了回去。
第二天德泉回电到了,说准定赁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附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继之已经送过中丞,自己也到任去了。姊姊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侣笙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丞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恒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泉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
这天天气晴明,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正是:不是偷闲来竹院,如何此地也逢僧?
不知这和尚是谁,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你道那和尚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弟妇的黎景翼。不觉吃了一惊,便问道:“你是几时出家的?为甚弄到这个模样?”景翼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傅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傅,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的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翼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翼又问我到这里为甚事,住在哪里。我心中一想,我个人招惹他不得,因说道:“我到这里没有甚么事,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翼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一圆洋银给他,他才去了。
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我道:“他在俗家的时候,我就认得他的。”茶博士道:“客人认得他也罢!”我道:“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么能够不认得呢。”茶博士道:“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傅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投到别家庙儿里去。有一回,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请了一百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枷号一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家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
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哪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想,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帐簿上都看见过的,只是一是时想不起来。猛可想起鼓楼弯保合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路到鼓楼弯去,寻到了保合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坐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道:“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舍侄便知道了。”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道:“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哪里?”那后生道:“他捐了个盐知事,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道:“客人快点下船罢,不然潮要来了!”展图道:“知道,我就来。”我道:“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道:“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
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又到镇江稽查了两天帐目,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继之之外,只有文述农是个熟人。我把各处的帐目给继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述农谈天。此时述农派做了帐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帐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述农联床夜话。好得继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游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继之又带了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
这天述农同了我去逛容园。据说这容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三十八处,却又处处的装璜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述农,说这容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述农道:“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化去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化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我道:“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只要他肯化了出来,外面有得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辇到他家么。”述农道:“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化的钱,实在冤枉得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化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三万多银子!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癖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我不觉笑道:“这却为何?”述农道:“这件事你且慢点谈,可否代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我道:“说得好好的,又当甚么差?”
述家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披,是阮文达公写的字。我道:“忽然看起这个做甚么?”述农指着一方图书道:“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摹出这一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三个字。因说道:“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仿摹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仿来何用?”述农一面把横披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道:“摹下来自有用处。方才说的那一班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号甚么意思?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说是那东西既是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