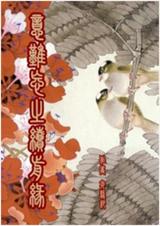不思量自难忘-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爷伸手一挡,上下打量我一番,低声斥道:“还未责问你为何深夜遁逃,你却先来问主子的话?”他又逼近几步,手中捏着一褶白纸,我抬眸一看,愕然而惊,眼前的分明是下午自己做的“课堂笔记”,印象中已被甩落到地上。
我一时无话可说,望着那褶白纸发呆,心想四爷为何偏生盯住了我?此番神机妙算当真是捉贼捉脏,全无托辞。四爷见我噤声,将纸轻放在石桌上,又问:“就为这个?”
我看着那褶纸足有一指厚,心中甚是烦闷,将心一横,登时换上一副宁折不弯的神情:“若为自由故,性命也可抛。奴婢受不得这般约束,与其每日煎熬度日,不如逃了,成则海阔天空,败则死个痛快。再者奴婢以为王府仆从甚多,即便哪日丢了一个,也不过小事一桩,尤其是像奴婢这般猫嫌狗不待见的粗使丫头……”话到此处,便后悔不已,最后那句仿佛是指在桑骂槐。
四爷听闻反倒一笑置之,面色稍缓,道:“原本这等小事从不假我之手。只是猛然间想起凌虚老道的驱魔之物,恐你将那晚的事宣扬出去。”
我心脏一纵,心中已大有缠绵之意,却急声说:“那晚的事我早忘了。”
四爷黑眸一眯,转身便往屋内走,缓缓抛下一句话:“今晚之事就算了,下不为例。”
几日后,窗纸微明,天方破晓,门外骤然传来一阵噪杂之声,我此时清梦正惬,立时惊坐起来,心中窜起一股无名之火,披衣下床,见一红衣女子正指手画脚,吩咐另外几人抬进几只硕大的木盆,盆中衣物堆成得似小山一般。我认得那女子正是弄玉,在嫡福晋乌拉那拉氏身边服侍,近来颇受倚重。这弄玉生得唇红肤白,容貌不俗,只是一说话,必定露出牙龈,面目陡显狰狞。
我推门而出,按捺住火气,问道:“姑娘有何吩咐?”
弄玉眼睑微翻,似乎平日只用眼白看人,指着地上几只木盆,说道:“今日便要把盆中衣物洗完,不然主子责罚,我们一干人还要无端受牵连。我明日一早便要来收。”
我心下愕然,估计此番抬来的衣物足有百十件,便问:“莫非府中只有我一个洗衣的丫头不成?姑娘不是说笑吧?”
“谁有工夫和你说笑了?有道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从前如此,以后也休望有变。你已闲了数月,以后每日都要如同今日这般,按规矩办,打理好后次日一早定会有人来取。”
听到此处,我立时想起几日前小林子的话,大感他当时所言句句非虚,心中登时燃起一团火,心想主子、奴才,奴才、主子,一个不少,都要这般欺软怕硬么?便道:“以展眉一人之力,怕是不足以完成使命。”
弄玉冷笑声乍起,尖声说:“你须得记住,这并非是和你商量,做奴才就是条狗,主子往西,你还想往东不成?莫要以为自己变了模样,长得有几分姿色便一朝得道,把自己抬到天上去。若让主子察觉有忤逆之举,左不过一顿板子?到时候,人脸便成了狗脸!”
我心头热血一窜,回讽道:“多谢姑娘赐教,现下展眉终于明白狗是如何仗了人势的。只是姑娘还须记住什么叫做狗拿耗子,明日展眉必会将衣物一件件洗完,绝不会让人看了笑话。”
弄玉“哼”了一声,便往外走,临到门口还不忘狠啐一口,口中喃喃,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院内一干人等不敢多言,也随之一哄而散。
我怔怔的盯着那堆衣物,半晌才缓过神来,从前即便洗过,也未曾想到今日会以洗衣为业,心口不禁隐隐发酸,却哭不出来。水井旁的皂角粉早见了底,看来只可用手,直到搓净为止。我抬头看了看天色,东方己白,顾不上梳头,便开始打水洗衣,午饭也顾不得吃上一口,直忙到红日西斜才算做完。
陡然感到饥肠辘辘,却迟迟不见有人招呼吃饭。微一沉吟,才想起满人惯于以早午膳为正餐,晚上只进少量饭食,以我这等身份,晚膳怕是免了。想到此处,便回身捧起中午未动的白饭狼吞虎咽起来,待到最后才发觉米饭散着淡淡嗖味,想来定是今日酷热,室中又不通风导致食物腐败变质了。
我顾不得抱怨,只怕吃下腐败之物一病不起,这里连抗生素也无,小病死人是寻常之事。战战兢兢熬过几个时辰,幸好只是腹泻几次,也未见发热,后半夜便倦得昏睡过去。
接连数日,我便过上了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的日子。心下时常疑惑自己究竟是被何人剥削了?四爷么?为何心中总无深刻的阶级仇恨,反而颇多惦念,思来想去便有了答案,或许根结还在于自己觉悟不高。
这晚,小林子来看我,见我神色坦然,也安了心。走时又问要不要替人绣花赚些银两,我颇为心动,便应下了。小林子拿来纸样,不过是寻常的鸳鸯戏水,却要我暂且秀在锦帕上做个小样儿,先给人过目,若绣工过的去,才下定金。待他走后,拿起针线才发觉自己平日连纽扣也缝不好,硬下头皮穿针引线,秀来一看,图案非但全无雅趣,还甚为滑稽,鸳鸯大嘴大眼,不似鸳鸯,倒有几分卡通,不禁怀疑这品种是否与唐老鸭有近亲血缘。
第二日,依旧起早,懒得梳头便开始在井边劳作,只简单披件白色短衫,穿上几日前剪短的半旧长裤,赤脚站在井边的青石台上来回踩踏铺展开的湿衣。裤子因被修剪,卷边早已发毛,几日下来,大有愈穿愈短之势,如今已短至膝部之上,原本七分的裤子变成短裤,不过尚可再将就几日,待立了秋,便可光荣退役了。
耳畔忽而脚步声起,我惕然一惊,不知是哪位不速之客,飞身跳了半圈,脸正对向门口,定睛一看,却是四爷立在眼前。
四爷黑眸沉暗,喃喃道:“瘦了。”
我轻抚脖颈,只觉锁骨峭立,也是吓了一跳。四爷走近几步,凝神看我,从上到下,我想起今早头发未束,短衣短裤更不登大雅之堂,神情甚为局促,便道:“奴婢这就去更衣梳头。”说着,匆匆弯腰穿鞋。正弯腰间却来一阵刺痛,我眉头深蹙,痛得几乎站立不住,扶着井沿半弯腰身,心中只怪连日积劳伤了腰肌。
他四下张望,见地上铺满衣衫,几无下脚之所,不远处还有五六只木盆,内中还有未的洗衣物,脸色一暗,问:“这是积了几日的东西?”
我苦笑一声,答说:“这均是今早送、明早收的。四爷莫怪奴婢‘劳者歌其事’,您可知身上衣衫件件皆辛苦啊!”
过得片刻,我已能缓缓活动,试图再弯下腰身,却陡然觉得身子一轻,已然被四爷凌空抱起,下意识轻蠕身体,立时感觉他双臂一紧,身子再无动转余地。我仿佛跌进一个温暖的陷阱,侧眸看着映射在青石砖墙上光影,轻轻别过头,墙上的影子立时没了距离,叠到一起。四爷见我不住的往墙上瞟,颇为惊疑,循着视线看去,身子忽然一硬,抱的更紧了。
我平躺在床榻上,腰间痛楚却丝毫不减,前额冷汗直冒,四爷伸手,托住我的背脊,蹙眉问道:“很疼么?”
我微一垂首,只觉得他的手只与我的身体隔着薄薄一层衣衫,若就这般抱着不放,可如何是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男子气息,不禁鼻息浅促,连耳根也红了。过了良久,四爷猛然松手,我“哎哟”一声,背脊撞到榻板上,他也是一惊,微一欠身,正要再行察看,我轻轻扭转下身体,陡感腰身轻快,再动转几下,活动丝毫不受牵制,痛意立消。万没料到这腰疾在一撞之下,竟好了大半。
我心中大奇,不及细想,便连声道谢,“多谢四爷,奴婢的腰被您撞好了。”
情势陡转之下,四爷也颇为意外,神情颇有些哭笑不得,怔了片刻,才开口说道:“早知如此,何必陡费周折,刚刚在外面便可轻而易举将你医好。”
我听他口吻似是说笑,遂点头假意啧啧赞道:“四爷这偏方解了奴婢燃眉之急,又救我一次,”
四爷浓眉双扬,却说:“那日我虽答应将你从凌虚老道手中救出来,但对凌虚身份有所顾忌,其间又牵涉甚多,思度良久也无万全之策,倒是你一番智勇,揭了他的巧局,救了自己的性命。”
我连连摆手道:“四爷缪赞了,奴婢只是碰巧……”
他淡然一笑,截住话茬:“看来这几日和小林子学了不少处事之道,只是不知应当夸赞你好,还是要你以本色示人。”
“奴婢性子粗直,若以本色示人还不知能否活到明日午时。”我叹口气,继续道:“此前奴婢想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却被您抓个正着,既然逃不得,不得不随波逐流,总要咬牙挨着活下去不是?”话到此处,我微扁了嘴唇,心中虽有七分不平,话却说得软了三分。
四爷沉吟片刻,又仔细端详我的神色,忽而脸显浅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这般口是心非,怕是想让人疏于防范,待更风声不紧了,再伺机逃匿吧。”
“你……”听他如此言语,我心下登时着了恼,赌气道:“既然四爷怕奴婢口风不紧,唯恐我哪日私逃,不如今日便将我灭了口,岂不干净?顺带告诉您,我展眉平生最恨的便是洗衣,早恨不得把门口那堆东西一把火烧了!”
“展眉?”他喃喃念了几遍,双眉一舒,说道:“你岂是轻易认命之人,这么容易便丢了性命?不说别人不信,怕是自己也不信。”
我此时心口一酸,两滴泪珠夺眶而出,又是委屈又是恼怒,起身拿起放在桌上的锦帕胡乱一抹,又甩手掷回去。四爷起身走到我面前,神色已大为柔和,声音却淡若清水,说道:“这几日叫你受了委屈,你腰伤还未痊愈,暂且不要乱动,那堆东西自会有人收拾。”话未说完,方才放在桌上锦帕被风一带,飘落地上,我弯腰要捡,却听他说:“我来。”
一言方毕,已见他将锦帕拿在手上,正凝神看上面的刺绣,边看边连说了几次:“没想到”。
我不禁暗暗称奇,像他这般惜字如金之人居然一改故辙,一再重复这三个字,一时好奇心起,浑然忘了刚刚还是泪水涟涟一肚子委屈,侧头轻问:“没想到什么?”
他见我片刻之下又换上一副面孔,之前的凄苦之意仿佛早抛到九霄云外,神色间已大为快慰,含笑答说:“没想到府里居然有如此‘心灵手巧’的丫头。”
我定睛一看,见他手中拿的正是我昨晚绣的“鸳鸯”,颇为尴尬,疾声分辩道:“这不是我所长。”
他轻声一笑,眼中似有促狭之意,将那锦帕收到怀里,转身要走,我一个健步飞身堵在门口,强笑道:“四爷,那是我的。”
他慢慢上前附在我耳边,低低吐出一句话。我猛一抬头,正对他的脸,恍惚中,只觉得他神情极为复杂,仿佛这话我早应知道,却横生枝节,偏不领情。
第二日,我一觉醒来,天方大亮,心中甚为奇怪,昨日傍晚破天荒有人来送晚膳,精巧的食盒中饭菜一应俱全,颇为精致,旁边还有一小壶酒,我心喜难耐,打开酒壶,却是一股药香扑鼻,心想几日前虽言语间得罪过某人,却也不至于下毒害我,便安下心享用了这顿美餐。饭罢,只觉眼皮沉重,不及收拾便睡下了,一夜无梦。
我匆匆起身,却见桌子一尘不染,早没了昨晚的杯盘狼藉,门外也再无往日的“彩旗飘摇”,心念一动,登时想起四爷昨日临走时说的话:“这府中哪一样不是我的?”他的?这话究竟是别有深意,还是听者有意的胡乱猜疑?我心中又是甜密,又是失落,万般滋味难以一一理清。
![[hp]史上最花心阿不思!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
![[hp]重生阿不思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7/27069.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