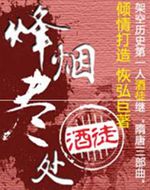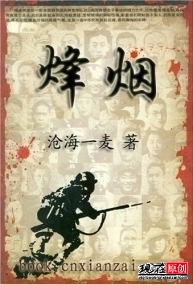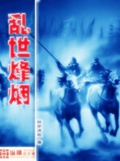烽烟杂感随笔集--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咀嚼一个过程>>
在这一咀嚼过程中的统摄与醒省,必然会让她的诗走向对生命之美与痛苦的更持久更系统的关注。现实中运动的物象,必然会呈现于不同观察者的视角里,本能的、习惯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常常令许多诗人难以避免不同程度的片面、自相矛盾甚至自欺。
难以缔造的,也许才是最激动人心的。化身如一粒沙,淘洗于语言的海潮中,这样的勇气与果敢,或许才是诗人应有的珍贵品格。
栖息于浪尖的君儿,正是幸缘于天地间的起伏。她在心灵相通的观照中,世界竟忽然生发了奇妙的变化--
“它是无所不在的,譬如我开门时顺势而入的寒流
譬如唇齿相依时的亲密无间。
再譬如我所钟爱的水袖、丝竹和远道而来的燕子
它们总使我迷离其中,却使你清醒万分……
春天的钥匙已经在我的衣角叮当作响,
我们正襟危坐,桃花却在我们小小的心脏里破土而出
留恋这片土地。甚至不用告别,我也会泪如雨下
象孩子似的匍匐在你的臂弯,哽咽无语。”
--<<春天是这样来临的>>
在一种令人眩晕的、自然而然的、同时又颇具神秘的沉潜和虔诚里,她坦然接受了对孤独境界的神往。那些引人注目的的跃动,那些交错不休的生命大系,那些意味深长的精神对白无一不刻上内省后的释放,释放后的内省。在一种可贵的阅读相遇中,我想君儿也是幸运的,因为关注与相倾撑开了夜的睡袍,也撑开了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对于一位诗人,语言永远是令她既着迷又困惑的精灵。在一个倾向性创作日益盛大的时代,诗人君儿应该是属于那种敏感得近乎想放弃所有却又不能放弃所有的诗人。惯用的、纯正的、风雅的诗歌语言已经无法满足她对现实的深深体察和对内心世界的完整确认。她在一种可怕的混乱和痛苦中,努力净化着属于她的过去的积雪的声音。她的语言试图穿越内心的呼唤(而这呼唤现在已经被深深掩盖),建立一种对过去和将来秩序化的排列。
“当然,我还保存着同样的病历
和一面墙同居了许多年,
至少我还能很自然地微笑、点头示意。
有的时候,邻居们的窃窃私语
使我感到我们起码都是
即将康复的精神病患者。”
--<<一天的三个过程>>
基于一种暗示,在并非巧合的矛盾中,我们将痛苦而清醒地看到:精神自由与权力结构形成的对峙;典雅庄重的艺术传统与实用媚俗的大众文化的对峙;孤独、敏感的个人独特性与大规模、标准化的技术力量的对峙似乎大众和技术的胜利已属必然?真正不朽的诗篇,难道就是由这样的所谓“胜利诗人”来成就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诗人君儿向我们迎面走来。并携带着不招自来的语境,彻然构筑着深深悲凉中的反复凄吟。
“除了变,一切都不能长久。”(雪莱语)这时候,我似乎看见:执着的诗人,本色的君儿,静静坐在晃动的窗前,在变化的铁的规律下,松开了灵魂的纽扣花朵会有凋谢,花园会有荒芜,花园的主人也会长眠,但“美”永不会消逝,“爱”永不会死去。
“穿着睡衣的女人,她的指甲
象匕首一样刺穿了津津乐道的
家居生活。
她摆放拖鞋的位置,必然令我们
无法产生任何暧昧的联想。
左边是河,右边
并非是岸。
她在船里生育孩子,
一个接着一个。”
--<<家居生活>>
君儿无疑是“理性王国”的离经叛道者。精神的自信与孤独的内视,构成她的个性之美。
在不违反“意象繁复恐慌症”和“形容词禁忌症”的前提下,君儿一直远离着别人的呐喊,她用属于她的特有的距离的远近交替、声音的亢奋与衰弱、光线的明灭与喑哑、心理的沉寂与蹿动,频频与我们约会交谈。在一根细小的针孔缝隙里,揭示着诗人灵魂深处难以遏制的现场“招聘”与“认证”渴求行为。
对此,毋须否认:诗人正力图发现并改造语言和诗质的生命。
这时候,我们应该暖暖注视:诗人有意谓的选择,在不同语境下产生的对客观世界和个体命运的反复检验与垂询,正沿着不断演绎的诗歌大道显出微妙而丰富的语义和要旨。
让我们悄悄擦去所谓的“标准”一词,或者让它淹没于我们能够自然发音的喉部。不期而至的诗歌大潮,势必会在诗人君儿的眉梢豁然舒卷。更多的关注以及深切的凝望,必然趁虚而入。
当然,阳光、鲜花和掌声,并不能替代孤独。
而生命,是一段速溶咖啡的历史。诗人君儿的颤栗俯身察看时,自然形成心灵的投影。这投影,是属于速溶咖啡的投影,也是它的唯一搅拌者。而习惯了搅拌速溶咖啡的君儿--在生活与现实、痛苦与幻想中作息的诗人,必将孤独而卓然地用她自己的声音印证着生命的全部意义。
2003。3。4于深圳
第八篇:新世纪红色胎记的制作者
第八篇:新世纪红色胎记的制作者
新世纪红色胎记的制作者——
论安歌诗歌的话语结构与冲突意识
文/烽烟
一个动荡的时代文学变化的突破口往往是诗歌。时代的特征和生活艺术的再现首先在诗歌中得到反映。
但在反映的过程中,诗歌需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前提:认知。
认知的行为不同于去听一个早已形成的话语,一首我们必须要阐释的虚构作品。它是对一个新的话语的全面论述,是对一种缄默的阐明。认知不是去发现或重构一个被遗忘或隐藏起来的潜在含义,它是被重新唤起的某种东西,是对现实的一种补充。而现实正是它的出发点。
“作品中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才是重要的东西。”(弗洛伊德语)
我常常习惯性地把诗歌的创作指征分为三个过程:一是承诺某种意识形态的过程(提出问题);二是揭示实现承诺的过程(解决问题);三是承诺回归的过程(提升问题)。而在这些过程中,个人的经验取舍、技术运用将决定是否能擦洗掉“失真、失控、失望”的痕迹。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呼唤,我在新世纪的猎猎风中,在一堆看似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话语中,发现了诗人安歌。以及诗人安歌向我们提供的一种新的创作可能和企图建立新的心理阅读挑战的样板。
“只用一种方式忘却
用火的热忘却热,用冰的冷忘却冷
你可以说日期已经被调整,从2001到2002
是九天,说我已如水蔓,已穿过了你身体的河流
已缠绕,在缠绕中已成缠绕
你完全可以不理会火焰的尖叫,你在树木的柴中
我将走尽所有枝丫的歧路,而燃烧的是你
火焰是你,灰烬是你
落上马背的尘土是你,将被尘土吹去的是你
是你的脸——”——
《怀念》
纠缠在一种尖叫中的情感,势必激起回肠荡气的应答。作为一个“灵魂动作“的深入策划者,安歌把彻底粉碎一切的姿态显露出来。但不是简单的狂嚣或喧哗,而是建立在远期的呼唤之上的有节制的理性漏泄。
在安歌的诗歌处于游移状态下的暗示或指证里,在她创作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开的处方之间,总是缺乏一定(或是必然的)连贯性,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破裂的关系。我似乎听到了这种破裂的声音——在秋天的旷野,在行进的火车与躁动的城市,在她体内弥漫不休的撕扯的声音。
“你相信我,还相信他们,这些黑暗中的孩子
需要被相信。正如闪亮的牙齿需要
咬小龙虾,民巷需要着火的大排挡
那人,不一定是你,但叫你,就是你
是你,在黑暗的转弯,拉住了我的手臂
车灯突然亮了,我迷路,我怕这些拐弯,一向如此
所以你是如此亲切,你——我如何收拾这骗局?
你把纹身的鹰贴上我的手臂,我没告诉你
我多么喜欢这个,牠在始终缺少的人那里才会
双目发光。你知道的,你知道
我喜欢你的动作,这是部分真象:
一个过路的妇人在说
我曾经以为我的一切都和你有关
我们的笑声恰好在这句话后响起……
决定螺钉永远独自在你们那里
决定螺钉就是我们各自栖居的陆地”——
《独自》
她遵循事物的常态,把它们可能存在的象征意义任意搬移。安歌似乎在这一刻才体验到在自己房间搭建情绪或者在花园种植的妙趣。然后她总会理智地推开情绪,象刚刚醒悟的剪刀,在她构筑的情节的最后,轻轻一挥舞,剔除多余的花枝。
阅读安歌的作品,我更多的时候是陷入了一种冲突——明确的话语、含蓄的话语、缄默的话语和潜隐的话语之间的相互撕咬与冲突。因此,当我试图单一地去解读她的作品,并对她的作品的连贯性、总体和谐性、美学统一性进行衡量和评价时,这种冲突忽然互不兼容地奔到我面前。在一个激烈的和不断翻新的过程中,这种互不兼容性把生活艺术与现实场景有力地连接在一起。形成跨寓意的链接存在。
“我相信夜风推窗的真诚
相信还未降下的雨
相信还有一些话,在叶子上
还未说出;还有一些路
在风中,还没有撤走
我相信你一直站在那里
是为了等我到来,相信因为思想
你比瘫痪的树更漆黑
我相信那些消失了的杯子,就在你手上
相信你的手溶化进的空气依然站稳
整个动摇的大海
我相信是河流与大山的话语使野花盛开
相信季节,相信它翻开的书页不是唯一的
并相信除此书并无其它沙漏
即使,叶子已扫荡了归路
可我不相信我站在这里,不相信
碎进身体的字是你的吻
不相信宽衣解带我就可以成为动摇的女人
我不相信我不动摇,正如相信
水一进入身体就变成撤退的河流
再注入一杯酒就可以把自己彻底冲走
而雨落上道路就有脆弱的泥泞轰响
酒瓶密封着的是体内锋利的刀刃
我相信它们替我走出的道路也是道路
我准备相信这一切,相信黑夜转身
对准我的脊背就是
背井离乡。相信我将完全拥有
孤独以及对时间的恐惧,相信其中
不断盛开的花朵”——
《相信》
我相信这种冲突不是一种完美的标志,它很任性,但亦人性;我也相信安歌的作品中带有别人的影响的印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独立的,但有同源性;我也相信安歌和她的诗歌,或许正为那些无法说出的压抑、以及蹿动不止的词大伤脑筋。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作为一个岂图把诗歌向某一方向延伸的勇气的制造者,安歌无疑是七十年代诗人群中优秀的代表性人物之一。